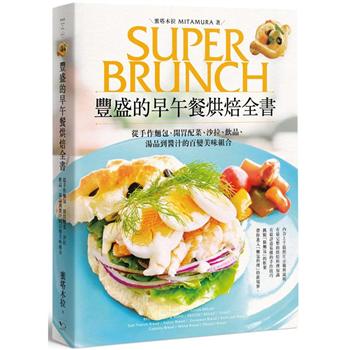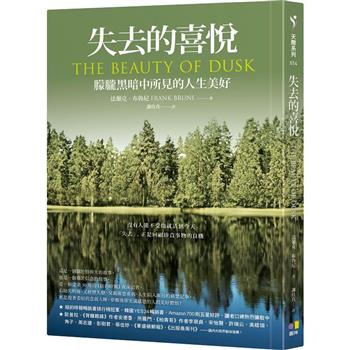圖書名稱:馴羊記
一名旅者為了尋找雪豹,再次突破重重阻礙抵達青藏高原,獲准在保育研究站,進行七十二天的雪豹調查工作。回到臺灣,偶然翻開旅行日誌,發現自己的心仍停留在西藏,毅然決定休學,三度重返高原,這次他要追尋的又是什麼?
一九五○年代,宇田川慧海為了理解更精妙的佛法,遠渡印度非法入境西藏,當時藏軍和解放軍正在各地展開游擊戰,他最終落腳拉薩,與記憶日漸模糊但對佛法有精妙見解的桑吉仁波切一起生活。他將所聞見的經歷,寫成《馴羊記》。
徐振輔以兩條不同時空的故事主線,輔以藏戲《文成公主》故事,將西藏七世紀、二十世紀和當代的重要歷史場景摺疊在一起,讓所有的事件突破時間的限制、羅列眼前,赫然看清一般人認為佛光普照的青藏高原,其實從未平靜。歷經漢代的文化移植,文革席捲,造林停牧,藏人不只命如蜉蝣,原初天性與生活也早已歷劫數次,隨波逐流。
從當代旅者的視角看見藏地的生物萬象,彷如西藏博物誌,岩羊、鼠兔、雪豹、禿鷲等繫起草原生態的自然平衡,同時也從環境史地理學角度寫羊群流行病現象,拉出礦業汙染、草原鼠災、農牧衝突等環境議題,反映西藏正面臨的情感認同與經濟發展衝突。
整部小說語境優美,哲思與隱喻精妙,融合生態、地理、戲劇、建築、遊記等多種元素,將西藏的人文風景、牧民文化、藏人天性描摹得細緻入微,除了展現出作者深厚學養與田調豐富經驗,更處處可見對土地與人文的深情關照。在悼亡的哀惋中,《馴羊記》讓人們看見歷史如何在這片憂傷的高原上重複搬演,以及人民所面對的困境。
作者簡介
徐振輔
一九九四年生於臺北。臺灣大學昆蟲學系畢業,現就讀地理所碩士班。喜歡攝影、旅行、啤酒、貓貓。心血來潮時研究一點點象鼻蟲,已發表SCI期刊論文數篇。
寫作方面在散文、科普、遊記、小說之間搖擺不定,近年比較用心的主題是北極、西藏、婆羅洲、螢火蟲。曾獲選為keep walking西伯利亞極地研究員、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雪豹研究志願者、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等。於《鏡週刊》開設專欄多年,作品四度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臺北文學年金、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若干獎項。
攝影方面胸無大志,夢想是拍攝雪豹、獨角鯨、天堂鳥之類有些人以為是神話的生物。曾任Canon講座講師,舉辦鳥類生態攝影個展《翼疊翼,光覆光》。

 7 則評論
7 則評論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2021/05/19
2021/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