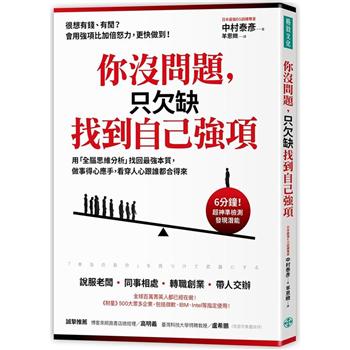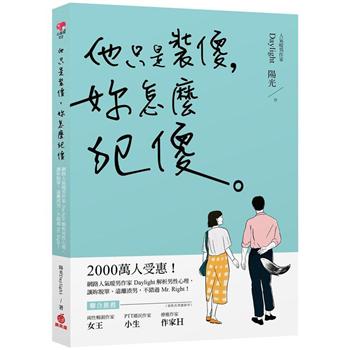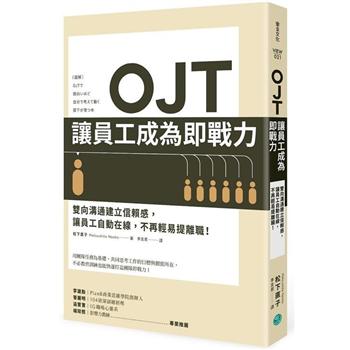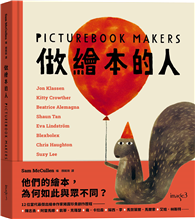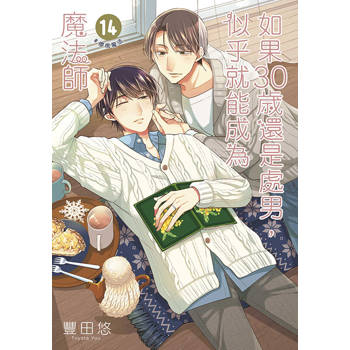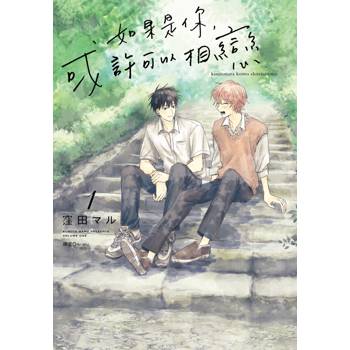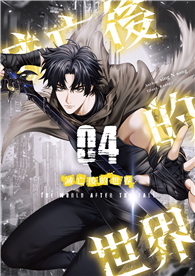一場閱讀的造反行動,
讓150年來活躍於虛構世界的偵探們,
全面揭露,無所遁形……
想像一下,詹宏志身披風衣,口叼著一根菸斗,手中拿著放大鏡正趴在地上「偵察」某個案發現場……,那會是怎樣的一個畫面!?事實上,他的現實生活是時時刻刻帶著「偵探」精神跟本事的。
過去,他是偵察社會變遷的偵探,這回,他從四十年閱讀偵探小說的「老推理迷」身分,扛著紅旗反紅旗,竟開始檢視起150年來活躍於虛構小說中執業的偵探們,將他們拉出虛構幻想的世界,談他們的感情私史、心智結構、職業技能、內心世界、辦案手法,以及偵探們出沒辦案的駐在城市……全然攤開一一檢視。
尤其妙絕的是,作者詹宏志更發揮他的經濟學專才,竟然替這些執業的偵探理出了一份在他看來不符合營運模式的「收費帳單」……耶,看倌可別忘了,偵探工作可也是一份攸關生計的生意啊!
在詹宏志筆下,虛構情節裡的偵探全都”化身”為真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一般,總是在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場景被徵調出場;有時,還會被作者拿來嘲諷現實生活裡所發生的荒誕弔詭的社會事件。畢竟,第一位被創造出來的偵探也是從「嘲弄真實警探」出發的。
全書分成三大篇:
◎第一篇〈想像與真實〉
作者一開始便以一句話透露出箇中玄機:「真實的生活永遠比任何幻想更大膽。」他企圖用虛構情節裡的偵探來嘲諷真實世界。
將時間倒轉一下,幾年前,一列在夜晚行駛台灣東部鄉間僻靜路段的火車突然脫軌,造成中央幾節車廂翻覆,車上乘客飽受驚嚇,而在這次離奇的火車出軌事件裡,卻有一名嫁到台灣的越南新娘喪命……事後偵察發現這名女子被保有鉅額的保險。還不僅止於此,保險公司發現她先生的前一任妻子同樣死於意外,也一樣有巨額的保險。
這樁奇案牽扯出的幾種犯罪模式:毒蛇殺人手法,同樣的橋段便發生在《福爾摩斯辦案記》中的〈斑斕帶〉一篇裡;以火車為犯案地點,從依瑟兒.懷特的《小姐不見了》可見源頭;注射毒針的方法,則接近阿嘉莎.克莉絲蒂的《謀殺在雲端》裡的手法。此外,在〈長頸鹿的眼淚〉中,作者特意將虛構與真實兩造的偵探放在同一個位置作了有趣的對照。以偵辦國務機要費被大家熟知的檢察官陳瑞仁來說,現實世界裡的陳瑞仁為追求真相、鍥而不舍地走訪探詢,不正像極了土屋隆夫筆下的千草檢察官嗎?再者,他堅持發掘真相,不畏現實壓力的道德勇氣,又有達許.漢密特筆下的冷硬派偵探之風。……別忘了,幻想,永遠是真實生活模仿的對象。
◎第二篇:〈訪問記〉
記錄作者親自前往牛津與日本,實地造訪英日兩位推理大師柯林.德克斯特和土屋隆夫的訪談過程。
◎第三篇:〈偵探研究〉
作者從眾家偵探的感情生活、駐在城市、心智結構、職業世界等面向,一一拆解,頓時,讓偵探們再也無從隱藏;甚至連他們收取費用的帳單,也被作者攤開來加以檢驗是否符合營運模式,合不合情理。
該不該讓偵探談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愛?這問題似乎是每位創造他們的作者不約而同儘量避免的部分。然而,綜觀150年的偵探史,果真每個神探都是性欲和愛情的絕緣體?
哦!作者詹宏志要告訴你:當然不是!至於談到偵探的感情生活,福爾摩斯自然是作者第一位「追究」的對象了。到底絕對理性、沉著像一部精密「思考機器」的神探福爾摩斯,可有對某個女子動過心的時候?答案是,有,而且是唯一一次可尋的線索,便是在《波宮祕史》裡,與波希米亞王儲談了一場不被王室所接受的戀愛、名叫艾玲.愛德勒的前衛女子。福爾摩斯寧願捨棄價值連城的酬庸,只為了換得一張她的照片。終其一生,福爾摩斯心中只有「那位女士」(the woman)。由此顯見,柯南道爾刻意塑造一個不容愛情干擾的高度理性的偵探角色。循著這個偵探典範而下,如G.K.卻斯特頓創造了一個神職偵探布朗神父、奧希茲女男爵筆下的「角落裡的老人」……都還是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偵探「禁色」的模式。
第一位起而挑戰「偵探不談戀愛」的禁忌,並質疑缺乏感情生活不合理的,正是身兼記者與詩人的英國作家艾德蒙.克禮修.班萊特,他在《褚蘭特最後一案》便讓褚蘭特墜入案件裡的愛情,藉以諷刺之前的推理小說,他提出偵探也是血肉之軀,如何能不動心動性?之後跟著熱鬧豋場,而且掀起推理小說「美國革命」的,則是達許.漢密特。從此,推理小說被注入人性化元素,偵探隱私被赤裸裸地現形……
詹宏志以一種英式的幽默,冷調卻又處處機巧地嘲弄了虛構小說裡眾家偵探一番。看似嚴謹廣博,卻有信手拈來字裡行間揮灑的趣味。正如作者在序文中所言:這些看似「學問很大」的洋灑論述,講的其實都是「不重要的事」。這些知識不僅無關國計民生,甚至無關「推理小說的欣賞」。……但多了一點對小說「字裡行間」以及「場內場外」的了解,我卻知道,那是可以帶來無窮盡的「娛樂」。
作者簡介:
他,閱讀很雜食。從小學四年級便因為福爾摩斯一頭栽進偵探小說的世界,不可自拔。四十多年來讀過一千多本推理原文書。他自稱是上古時期的「宅男」。有一幕,他「躲」在會議室裡看偵探小說的畫面,至今仍是大家津津樂道的經典畫面。這也是對一位資深推理迷最傳神的詮釋。1956年出生。雙魚座。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現為PChome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對於文化趨勢、社會發展及網路產業,總是比別人觀察得深遠透徹。曾任職於《聯合報》、《中國時報》、遠流出版公司、滾石唱片、中華電視台、《商業週刊》等媒體,並策畫和監製包括《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九部電影。1996年,首創城邦出版集團,為台灣出版產業帶來嶄新的經營概念。1997年,獲台灣PeopleMagazine頒發鑽石獎章。著作有《兩種文學心靈》、《閱讀的反叛》、《趨勢索隱》、《城市觀察》、《創意人》、《城市人》。2006年發表首部散文集《人生一瞬》,2008年《綠光往事》。他的角色多元,但此刻,「自由作家」是他最珍惜的身分。
章節試閱
謀殺會計學
每一份財務報表背後,都隱藏著一場或多場的人間戲劇。
你不一定讀得出來,但它一定化身成某種數字的加減,偷偷影響著你的「最後一列數字」(bottom line)。那可能包含某位副總裁與資深副總裁之間長年的權力惡鬥,或者因為行銷副總的偷情所造成的海外子公司四千萬元的虧損,或者是一份因個性差異而未能談成的合約,或者是採購主任某次喝醉了酒所犯下的錯誤,或者僅僅是一場時間不湊巧的心臟病發……。
沒錯,這些人們亟欲遮蓋的事情都被忠心耿耿的會計帳悄悄記錄下來。企業的財務報表上許多看似面無表情的數字背後,其實是一場場天天激情上演的「人間喜劇」(Human Comedies),要寫下這些故事,恐怕一百個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也不夠用。
倒過來說,那也是可能的,每天耽讀財務報表的人,偶爾也會察覺到某些會計帳上的異常,讓他忍不住盯著數字低頭玩味沉思,如果他願意就鉛筆打勾的數字一路向上追蹤回溯,到了最後,數字也將不再是數字,他將要一頭撞進一場場經過還原的人生驚奇、狂亂、愚昧、荒謬與不堪,甚至還可能撞見幾具錯落其間、不欲人知的屍體……。
推理小說家們顯然是看到這個趣味的,財務報表中不透明數字的foul play,對照真實世界的權貴神祕,死亡可以投資,謀殺也有會計帳,更不要說大量的金錢流動──財富的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為犯罪提供了生猛有力的動機,這當然是推理小說最佳的溫床了。
譬如說小股東借小事發揮鬧場鬧事,讓大股東與經營階層頭痛難堪,這是台灣上市公司近年很常見的場面。有一個故事就說,有家規模龐大卻連年績效不彰的電腦公司,遭到一位小股東的騷擾,但這位小股東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位知名會計師,他寫的會計學教科書甚至是會計科系學生的必讀書。這位會計師股東揚言公司經營欠佳疑有弊端,他號召小股東們的支持,更取得了法院的許可,入駐公司進行查帳,他鬥志昂揚地聲稱要給繼承父業的懦弱總裁和他無能的經營團隊一點顏色看看。他果然讓這家電腦公司的上上下下芒刺在背、坐立難安,不得不搬出其他大股東來當救兵,當兩家大股東法人代表趕來想與這位憤怒的會計師見面情商時,這位會計師卻被發現倒臥在查帳的臨時辦公室裡,計算機的電線緊緊纏在他的脖子上……。
倒臥在帳簿中的死亡,這在真實世界也不少見,台灣軍事採購驚天動地的大弊案「拉法葉艦案」就是這樣的故事。高達數百億元的回扣佣金全球流竄,涉案者固然包括台灣、法國買賣雙方的政軍要人,就連軍事採購所針對的「敵方」北京高層也收到共謀的酬謝,情節離奇到叫人看得瞠目結舌;更駭人的是,案子爆發後,辦案過程困難重重,事實真相阻礙難查又曠日廢時,一段時間回頭再看,涉案當事人一個個在過程中暴斃、病卒、車禍、自殺,出事率百分之百,最近連最後一位關係嫌疑人也死了,所有的線索全斷了,帳簿裡的疑問數字變成了一具具呈問號形狀的屍體,這個案子怕是無解了。
我前面說的那個被計算機電線絞死在小房間裡的會計師的故事,很幸運地,則是來自推理小說名家艾瑪.拉森(Emma Lathen)的名作《謀殺會計學》(Accounting for Murder, 1964),我說「很幸運地」,是因為它來自小說,小說作者一般遠比上帝負責,他總是在另一個鋒面來臨之前,把凶手指出,把真相告訴我們,讓我們不至於餘夜難安,睡不著覺,或者覺得花錢買這本書是個冤大頭。
艾瑪.拉森在推理小說史上是一個很奇特的作者,首先,她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她是推理小說界另一個傳奇的「謀殺雙人組」,或者說,她們是共用一個筆名也共同創作的兩位女作家。其中一位瑪麗.珍.拉昔絲(Mary Jane Latsis, 1927- 1997),是一位曾受雇於聯合國的經濟學家;另一位瑪莎.漢妮撒(Martha Henissart, 1928- ),則是企業金融和銀行的專家。她們兩人自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本推理小說《死亡投資》(Banking On Death)開始,合作無間,共寫了二十四部以投資銀行家約翰.普特南.佘契爾(John Putnam Thatcher)為中心角色的華爾街推理小說,另外還聯合以另一個筆名合寫了七部以國會議員班頓.沙佛德(Benton Safford)為中心角色的政治推理小說,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拉昔絲逝世為止。
兩位作者有趣的地方不只是這樣,她們兩個人不愛公開露面,連多次作品得獎都不肯出席,她們的理由是她們另有專業工作(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要做,不想讓她們的客戶或雇主誤以為她們小說中的內容別有所指,最好不要露面招搖。她們還用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方式合作寫書,兩個人住處海天相隔,她們是用電話討論好案情,然後一個人寫單數章,另一個人寫雙數章,然後匯合成書。這樣的創作竟然能夠銜接得天衣無縫,文字風格與角色塑造也都看不出差異或破綻,真是奇蹟一件。
看帳與謀殺,本來似是風馬牛不相及,但一筆筆帳目來到老練的查帳者眼中,有時候就看出種種蹊蹺。這些帳目的異常,可能就對應了人世間的麻煩事,麻煩事對投資銀行家而言,是該解決的,否則將不利於投資。對冷靜近乎無情的老銀行家佘契爾而言,如果麻煩的帳目竟穿插了幾具屍體,他之所以努力訪查真相,非關公平正義,只是「謀殺無益於生意」,他只是盡力保護公司投資人的利益而已。
會計師臥死於他自己的查帳辦公室的帳簿之中,這個故事出自「謀殺雙人組」艾瑪.拉森在一九六四年的得獎作品《謀殺會計學》,投資銀行家佘契爾再度出擊,從華爾街式的推理中巧破奇案,幽默有趣,發人深省,讓你對上市公司的生態另有體會。
推理小說之所以能夠深入社會千百行業,原因可能正是它吸納百川,千百行業的專家都客串推理作家來說故事,因而創造了「百工圖」式的景觀。醫生投入寫作,推理小說乃有白色巨塔的內幕與面貌;符號學專家投入,我們才讀到《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1983);也正是因為銀行家現身說法,我們才有《死亡投資》這樣的書和艾瑪.拉森這樣的作家。
如果有一天,我的三十年圖書出版和販賣生涯,其中某些刻骨銘心的工作經驗也能化成某種作品,注入推理小說的巨流之中,我猜想至少有兩部作品的書名就應該叫做:《應收帳款謀殺案》和《庫存盤點謀殺案》。
福爾摩斯的帳單
雖然我已經花了相當篇幅討論偵探的職業世界(以及他們的營運模式),但對小說當中偵探的「收費」問題還覺得意猶未盡,好像還可以再多談一些。
但這樣一筆複雜難清的帳,要從何說起?以我的想法,最簡易可行的方法,應該還是回頭重新從福爾摩斯說起;卡爾.雅思培(Karl Jaspers, 1883-1969)不就說過嗎?所謂的「經典」,就是那些我們不斷要回頭重新造訪、也不斷會有新的收穫的典籍。而在偵探這個行業裡,恐怕沒有比福爾摩斯更經典的了。
讓我用福爾摩斯故事中〈松橋探案〉(The Problem of Thor Bridge)這個例子來說明吧,〈松橋探案〉收錄在最後一部短篇小說集《福爾摩斯檔案簿》(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1927)裡,這一部短篇小說集是柯南.道爾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之間所寫的福爾摩斯故事,也是最後的一批。這個時候,柯南.道爾已經撰寫福爾摩斯故事前後將近四十年了,他對自己筆下的角色已經全盤了然於胸,角色的個性、脾氣、語氣都已經完熟了,作者在描繪福爾摩斯的時候,似乎可以不加思索,我們讀起來也覺得生動得「如在眼前」。
在〈松橋探案〉裡,一位擔任過美國參議員的金礦業鉅子前來委託福爾摩斯一個案子,這位外表氣派、態度傲慢、性情急躁的億萬富翁劈頭就說:「讓我話先說前頭,福爾摩斯先生,在這件事上,錢對我不是問題。」他繼續用詞尖銳地說:「你可以把錢拿去燒,只要它對照亮真相有幫助。」最後他極不禮貌地結尾:「你開價吧!」(”name your figure!”)
肥羊上門,開口就說「錢不是問題」,帶來的問題又顯然頗為急迫(牽涉到一條人命,加上一位女子的清白),何況當事人還有一種「為富不仁」的身份,如果福爾摩斯有點「供需法則」的概念,或者有些「劫富濟貧」的俠義之感,他就應該狠狠地開出一個「社會所得重分配」、大快人心的價碼。但是,如果你熟悉福爾摩斯的小說,你當然已經知道不該期待這類的戲劇性,因為福爾摩斯絲毫不為所動,只是淡淡地說:「我的專業服務是固定按級收費的,並不因人而異。你可以先不付,我會最後再一併請款。」(”My professional charges are upon a fixed scale. I do not vary them, save when I remit them altogether...”)
福爾摩斯顯然是不知道或不相信經濟學上「價格差異」(price discrimination)這件事,他並不想向有「支付能力」的有錢人提出更高的價格,他說他「固定按級收費」。但問題是,如果價格是「說一不二、童叟無欺」,那意味著我們在其他篇章裡看到前來求助的「無產者」也付的是相同的價格,這對手上窘迫的無產階級並不是好消息,除非福爾摩斯的服務「物美價廉」,人人付得起。但這樣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一是福爾摩斯極可能會「入不敷出」,另一個副作用是他的案子會太多,讓我們的大偵探疲於奔命,應接不暇。
這兩件事似乎都不曾發生。雖然在辦案時福爾摩斯似乎從不考慮成本,該雇車就雇車,該出差就出差,該登報就登報,該付錢給打聽情報的街童或車伕,他乾脆痛快,從不小氣,我卻不曾在小說裡看到福爾摩斯有過任何財務周轉問題的蛛絲馬跡。而福爾摩斯退休後,他隱居在沙塞克斯郡(Sussex)一棟面對吉英利海峽的「小房子」裡,他謙稱他的房子是「小房子」(my little home),可是有時候又稱它「我的別莊」(my villa),「別莊」一詞源於羅馬時代,指的是「上流階層的鄉間住屋」(an upper-class country house),可見不是寒酸的物件,此屋坐落在一大片土地上的一角,福爾摩斯養蜂消遣自娛,屋中雇有管家照顧他的起居,退休生活優渥舒適,「老有所養」,似乎顧問偵探的營生並不太壞。
福爾摩斯經濟寬裕,似乎並不是來自「薄利多銷」,我在書中看不到他業務繁忙、疲於奔命的模樣(事實上,他的業務有時候冷清到他必須施打嗎啡來提振一點人生的刺激性),福爾摩斯大部分時候一次只辦一件案子,很符合今天我們強調企業要「集中專注」的精神。而福爾摩斯也曾在〈紅櫸莊奇案〉裡對偵探業務的「冷清」感到擔憂,他向華生醫師抱怨「好案子」難尋,他的業務已經快要淪為「替人尋回遺失的鉛筆,以及為寄宿學校女生提供意見的事務所」。總之,他的收費並不低廉到沒有足夠的「累積盈餘」,而他的業務也沒有多到積案盈尺的地步。
雖然作者沒有明說,我總覺得,福爾摩斯的收費標準並不是真的像他所說的「固定按級」那樣不二價(他的說法可能只是對仗財欺人的金礦鉅子的反擊之詞)。當他的客戶是收入微薄的家庭老師(〈紅櫸莊奇案〉)、或入不敷出的當舖小老闆(〈紅髮者聯盟〉)時,福爾摩斯常常是完全不提收費的事;而在某些時候,他對委託人或當事人,也僅要求返還代墊的相關開銷。如果福爾摩斯還能有豐富的積蓄,意味著他極可能在某些(我們沒看見的)時候是「要求」(主動)或「接受」(被動)「較高酬勞」的。
這些「較高的酬勞」究竟可以有多高?如果我們記得福爾摩斯曾經有過多少達官貴人的客戶,或者他經手的案子有時候牽涉到多少驚人的「金額標的」,就可以想像其中的酬勞「可以有多高」。還記得波希米亞王儲委託福爾摩斯時說的那句話嗎:「我願意以國土的一省換回那張照片。」這句話說明了,在某些關鍵性的案件裡,福爾摩斯的確是可以收取一生享用不盡的報酬的。
如果真的要咬住福爾摩斯那句不因人而異的「固定按級收費」,我們要如何來想像這一張「服務價目表」?譬如說:
福爾摩斯顧問偵探社服務收費一覽表
(明碼實價.童叟無欺.保證開立收據.現金支票皆宜.堅辭小費禮敬):
1. 代為尋找遺失的鉛筆(〈紅櫸莊奇案〉)、照片(〈波宮秘史〉)、國防機密文件(《布魯斯-巴丁登計畫》﹝The Adventure of the Bruce-Partington Plans﹞)、價值連城寶石(〈藍柘榴石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或皇冠(〈綠玉冠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等:收費二十英鎊;
2. 代為尋找失蹤或誘拐的雇主(〈紅髮者聯盟〉)、丈夫(〈歪嘴的人〉﹝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未婚夫(〈身份之謎〉)、未婚妻(〈獨身貴族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等:收費五十英鎊;
3. 代為調查死亡或謀殺案件(〈斑斕帶〉):收費一百英鎊,倫敦市外交通食宿費用另計;
4. 代為洗刷罪名或犯罪嫌疑(〈波士堪谷奇案〉﹝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收費一百英鎊,倫敦市外交通食宿費用另計;
5. 代為澄清疑問或解答謎團(〈紅櫸莊奇案〉):視案件性質及複雜度而定,基本收費為二十英鎊。
但這份收費表看起來是行不通的,花二十英鎊找回遺失的鉛筆是不可能的,當時的物價一位家庭教師的年薪約為六十英鎊,你會花三分之一的薪水去找一枝鉛筆或一頂舊帽子嗎?反過來說,藍柘榴石和綠玉冠都價值連城,遺失者甚至都已經出價一千英鎊作為尋獲獎金,收費二十英鎊看起來是不對的了,我們還得再想別的辦法……。
謀殺會計學每一份財務報表背後,都隱藏著一場或多場的人間戲劇。你不一定讀得出來,但它一定化身成某種數字的加減,偷偷影響著你的「最後一列數字」(bottom line)。那可能包含某位副總裁與資深副總裁之間長年的權力惡鬥,或者因為行銷副總的偷情所造成的海外子公司四千萬元的虧損,或者是一份因個性差異而未能談成的合約,或者是採購主任某次喝醉了酒所犯下的錯誤,或者僅僅是一場時間不湊巧的心臟病發……。沒錯,這些人們亟欲遮蓋的事情都被忠心耿耿的會計帳悄悄記錄下來。企業的財務報表上許多看似面無表情的數字背後,其實是一場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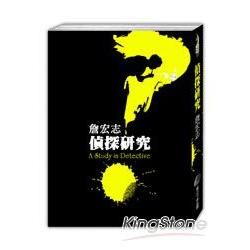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