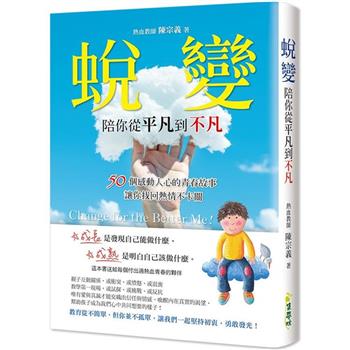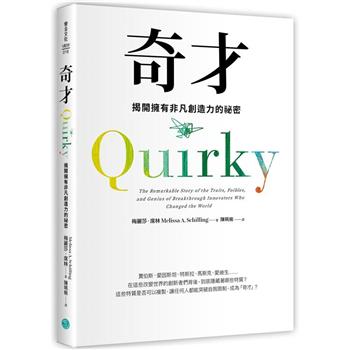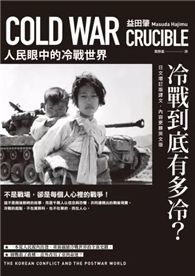我總覺得好像把什麼東西遺忘在家裡了。最後才發現,我沒有帶出來的是「家」。
妮達莉,一個像龍捲風般的開朗少女,她在波士頓出生,但旋即被父母帶回科威特,在那裡長大。出生於伊斯蘭家庭,她有許多不得不遵守、服從的規定與被寫定的命運;而環境中發生的種種紛擾、戰爭,她無從躲避,可是,這些都不是她的問題,因為她有超級無敵的武器──幽默,可以對抗邪惡世界!
她一出生就搞得全家雞飛狗跳,父親希望她是男孩,替她準備了一個男生的名字Nidal(有掙扎、爭吵之意),等到發現她是女孩,只好勉強加上一個字母,變成女孩的名字Nidali,但是,她的母親非常反對,因為,她不要她的女兒一生註定背負著「掙扎」之名。這個鬼靈精怪的小女孩,像雅典娜一樣,從小就讓父親頭疼,她有自己面對這個世界、面對變動不斷的生活、面對挑戰與外界差異的力量與主張。
雖然她父親老是說他們會回到巴勒斯坦,可是她以為科威特是他們永遠的家。直到她十三歲,伊拉克入侵,街道上響起長長的警報聲,他們不得不漏夜展轉到埃及亞歷山卓投靠外公。她的父親仍然想要回去科威特而一天到晚有不同的計畫卻不看現實,她的母親躲在音樂中尋找心靈的平靜。她只好自己想辦法去面對這個世界。
以下這封信,只是她的豐功偉業之一:
親愛的薩達姆.海珊先生,我坐在我父母那輛快解體的車中,我們正跨越您那美麗的國家,從您那醜陋的軍人手中逃脫。我爸爸目前已經送出了四瓶約翰走路跟三條絲質領帶給檢查哨的人員;我媽媽光是在過去四十公里的路途上,就捏了我的腿將近十三次。而我姑姑的火鳥汽車著火,被丟在卡巴拉省。而我,您也許懷疑,當我身邊發生這些無聊的事情時,我在做甚麼?我的內褲裡面正在淌血,卻因為太尷尬而不好意思請車隊停下來。我寫這封信給您,要讓您知道,我焦急地等著見到某位叫做法赫爾.阿爾丁的人,他長得很帥,很愛挖苦人,他今年應該就是我男朋友了,但是,拜您所賜,現在一切都搞砸了。我恨您那他媽的勇氣。我非常希望那佈署在最接近您的火箭船可以用力掰開您的屁眼,我也希望您被驅逐出家園,永遠與您的人民分離,被萬能的阿拉判終生監禁,關在最底層的地獄裡,讓您永遠得用您的左手辦事,讓您手的皮膚永遠被燒光然後再重新長出來。您真摯的朋友,妮達莉.阿墨爾
本書特色
★中東新世代 甩開悲情 用幽默反擊宿命
★《歷史學家》作者Elizabeth Kostova讚歎:我認為我是相當嚴格而不容易動容的讀者,
但在讀到她書中對於家人與生活的敘述,有好幾次忍不住大笑,或者流下眼淚。
★Amazon讀者一致給予五顆星的評價
★這是一本充滿了愛、幽默與洞見的書
作者簡介
朗達.婕拉爾Randa Jarrar
小說家、專欄作家,也是阿拉伯語文學英譯者。一九七八年出生於芝加哥,母親有希臘與埃及血統,父親是巴勒斯坦人,但她是美國人。出生兩個月後,舉家遷移至科威特。她五歲就開始上學,從此喜歡上讀書。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因此全家搬到埃及亞歷山卓。一九九一年,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而遷至紐約。十八歲,她生了一個兒子;二十歲,為了遠離家人與前男友,於是她搬去德州奧斯丁。二○○○年,開始寫小說。
二○○七年,自傳性質濃厚的處女作《帶走月亮的女孩》獲得密西根大學「霍普伍德獎」(Hopwood Award)。二○○八年,此書獲得Arab American Book Award最佳小說獎。《歷史學家》作者Elizabeth Kostova也讚歎:我認為我是相當嚴格而不容易動容的讀者,但在讀到她在敘述中對於家人與生活的論斷,有好幾次忍不住大笑,或者流下眼淚。
她不滿三十歲之前,已經經歷非常多令人驚訝的事情。在她部落格的自我介紹欄中,她寫道:接下來的歲月,還會有戲劇性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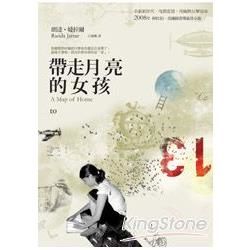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