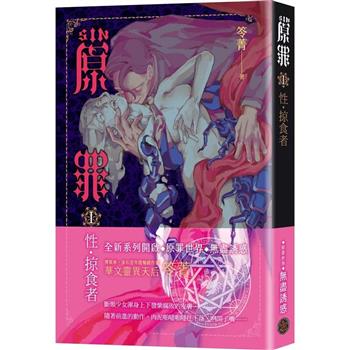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 今日人們常懷想巴黎的美好、藝術與人文,其實巴黎正在1920年代達到高峰。
巴黎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大城,法式生活方式、法式人生觀、法國文學、藝術、電影、料理,更別提建築、豪華渡輪、汽車,都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準,即使現在,我們回首這段風光歲月,依然嘆為觀止。
◆ 本書作者出身於新聞記者,在寫作上卻具備的深度文學技巧。他對於美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個性狂妄,下筆爽快,當眾人奉行「米其林」為至高無上的標準,他卻認為米其林已使得食物的評判統一化,失去了法國外省餐廳的多樣化,還有人們自行開發菜餚的美好感覺。
◆ 原書出版於1959年,至今暢銷。
巴黎最好的一年
1926年,李伯齡在索邦大學遊學,當時的巴黎有多美好?伊夫.密杭德曾經寫道:
「……璀燦、優雅且精緻的巴黎,在上流社會與中上流社會,饗宴輪番不斷,狂歡夜生活接著心醉神迷的宵夜。當時是高級妓女的風雲時代,人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沒人為了老年未雨綢繆,他們都是賭徒、美麗的女賭徒,舉手頭足自然流露高貴的氣息與無以形容的好風度:軟帽飛過風車,卻不流於低俗。」
李伯齡的美食主張
主張之一:沒有好胃口,就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累積足夠的飲食經驗
要將美食寫得活色生香的不二法門是擁有饕餮之胃。沒有好胃口,就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累積足夠的飲食經驗,獲得足堪記錄的材料。因為每一餐都是一次田野調查的機會。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風雲時代,人們除了巨無霸午餐、豪華晚餐之外,看完戲或從事其它夜間消遣之後,還會吃一頓豐盛的消夜。這些講究飲食的人們,到了八十餘歲,食慾依然無懈可擊地好,也一直保持愉快的心情──活力四射、看穿世事,沒有因為擔心飲食不夠均衡而得到胃潰瘍,因此我們怎麼能放棄對人生的好胃口?
主張之二:你當食客學徒期間,你的資金得足以支付帳單,卻又不夠讓你為所欲為。
一位青少年時期即坐擁財富的人,他幾乎註定要成為門外漢食客,因為他不懂得多樣化的調配帶來的美妙。
以珍鳥與牡蠣為主的飲食習慣,和以油膩的甜甜圈與漢堡為主的飲食習慣一樣容易養成,只是前者比較健康,不過卻同樣地畫地自限。並非因為百萬富翁都是笨蛋,而是他們並不需要多嘗試多歷練。學習吃,一如做心理分析,消費顧客必須對價格很敏感,才能有收獲。
終其一生都是有錢人的人也很可能無緣認識味道強勁的肉類佳餚:熱騰騰的腸肚包與豬血腸、市集餐館菜餚、紅酒兔肉煲與老火雞,都是那些只待在某些米其林餐廳的人會錯過的佳餚,他們怎能得知家常料理、大塊烤牛肉的美好!
年幼時曾到過巴黎,1926年又到索邦大學遊學一年,李伯齡在巴黎餐桌上結識的人物,每個人都有他們美妙的故事,加上當時「美好年代」的信念,在巴黎的人、在巴黎做的每件事都是如此讓人印象深刻!透過李伯齡旁徵博引,以及通曉法文的語言天份,本書記憶的法國人物與故事就像一道好菜,讓人回味無窮!
作者簡介
李伯齡(A. J. Liebling)
生於1904年,是紐約客記者,是知名新聞記者,他有一句名言:「新聞自由只屬於掌握新聞的人。」
雖然一出社會就從事新聞業,李伯齡真正想做的是小說家,報社只是他變成偉大作家的中途站。但他總是不能如願,最後他決定繼續新聞工作。詹姆斯?索特說:「他對這份工作又愛又恨,包括做這份工作可以享有的特權、不定的工作時間,以及它的魅力。」
李伯齡在孩提時代曾到過巴黎,1926-27年接受父親的贊助,至巴黎索邦大學遊學一年,1963年辭世之前又前往巴黎一趟。在索邦大學時,他不常上課,「吃」是他的主修科目。
李伯齡著作約有十八種之多,如:李伯齡精選集(The Most of A.J. Liebling)、李柏齡《紐約客》文選(Liebling at The New Yorker)。其中,甜蜜的科學(The Sweet Science)被藍燈書屋選為二十世紀,一百本最好的非文學類作品之一。
譯者簡介
陳蓁美
政大廣告系畢,法國Poitiers大學電影博士候選人。一九九六年至二○○四年,旅居加拿大蒙特婁、法國Poitiers、Laval等地求學。回國後從事翻譯,譯有《花的智慧》、《藍色圓圈之謎》、《夜》。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