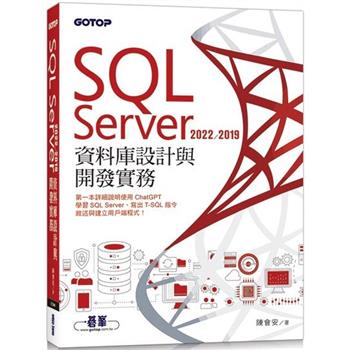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林峻煒的圖書 |
 |
$ 446 ~ 675 | 思想史 12: 史思傳薪 紀念余英時院士專號
作者:傅揚/韓承樺/徐兆安/孔德維/張曉宇/楊正顯/翁稷安/林峻煒/余一泓/黃相輔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1-18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思想史12(史思傳薪:紀念余英時院士專號)
內容簡介
《思想史12》收錄論文10篇,本期的專號是「史思傳薪:紀念余英時院士」,論文有傅揚的〈余英時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韓承樺的〈史家的兩個世界余英時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徐兆安的〈錢穆與余英時的兩種「士之自覺」:從1960年論學書切入的討論〉、孔德維的〈在三十五年後回顧余英時的「韋伯式問題」:宗教學的觀察〉、張曉宇的〈橫看成嶺側成峰──《朱熹的歷史世界》理路芻議〉、楊正顯的〈王陽明的教化觀:從余英時先生「覺民行道」說談起〉、翁稷安的〈「革命的果實轉化成了對他們自己的毀滅」──試論余英時對中國近現代激進化的思索〉、林峻煒的〈明代中晚期《中庸》鬼神章之詮解-以蔡清、袁黃與葛寅亮為主的討論〉、余一泓的〈重訪人文之道:劉咸炘的中西文化論說(1922-1932)〉、黃相輔的〈進化與普世:雷海宗對《世界史綱》的批評〉。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傅 揚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韓承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徐兆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孔德維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
張曉宇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楊正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翁稷安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林峻煒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余一泓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講師
黃相輔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目錄
潘光哲 主編小引
【專號論文】
傅 揚 余英時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
韓承樺 史家的兩個世界:余英時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研究
徐兆安 錢穆與余英時的兩種「士之自覺」:從1960年論學書切入的討論
孔德維 在三十五年後回顧余英時的「韋伯式問題」:宗教學的觀察
張曉宇 橫看成嶺側成峰——《朱熹的歷史世界》理路芻議
楊正顯 王陽明的教化觀:從余英時先生「覺民行道」說談起
翁稷安 「革命的果實轉化成了對他們自己的毀滅」——試論余英時對中國近現代激進化的思索
【一般論文】
林峻煒 明代中晚期《中庸》鬼神章之詮解——以蔡清、袁黃與葛寅亮為主的討論
余一泓 重訪人文之道:劉咸炘的中西文化論說(1922-1932)
黃相輔 進化與普世:雷海宗對《世界史綱》的批評
【專號論文】
傅 揚 余英時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
韓承樺 史家的兩個世界:余英時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研究
徐兆安 錢穆與余英時的兩種「士之自覺」:從1960年論學書切入的討論
孔德維 在三十五年後回顧余英時的「韋伯式問題」:宗教學的觀察
張曉宇 橫看成嶺側成峰——《朱熹的歷史世界》理路芻議
楊正顯 王陽明的教化觀:從余英時先生「覺民行道」說談起
翁稷安 「革命的果實轉化成了對他們自己的毀滅」——試論余英時對中國近現代激進化的思索
【一般論文】
林峻煒 明代中晚期《中庸》鬼神章之詮解——以蔡清、袁黃與葛寅亮為主的討論
余一泓 重訪人文之道:劉咸炘的中西文化論說(1922-1932)
黃相輔 進化與普世:雷海宗對《世界史綱》的批評
序
主編小引
潘光哲
陳寅恪(1890-1969)在二十世紀華人史學社群裏的地位,眾所公認。只是,想要解讀他的著作,以及背後的心態,卻不見得是件容易的事情。舉例來說,當他完成〈論再生緣〉(1954年),向外流傳,頓即引發各方回應,「傳播中外,議論紛紜」。例如,胡適(1891-1962)也得到了一分,批讀一過,對陳寅恪這部自稱「說盡人間未了情」的書,幾乎全無認同,不時留下「迂腐」這樣字眼的眉批。陳寅恪當然不可能知道胡適的批評(他應該也會不在乎);相形之下,不到三十歲的余英時(1930-2021)在1958年解讀〈論再生緣〉之要旨,一在藉考證〈再生緣〉作者陳端生之身世,以寓自傷之意;二在藉〈論再生緣〉之書,而感慨世變,以抒發其對當前之極權統治之深惡痛絕之情,卻讓陳寅恪視為「作者知我」,儼然深感一己的苦心孤詣,確有知音。時隔多年,因緣際會,余英時又提筆寫下了〈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983年),這回他得承受的,卻是來自中共官方的絕無善意的批評;箇中曲折,如何廣引史材,詳為疏理,有待賢者,這裡就不詳述了。
舉此一例,正可想見余英時的學術遺產,豐富多樣;《思想史》本期以「史思傳薪:紀念余英時院士」為專號,以青年世代的學者為撰稿主力,其意不僅在為余英時的學術貢獻,闡幽抉微;更願長江後浪,乘波而起,再創新知。即如本期專輯裡,韓承樺教授闡明余英時研究中國知識群體的意涵,雖未全盤清理余英時研究陳寅恪之始末與爭議,仍復以此為例,余英時如何透過陳寅恪的書寫,向讀者揭露歷史與當代、知識和價值,兩個世界在知識階層研究的交織互動。新生世代對於史界前賢的詮解,自有一己的獨特觀照。即如徐兆安教授藉由錢穆致余英時的論學書信,鉤沉師徒對於「自覺」概念的重大分歧,非僅述說雙方歷史解釋的不同進路,復可考索各自的思想淵源,亦有獨特之見;而如孔德維博士反思余英時另一名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6年),藉他山之石,進而析論研究近世的中國宗教與經濟活動,已然拓展的面向與可以持續關注並深化的議題。至於本期專號的其他佳作,各有貢獻與成績,有心之士必然展卷有益;不勞筆者一一費辭。
二十世紀的中國鉅型知識人(及其相關人物)研究,早已蔚為龐大的學術事業。研究魯迅(1881-1936),「魯學」乃興;研治胡適,「胡學」正盛;探究陳寅恪,「陳學」已立。我們相信,未來研究余英時,也必將展現「余學」的閎闊格局。然而,啟步之始,套用他的提醒:
一部中國史浩瀚無垠,它不是一個只可供少數逞才使氣的英雄人物馳驅征服的疆場。只有許多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把這塊大地化為一片肥沃的綠野……。
研究余英時,需要的不是摭拾其著述之一二,仰仗小知小慧,信筆而就的才子;相對的,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讓余英時豐厚的學思遺產,在華人文化知識社群裏,化為永遠不能割捨的構成要素。
本期專號的文章,最初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研究群主辦之「余英時院士逝世周年紀念工作坊」(台北:2022年8月5日);會議宣讀之論文,須經審查通過,始得出版發表,不免有遺珠之憾。會議之舉辦,蒙近代史研究所支持,並得余氏高徒王汎森院士俯允,擔任主題演講人,謹此特致謝悃。與會宣讀與評論諸篇論文之名家,亦在此一併致謝。個人承司本刊主編,得以匯總諸篇佳作,簡略稍抒愚見,自感榮寵。一切努力,如能得到學界的支持迴響和批評指教,必將是最大的榮幸。
潘光哲
陳寅恪(1890-1969)在二十世紀華人史學社群裏的地位,眾所公認。只是,想要解讀他的著作,以及背後的心態,卻不見得是件容易的事情。舉例來說,當他完成〈論再生緣〉(1954年),向外流傳,頓即引發各方回應,「傳播中外,議論紛紜」。例如,胡適(1891-1962)也得到了一分,批讀一過,對陳寅恪這部自稱「說盡人間未了情」的書,幾乎全無認同,不時留下「迂腐」這樣字眼的眉批。陳寅恪當然不可能知道胡適的批評(他應該也會不在乎);相形之下,不到三十歲的余英時(1930-2021)在1958年解讀〈論再生緣〉之要旨,一在藉考證〈再生緣〉作者陳端生之身世,以寓自傷之意;二在藉〈論再生緣〉之書,而感慨世變,以抒發其對當前之極權統治之深惡痛絕之情,卻讓陳寅恪視為「作者知我」,儼然深感一己的苦心孤詣,確有知音。時隔多年,因緣際會,余英時又提筆寫下了〈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983年),這回他得承受的,卻是來自中共官方的絕無善意的批評;箇中曲折,如何廣引史材,詳為疏理,有待賢者,這裡就不詳述了。
舉此一例,正可想見余英時的學術遺產,豐富多樣;《思想史》本期以「史思傳薪:紀念余英時院士」為專號,以青年世代的學者為撰稿主力,其意不僅在為余英時的學術貢獻,闡幽抉微;更願長江後浪,乘波而起,再創新知。即如本期專輯裡,韓承樺教授闡明余英時研究中國知識群體的意涵,雖未全盤清理余英時研究陳寅恪之始末與爭議,仍復以此為例,余英時如何透過陳寅恪的書寫,向讀者揭露歷史與當代、知識和價值,兩個世界在知識階層研究的交織互動。新生世代對於史界前賢的詮解,自有一己的獨特觀照。即如徐兆安教授藉由錢穆致余英時的論學書信,鉤沉師徒對於「自覺」概念的重大分歧,非僅述說雙方歷史解釋的不同進路,復可考索各自的思想淵源,亦有獨特之見;而如孔德維博士反思余英時另一名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6年),藉他山之石,進而析論研究近世的中國宗教與經濟活動,已然拓展的面向與可以持續關注並深化的議題。至於本期專號的其他佳作,各有貢獻與成績,有心之士必然展卷有益;不勞筆者一一費辭。
二十世紀的中國鉅型知識人(及其相關人物)研究,早已蔚為龐大的學術事業。研究魯迅(1881-1936),「魯學」乃興;研治胡適,「胡學」正盛;探究陳寅恪,「陳學」已立。我們相信,未來研究余英時,也必將展現「余學」的閎闊格局。然而,啟步之始,套用他的提醒:
一部中國史浩瀚無垠,它不是一個只可供少數逞才使氣的英雄人物馳驅征服的疆場。只有許多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把這塊大地化為一片肥沃的綠野……。
研究余英時,需要的不是摭拾其著述之一二,仰仗小知小慧,信筆而就的才子;相對的,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讓余英時豐厚的學思遺產,在華人文化知識社群裏,化為永遠不能割捨的構成要素。
本期專號的文章,最初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研究群主辦之「余英時院士逝世周年紀念工作坊」(台北:2022年8月5日);會議宣讀之論文,須經審查通過,始得出版發表,不免有遺珠之憾。會議之舉辦,蒙近代史研究所支持,並得余氏高徒王汎森院士俯允,擔任主題演講人,謹此特致謝悃。與會宣讀與評論諸篇論文之名家,亦在此一併致謝。個人承司本刊主編,得以匯總諸篇佳作,簡略稍抒愚見,自感榮寵。一切努力,如能得到學界的支持迴響和批評指教,必將是最大的榮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