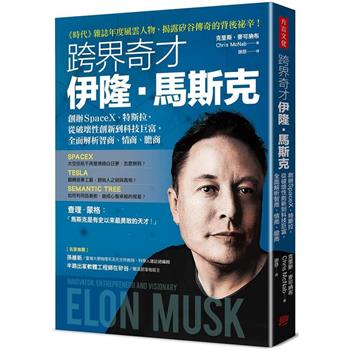世界,是我的田野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發現之旅
MARGARET MEAD: A BIOGRAPHY
瑪麗.包曼—克如姆◎著 楊德睿.陳秀琪◎譯
隻身勇闖南太平洋叢林、追尋生命答案的瑪格麗特.米德說:
「最微不足道的旅程,卻可能是永恆之旅。」
●全世界最受歡迎的人類學家.台灣書市最平易近人的完全讀本
●國際級紀錄片導演、人類學家 胡台麗 推薦
關於瑪格麗特.米德:
★1925年,未滿24歲的米德便隻身遠赴南太平洋上的小島薩摩亞。在薩摩亞的九個月以及後續的旅行,讓米德成為南太平洋文化的權威。米德的口頭禪是:「世界是我的田野,一切都是人類學!」
★1928年寫作出版《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大獲成功。米德改變了人們思考世界的方式,促使我們反思自己和其他民族的文化。
★米德對教育的看法是,年輕人需要「一段時間去發現自己,但我們的社會組織方式卻推促著每一個人從童年直接跳進成年」。
★雖然米德的看法常常令人難以接受,但她所說的話其實比她所身處的時代領先50年。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個世界才正在開始趕上她的想法。
★「紐約時報」評論:「若有任何人堪稱為博學大家,那米德博士便是被廣為認可的一位。」
★米德熱愛演講,職業生涯的高峰時期曾創下一年演講超過一百場的紀錄。米德曾有一次抱怨說她已累壞了。「好像全天下就只有我一個人會演講似的!」
★米德一生中共有三任丈夫,也離過三次婚,並有兩位極要好的女性知己。在1975年一篇文章裡她寫道:「我認為,我們必須把雙性戀看做是人類正常行為模式之一,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了。」米德說雙性戀並不新鮮,但拓展我們對於人類去愛的能力的知解和接納,卻很新鮮。
本書不但要訴說米德充滿爭議的人生旅程,更要引領你進入米德深具影響力的思考方式。
關於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
美國人類學領域最重要學者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人類學家,1978年逝世後隨即獲授總統自由獎章。
米德的父親是一位經濟學教授,母親是社會學博士,為爭取婦女權益、黑人或移民待遇等奉獻心力。米德在18歲時走到了一個生命的轉折點。對她而言,未來的成功取決於大學教育。她不顧父親投資失敗反對她讀大學,反而堅定自己的立場,爭取無論如何都要接受大學教育。
1924年,是她一生的另一個轉折。她結識了當時美國人類學界的重要學者法蘭茲.鮑亞士和露絲.潘乃德。米德成為鮑亞士的弟子,也獲得了投入人類學的勇氣和信心。米德23歲迅速取得心理學碩士之後,1925年,未滿24歲的米德便隻身遠赴南太平洋上的小島薩摩亞。她亟欲探討困擾美國青少年的問題究竟是文化所造成的後果,還是所有青少年都逃脫不了的宿命。
1928年米德出版了《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轟動一時,她不僅以生動、幽默的語言對原始文化的所見所聞娓娓道來,書中更強調「塑造人的行為方式的主因,是文化而非生物因素」,她發現薩摩亞的年輕人能毫無困難地從孩童過渡到成人階段,並未經歷過美國青少年的風暴和壓力。在「教養抑或天性」這一爭論上,米德無疑地站在了教養這一方。
1935年,米德再以《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一書,掀起「性別」議題的波瀾,影響了整個世代的女權運動者。這一次,她闖蕩新幾內亞的叢林,並以此書奠定了性別的文化決定論。
米德將人類學從社會科學中一個鮮為人知、艱澀冷僻的領域,帶進了公眾的意識裡,在這個過程中,瑪格麗特.米德成了舉世皆知的名字。
作者簡介
瑪麗.包曼—克如姆(Mary Bowman-Kruhm)
執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商業教育專業研究院,著有三十本以上的兒童和青少年讀物。
譯者簡介
楊德睿
1997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2003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博士,現任中國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譯有《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2002麥田)《搞電影的歌俚謳:尚.胡許的民族誌》(2003麥田)等書。
陳秀琪
1998年英國諾丁罕川特大學流行與織品學系碩士,現從事編輯企劃及翻譯。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