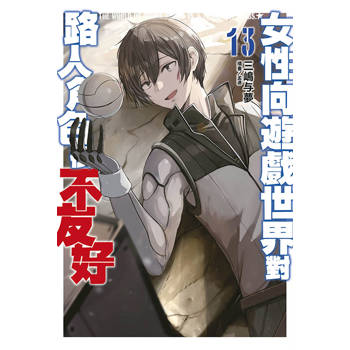序
接地氣的作家 王干
樊健軍在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的時候,我算作他的「導師」,文學創作找導師,實在是有點牽強,好多的行當需要承傳,需要手把手的教導,但唯獨文學不需要什麼師傅,什麼導師,文學創作的魅力就在於它的個人性、自學性和無師性。如果文學可以通過師徒的方式加以教授,那麼李白的家族就會壟斷詩歌的榮譽,曹雪芹的後代也會壟斷小說的世界,而莎士比亞的子孫則終日可以躺在戲劇的舞臺上吃不完。文學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可複製性,連大作家自己都很難寫一部重複自己輝煌的作品,甭說去指導別人寫作好作品了。
那些以導師自居的導師,多半是把文學當成手藝和工藝了,內心裡是為了受人膜拜而已。文學有大師,文學無大師傅。以文學大師傅名噪文壇的人,很多是遠離文學本質的門外漢。但文學不是封閉的產物,「宅」在家裡一時可以,「宅」一輩子的作家很難成為大師。文學需要交流,文學需要碰撞,交流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的,碰撞的方式也是不一定要面對面的。閱讀是一種交流,網路也是一種交流,對話是一種交流,傾聽也是一種交流。文學本身就是心靈與心靈的交流,也是心靈與現實的交流,寫作本身就是對交流的渴望而為。
雖然對樊健軍的創作提不出什麼指導性的意見,但我始終關注他的創作,一是工作的原因,因為我長期在選刊類的刊物工作,對當下的小說創作必須進行工作性的閱讀,二是樊健軍的小說和我所喜好的那一路小說有著內在的鏈結。鏈結是網路上的一個詞,但對文學來說,始終存在著某種鏈結,比如,你讀蘇東坡的詩歌,不能不聯想到李白,這種聯想其實是在思維裡搭了個「鏈結」,網路上的鏈結是手動的,而腦子裡的鏈結是全自動的,自動鏈結的。
樊健軍的小說鏈結的是沈從文、汪曾祺這一路的作家,這一路的作家常常被文學史家們歸結為鄉土小說或市井小說,在我們共和國的文學話語裡,鄉土是有正能量的可能,而市井則有貶義的嫌疑。其實,鄉土也好市井也好,而在我看來,他們都是接地氣的作家。好的作家是接地氣的,好的文學是接地氣的,好的小說必然是接地氣的。接地氣的說法來自老百姓,地氣也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包涵有根基、有人氣、有積澱等多層寓意。
在文藝界有一個比較官方的說法,叫深入生活,引起人們的歧義,因為處處有生活,你幹嘛另外去找生活,而且每個人都是在生活之中,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有價值的呀。但其實生活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有人生活在生活的高端,有人生活在生活的淺處,有的人生活平淡無奇,有的人生活波瀾壯闊,不是所有的生活質量都是等值的。深入生活的說法其實就是接地氣的意思,好的小說必然和當下的生活血脈相連,和老百姓的生存息息相關。不接地氣的作家雖然看上去很美麗,但實際是空中閣樓、沙灘的摩天大廈。
樊健軍的小說很接地氣,《水門世相》這本系列短篇小說集散發著濃重的生活氣息,甚至是那股漚過的青草的重味道,所以把它稱之為「草根」是恰切的。「這裡有身體殘缺的:高不過三尺的侏儒,石女羅鍋,眼瞎的、腿瘸的、耳背的,長著兩顆腦袋的女人;有下三濫的:賭徒酒鬼,騙子無賴,像種豬一樣活著的英俊男人,成天追逐男人的花癡;有裝神弄鬼的神漢巫婆,也有性格怪異的穴居者,有潔癖的盜賊,也有靠紙紮活著的手藝人……這些人聚居在一個叫水門的特殊村莊,構成了一個獨特的世界。他們既有謀求生活的小智慧,也有玩弄生活的小聰明,既有男歡女愛的純樸堅貞,也有遺世獨立的悲愴孤獨,既有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溫暖幸福,也有複雜得無法再複雜的辛酸蒼涼,既有順世昌運的得意,也有流世苟活的失落。他們不論『食草的』還是『食肉的』,各有各的方式,各顯各的能耐,三百六十行都能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生存空間,都有一套生存行規。」
樊健軍不僅寫出了他們的生存狀態,還寫出了獨特的鄉村生活智慧。中國鄉村的生存是不像一些田園牧歌者想像的那麼簡單,尤其是那些自然條件困難的地域人們的生存更是困難而艱辛,有時候會失去尊嚴而活著。比如「長相英俊的青玉,女人們人見人愛,卻淪為種豬一樣的男人,靠給女人借種而苟且活著;兵痞比歲為了逃避殺身之禍,將自己的女人刺瞎雙眼,靠了女人的掩護浪跡江湖。傻子阿三生就傻瓜相,誰也沒想到他是個騙子,屢騙屢屢得手;文叔是個乾淨得有些潔癖的人,紅白喜事都坐上房陪上客,一次酒醉後卻洩露了自己的祕密,他是個盜賊;濟堂老腳借了神鬼菩薩的嘴,騙吃騙喝,最終死在了貪吃的毛病上。」
這種鄉村生存智慧很難用道德評判,它時不時還會閃著歡樂的色彩。「高不過三尺的繡雲偏嫁給了牛高馬大的滿地,繡雲騎在滿地的脖子上看電影,過河,他們的愛情讓人忍俊不禁;仿明是個瞎子,紅繡又啞又聾,他們結合在一塊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再美的東西有眼睛看到,再動聽的聲音有耳朵聽到。」
作家雖然寫的是世相,骨子裡說的是中國鄉土社會的倫理文化,這倫理文化凝聚成鄉村的生存智慧之後,又反過來影響中國的倫理文化,鬆動或者板結我們腳下的這塊文化土壤。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因此生生不息,也因此根深蒂固,負載深重。
記得十多年前,也是與樊健軍地域相鄰的另一個江西作家葉紹榮出版小說集,讓我寫序,當時我的題目叫《野風浩蕩》,他們有某種相似之處,那時我看中的是其「野性的思維」,而現在我則把樊健軍的小說視為地氣升騰出的野果。這是我寫作此序時的一個橫向「鏈結」。
二○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於北京農展館南里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