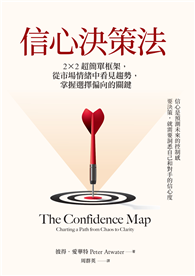在學校這個權力不對等的體制下,
兒童的小小生命,就被掐在教師手中……
兒童的小小生命,就被掐在教師手中……
「只要我忍耐,就不會有人受傷。」(被性侵的女高中生)
「老師生起氣來很可怕,可能我也有錯吧?」(被猥褻的國小女生)
──為什麼遍體鱗傷了,還要檢討自己?
為什麼說出真相,大家都包庇狼師?
作者池谷孝司是專訪日本「校園性別事件」的記者,也是日本唯一一位關注此議題的「男性」記者。本書是他10多年來的深度考察,詳載了無數曾遭教師性侵、性騷擾的學童們「不敢說不」「無法啟齒」「不見天日」的痛苦,並與日本唯一專門處理此類事件的NPO團體「防止校園性騷擾全國網絡」(SSHP)攜手,致力於杜絕全日本的加害狼師,協助被害人勇於說出真相。
無人聽見的求助──在學校才會發生的事件
在傳統的教育觀念下,我們總以為「老師不是一般人」「老師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特別是在校園這個封閉的空間裡,教師擁有絕對的權力──國小生的心智還不成熟,只得乖乖聽從老師的話;國高中生擔心對未來升學不利,所以選擇服從老師。
每當發生性別事件時,總是重複著以下的模式:
▶校方為了自保而慣性隱瞞,或是私下解決
▶其他老師同仁不想惹事生非,只是旁觀;甚至作證後反遭恐嚇,只得禁聲
▶擁護狼師的家長們組成「啦啦隊」來聲援,打擊被害人
▶加害教師始終堅稱:「我沒有做!」
於是一切便告終,受害學童就這麼被抹黑成「騙子」……
不僅教師無法察覺學生「無法說不」,家長也難以處理孩子敏感的心思與事件背後複雜的因素:
【無聲的抵抗】
國小女生被老師帶去賓館性侵,當老師脫光她全身的衣服時,發現她穿了兩條內褲。她無法拒絕,這是她僅能做出的抵抗:「求求老師不要碰我……」
【扭曲的心靈】
家長發現校隊顧問是狼師,瞞著女兒告發學校,然而女兒卻對此不滿。因為害怕自己過去的成就感被抹滅,還會遭來其他社員的攻擊……
【代代相傳的狼師問題】
許多年過4、50的媽媽前來諮詢,原因是發現女兒就讀的高中的校長,正是當年性騷擾自己的教師。原來要忍到這種地步才說得出口……
如何不讓孩子長大才喊#MeToo?
或許,我們無法立即翻轉教育、改變師培方式。但是至少從現在起,請對孩子說:「身體是屬於自己的,不喜歡就要說不喜歡,無論發生什麼事,爸爸媽媽都會相信你說的話!」同時也對自己說:「選擇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加害人的那一方!」當發生事件時,盡可能留下紀錄,由獨立機構介入處理,避免校方自行解決。
營造出讓受害孩子與旁觀者都願意坦白、說得出口的環境,或許,就能讓這樣的事件漸漸攤在陽光底下……
──性騷擾,沒有誣告!
房思琪,一個都太多!!
雖然當初說不出口,現在說出來也沒關係!
名人推薦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沈雅琪│神老師&神媽咪、資深國小教師
★林靜如│律師娘
★苗博雅│政治、新媒體工作者
★陳潔晧│《不再沈默》作者
★張旖旂│愛爾達電視體育主播
──沉痛推薦!(依姓名筆畫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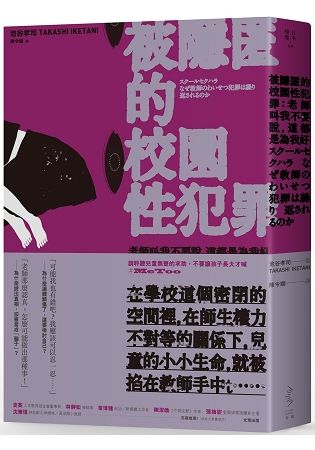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