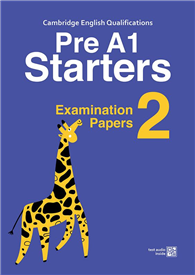推薦序1
精彩易懂的日治台灣邊緣史∕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帝國的外地台灣,向來被重視的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嚴格說來是民主運動)、殖民治理性與現代性、殖產興業、台灣菁英、總督府的南進政策等林林總總的問題,對於生活在台灣社會底層的民眾,一直不在學術研究的主流中。不要說是學界,就是台灣熱鬧滾滾的全民口述歷史,除了為平反政治案件而對政治受害者家屬、受難者本身訪談外,很少為弱勢者發聲,更不用說為社會邊緣人留下歷史。然而菁英的歷史、主流的歷史,並非歷史的全部,實存的底層社會的面貌也是重要的歷史,具有存在的價值。任何殖民地的歷史,都脫不了由民族、階級、性別這三個角度來加以觀察,台灣邊緣人的面貌也非得考量上述問題不可。
本書除導讀外,分由十位作者針對阿片吸食者、娼妓、受刑人、浮浪者、不良少年、窮人、漢生病患及精神病患,用淺顯的文字來加以描述,使讀者很快地被議題所牽引,而想一口氣看完。上述八種邊緣人,並不只發生在日治,綿延至戰後,事實上清代早已發生。讓我們由《馬偕日記》來舉兩個漢生病的例子。1888年10月15日馬偕「醫師」記載了漢生病患:「我們全去醫館。看診全部三十或四十名舊病患,還有大約二十名新病患。幾位痳瘋病患在其中。當我們與這種疾病面對面的時候,我們人類的知識多麼貧乏呀。一位年輕人二十歲,當我告知我們對他所能做的事很小時,看起來很悲傷。大腳姆指底下已經有一個大洞,一邊已經失去關節,他的臉有淡紅斑點,耳朵浮踵與變形。」1892年7月8日:「和禮德醫生去洲裡(今蘆洲),看到幾位痲瘋病患,其中有個十歲的男孩,情況很糟,他的祖父也是痲瘋病患。他們說,當其中一個死時,三天都沒有點火,以免煙會散布疾病。」本書每一位作者也都企圖與清代、戰後做聯結,但限於資料,有時並不能如願,但我知道作者群已竭盡所能。
本書的另一特色,是考訂清代就已存在的社會問題,在日治後因引進日本內地的法令,而使某一邊緣人有了清楚的定義及新的名辭。如浮浪者是不是等同於羅漢腳、鱸鰻?在狹義來說應該是,但就法律定義對象而言,則不只是無業遊民,也包括有犯罪之虞的危險人物,產生一個「浮浪者」的新名詞,訂有〈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可施以強制移住與勞動。又如以「不良少年」取代了「惡少」,並給予十四歲以下、有可能成為鱸鰻者之定義。
本書第三個特點是,不只敘述外地台灣,也敘述日本內地的情況。如討論精神病患的相關法規,作者即引了1900、1919 年日本發布《精神病者監護法》、《精神病院法》,而1936 年2 月起台灣也施行《精神病者監護法》、《精神病院法》,為包括朝鮮在內的其他外地所沒有的現象。作者在此基礎上再探討台灣精神病院的角色,就不至於失焦。又如上面所論及的不良少年,作者也描述了日本的不良少年,和台灣的不良少年兩相比對之下,就顯出台灣人不良少年的行為特徵是「好賭喜食」,相對於日本不良少年的「嗜酒逐色」,可見兩地的民風不同。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使用了不少日記史料,如阿片吸食者引用《灌園先生日記》,談到林獻堂不顧妻子反對繳出阿片鑑札(執照);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談到去捕魚時,一面吸食阿片一邊享受溪畔之明月。又如受刑人的獄中生活引了蔣渭水和簡吉的獄中日記。本書有學術論文的深度,卻沒有其詰屈聱牙,清新易讀,除在寫作的手法上有一番考究外,也使用了許許多多平常不容易看得見的照片,更增加了可讀性。
這十位作者,有的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新秀,有的是取得碩士學位後任教中學或服務業界,有的在研究機構任職,有的在大學教書,還有的仍在學中。他們因興趣接近而能合作寫出一本面對一般讀者的書,作為階段性的業績,同時也向學界宣示日治台灣邊緣史的研究業已展開。
作為一個閱讀者,我有先睹為快的感覺;作為一個研究者,我驚艷於年輕作者觸角的寬廣;作為一個「前輩」,我佩服這些「小輩」的行動力。先是姃湲請我作序時,我未讀內容有點遲疑,看過之後我不再猶豫,謹作序以為推薦之意。
推薦序2
從邊緣發聲、走出邊緣∕王泰升(台大法律學院特聘教授、中研院台史所法律所合聘研究員)
這本書想要描述的是,在殖民現代性底下社會邊緣人的歷史。「邊緣」乃是相對於「中心」,出於一定的基準而被歸類為此。在日治台灣,現代型國家掌握了定義這個「基準」的權力。這個現代型國家,透過刑罰法規定義了誰是不為法內在正義所容許的「犯罪人」,再以各種行政法規定義出國家所欲管制的浮浪者、不良少年、性交易工作者、吸食鴉片者,乃至罹患精神病、漢生病等特定疾病的強制防治對象,並以維護社會安全為由,進行程度不一的隔離,施以不同內涵的教誨、感化、治療等,以及對行政法規所定義的「窮人」予以救助。換言之,上述各類群體,在以來自近代西方的現代性的評斷下,是屬於被主流社會所排斥、貶抑的邊緣人。這個國家同時也是,身為殖民統治者的日本人的國家,故自居為中心、作為評斷基準的,往往是出於日本人,而非在台漢人或原住民的特定文化觀念。
處於前揭具雙重外來性,亦即現代性與日本性的國家統治下,當時的台灣人社會對於在此所討論的邊緣人,存在著多元複雜的觀感。被隔離於監獄中的犯罪人不必然是出身社會底層或窮苦人家,也有濫施暴力、侵奪他人財產的中上層社會人士。國家法律所嚴厲制裁之觸犯「匪徒」罪者,除了有鄉里所尊敬的抗日志士外,倒也不乏真正的強盜。而通常依國家的犯罪即決程序被定罪、被關在警署留置場的賭博犯,一般人卻可能投以相當多同情的眼光。浮浪者取締制度之被國家濫用,應無疑問,但又如何看待家屬之主動要求以收容為浮浪者的方式,挽救兒子的「失敗人生」呢?日治後期之以「更生院」強制矯治鴉片吸食者,向為今之人們所稱頌,然對於有38.02%受過傳統書房教育的原吸食者而言,因遭隔離治療而改變的不僅是鴉片癮,還有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對於同樣是性交易從業者,只因沒向國家申請發給牌照,就變成警察追捕的對象,恐怕也有不少人不以為然吧。在一般民眾未能從社會階層、經濟結構,以及教育或醫療的本質進行思辨的情形下,可能有很多人是支持國家對各類邊緣人為監控的。
就像符合現代性者並不全然是好或壞,稱社會邊緣人也不意謂著給予善或惡的評價。但無論如何,社會邊緣人的歷史應該被看到。歷史的論述向來是由當權者、既得利益者所壟斷,但於今之民主時代,不問強勢、弱勢,都應該在歷史書寫以及歷史記憶上,佔有一席之地。本書作者群之提出「邊緣史」的概念,寓有為弱勢人民發聲之意,余亦深表贊同。其實,作為本書主要論述對象的日治時期,在戰後台灣數十年來獨尊中國國族主義的教育文化宰制下,早已成為徒有歷史經驗、卻欠缺歷史記憶的「邊緣史」。這一群年輕的研究者,選擇了這些原屬「邊緣中的邊緣」的議題,做了深入淺出的論述,已明白地宣示其不再是邊緣了。為此而提筆為序,亦深盼讀者們一起來支持這樣的論史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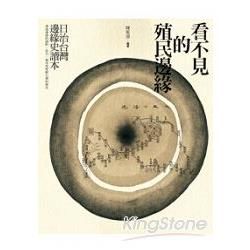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