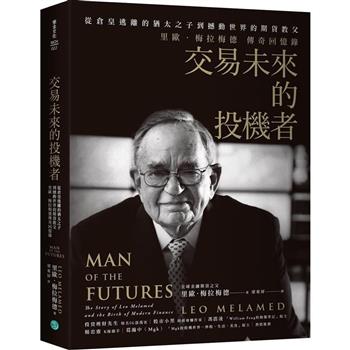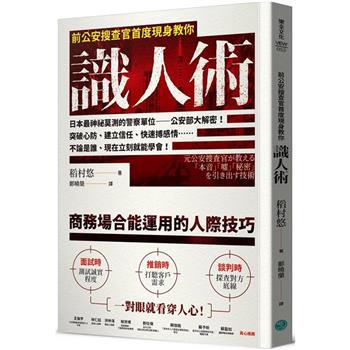導言
——從文化史、社會風俗到生活
一
在中國,「文化」一詞,最早可溯源自《易經》賁卦所說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種「人文」教化的意涵,到了近代開始出現轉變。19世紀末以後,西方意義的「文化」(culture),大量出現在文史學界的論著中,而其背景與中西文化交流愈益緊密離不開關係。
20世紀初,透過一批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的學生的譯述,許多文化史著作被陸續介紹進中國,其中日本的中國文化史論著,如中西牛郎(1859-1930)的《支那文明史論》、田口卯吉(1855-1905)的《中國文明小史》、白河次郎(1875-1915)的《支那文明史》等,其譯本均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或之前出版。而從20世紀初到中葉的50年間,中國史學界有關中國文化史的幾十部著作,大部分的歷史觀深受歐美、特別是日本文化史家的社會達爾文進化論、地理環境決定論、種族決定論、心理因素決定論等觀點的影響。
關於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梁啟超(1873-1929)無疑是一個開拓者。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在《新史學》就指出:「中國數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為此,他將史學重新定義:「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民國十年秋,他應聘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印有講義《中國文化史稿》,雖然內容「只能被看作歷史編纂學史的引言」,但卻是「中國高等學校關於這門學科的首出課程和首出教材」。或許他自己也感到名實不副,所以在正式出版時,改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不過,對於文化的進化論,他後來有所修正。民國十一年十二月,梁啟超接受南京金陵大學的邀請,演講〈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對文化史研究的歸納法、因果分析法和進化觀提出質疑,而開始傾向循環論。稍後,梁啟超又計畫撰寫多卷本的中國文化史,這一構想部分呈現在民國十四年於清華大學開課的講稿《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中。
20世紀初以來,最早以「文化史」為題的著作,歷來均認為是民國三年林傳甲在上海科學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史》。晚近有學者考證,此一說法純屬誤傳。林傳甲(1877-1922)的著作中,只有《中國文學史》而無《中國文化史》,而且《中國文學史》出版於光緒三十年(1904)。因此,若捨去梁啟超的《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不論,最早以「文化史」命名的專著,應屬顧康伯的《中國文化史》。顧康伯的《中國文化史》,係因在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任教之需所編,起稿於民國十年夏,完成於十二年秋,民國十四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他在〈自序〉中提到:「歷史云者,所以考究過去時代人類生活之狀況,而明其進化之階級,俾學者於國家、於民族、於社會,知有所以改進也。換言之,歷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其受到進化論影響的痕跡。
但若就編寫先後而論,柳詒徵(1880-1956)的《中國文化史》無疑在顧康伯之前。柳書的初稿,作於民國八年至十年間,原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授課的講義,隨編隨印,發給學生,「其後雖微有修改,亦迄民國十五年為止」。該書內容,民國十四年至十七年,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後來並出版合訂本。民國十七年,中央大學又出版排印本。民國二十一年,在南京鍾山書局正式印行。民國三十六年,上海正中書局將其收入大學用書,重新刊印。柳詒徵在書中嘗言:
世恒病吾國史書,為皇帝家譜,不能表示民族社會變遷進步之狀況。實者民族社會之史料,觸處皆是,徒以浩穰無紀,讀者不能博觀而約取,遂疑吾國所謂史者,不過如坊肆《綱鑑》之類,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舉凡數學、文藝、社會、風俗,以至經濟、生活、物產、建築、圖書、雕刻之類,舉無可稽。吾書欲袪此惑,故於帝王朝代國家戰伐多從刪略,唯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廣搜而列舉之。(見頁9)
正如學者所指陳,柳詒徵反對毫無止境的疑古,而認為必須廣蒐史料加以分析,表現出明顯的信古傾向,而從書中內容也可以看出強烈的民族主義。他還認為:「歷史現象,變化繁賾,有退化者,有進步者,有蟬嫣不絕者,有中斷或突興者,固不可以一概而論也。」這是一種進化與倒退並存的文化史觀。該書自問世以後,流傳與影響頗大,胡適(1891-1962)雖指摘此書有許多疵漏,但也認為「柳先生的書,可算是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而梁漱溟(1893-1988)也是在讀了柳著《中國文化史》後,「深受啟迪,從而有《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出版」。
當時,在學校講授中國文化史者甚多,有些講義並未出版,呂思勉(1884-1957)就是其中之一。民國十八年,他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講授中國文化史,現存《中國文化史六講》就是上課的底稿。他在〈序〉裡指出:「文化者,人類理性之成績也。」特別標榜「理性」的文化,這點頗值得注意。該課程原定分為二十講,現存講稿僅前面六講。
另外,陳國強的《物觀中國文化史》,民國二十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作者在〈導言〉中強調:文化「是人類依其物質生活條件為基礎而創造、而展開之精神生產的成果之總和」;故書中「在敍述各時代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注意說明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生產技術的發展階段,使讀者明瞭這兩者間的適應關係。」同年,楊東蓀主編的《本國文化史大綱》,由北新書局出版,他在〈序言〉提到全書的宗旨乃是「用經濟的解釋,以闡明一事實之前因後果與利病得失,以及諸事實間之前後相因的關聯。」
陳登原(1900-1975)所撰的《中國文化史》,則在民國二十四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他撰寫此書的動機,是覺得「某氏之書于心未愜」,所指乃是他就讀東南大學期間(1922-1926)的歷史老師柳詒徵所寫的《中國文化史》。陳登原在其書中明確提出現代意義的文化史理論,〈卷首‧敘意〉分別以「中國文化史之意義」、「中國文化史資料論」、「治中國文化史者的態度」、「何為治中國文化史」為題,探討文化史的核心概念、對資料的處理方法、文化史研究的預設理論,以及寫作文化史的目的等問題。陳登原提出其治中國文化史的見解有三,即:「因果的見解」、「進步的見解」、「影響的見解」,這是他文化史理論的基石,涉及文化發生、發展、本質等根本問題。這些見解並非他所獨創,其理論原型是民國一、二十年代進入中國學術界的巴斯典(Adolph Bastian, 1826-1905)、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以及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1884-1942)的系統論和文化整體觀。陳著除了理論性較強之外,內容也較能感動人,其重要原因就在於大量引用以私人生活和個體經驗為基礎的「私人敘述」(private narrative)文本。有學者曾給予此書這樣的評價:「就整體的學術地位及影響而論,陳登原或遜於柳詒徵。但若比較兩人的同題著作《中國文化史》,陳著成就並不在柳著之下,在體系的完整及論述的精當方面,還要勝出一籌。」又言:「綜合觀之,相較於柳著《中國文化史》,陳著無論是文本形式還是思維路數,都更具備現代學術的品格。」
民國二十五年,王德華編著的《中國文化史略》,由南京正中書局出版。王德華係蕭一山(1902-1978)在北平的受業弟子,蕭一山在序上指出此書有三大特點:一為發揮民族精神,一為闡述大一統之主義,一為發揚士人之正氣。實際上,以文化史振奮民族精神,是民國二十至三十年代相當多學者研究文化史的現實目的,柳詒徵、陳登原與陳安仁也不外於此。
陳安仁的《中國近世文化史》,是在中山大學史學系大三文化史課程的講義,民國二十四年整理,次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二十六年又編撰《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次年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印行。民國三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兩書合編,以《中國文化史》為名出版。他認為從歷史的進程來觀察人類的文化史,大概有三大範疇:(1)物質和心理的因子,即自然與物質的環境。(2)生理與心理的因子,即人類的欲望、思想與意見。(3)社會和歷史的因子,即經濟、政治、法律、風習、文藝、宗教的社會意識內容。他也意識到文化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互相依存,相互影響而不可偏廢。而其著書的史觀,明顯受到進化論的影響:「進化論旨,炯照於世,不特為科學界一種思想,而其範圍則能周括宇宙萬種之事理」,文化「不能逃出於進化範圍之外」。根據進化論,陳安仁提出他的文化演進史觀:「文化是有機進化和社會進化二者的產物」;進而歸結文化的基本動因,是為了求生存,並吸納「地理環境說」、「種族生物說」、「心理偶然模仿說」、「習慣環境說」、「本能習慣環境說」及「心理社會說」等理論,多方面探討影響、制約文化發展的因素;且秉持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等的文化進化階段論,指出文化是多元曲線發展,而不是單線直進的。另外,他受到文化傳播理論的影響,概括文化變遷的方式為「發明」、「傳播」、「吸收融化」三種。而文化演進的趨勢是「向上」的,最後的歸宿是各國的文化,均向世界人類最高的文化標準——大同的目的而邁進。
在抗戰前後,王雲五(1888-1979)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也值得一提。早在民國十二年,梁啟超在《國學季刊》上就提出整理中國文化史的方法有三,即索引式、結帳式與專史式。王雲五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所採取的就是專史式。他在〈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一文中,強調中國文化史分科式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對浩瀚的中國文化史史料,採取「綜合方式」加以整理研究極為困難,而各別專家就其所長,「擔任一專科史料之整理,其結果自較良好」。《中國文化史叢書》就採用這種方式,「分之為各科之專史,合之則為文化之全史」。這一叢書原計畫出版80種,後因戰亂,僅出版41種。即使如此,已經開創分專題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先河。其中,許多著作乃該領域開創性的專著,如陳登原的《中國田賦史》、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姚明達的《中國目錄學史》、鄧雲特的《中國救荒史》、胡樸安的《中國訓詁學史》、王庸的《中國地理學史》等。因此,有學者曾將這套書與王雲五主編的其他三種叢書——《萬有文庫》、《大學叢書》、《叢書集成》,並列為商務印書館影響近世文化的四大叢書。另也有學者說: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間,王雲五與傅緯平編輯的《中國文化史叢書》,是「中國文化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頗有意義的展示」。
民國三十年,錢穆(1895-1990)在四川成都撰寫《中國文化史導論》,部分內容曾在張其昀(1901-1985)等人創辦的《思想與時代》雜誌上連載。抗戰後,該書於民國三十七年由正中書局出版。錢穆在〈弁言〉中指出:「『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羣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羣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又言:「文化可以產生文明來,文明卻不一定能產生文化來。」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提到衝擊與反應的文化歷史觀:「文化必有刺激,猶如人身必賴滋養。人身非滋養則不能生長,文化非刺激則不能持續而發展。」錢穆坦承近代中國確實有許多問題,但正如余英時所言:
(錢先生認為)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中國文化自不能不進行調整與更新,但是調整與更新的動力必須來自中國文化系統的內部。易言之,此文化系統將因吸收外來的新因子而變化,卻不能為另一系統(西方)所完全取代。他稱這種變化為「更生之變」:「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徒於外面為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
錢穆對於五四以來思想界心慕西方、極端反傳統的思潮並無好感,而認為醫治近代中國文化的種種病痛,絕非與傳統決裂所能辦到。正因為他強烈的民族文化史觀,故學者曾經指出:抗戰以降,錢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以昂揚民族精神為主要內容,對於培養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的向心力,重鑄新的民族精神,確實有相當大的貢獻。
抗戰期間,陳竺同(1893-1955)任教於廣西桂林師範學院,其《中國文化史畧》撰成於民國三十二年,所論內容起自史前時代,迄於兩漢。他在第四章〈餘論〉曾說:「文化依拉丁語(Ku’tura)乃是耕作土地的意思,逐漸由這種勞動的成果,而完成人類超越自然的一切努力的成果。工具、原料,交易的技術,以及思想、藝術、習慣、政治,一切都是文化構成的要素。總之,文化進程是實際生活的各部門的進程。」其內容最大的特色,是以工具與生產力作為分析的主軸。
不可諱言,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界的確是百家爭鳴,而中國文化史的著作推陳出新,臻於空前繁榮之境地。但1950-70年代,中國大陸因為特定的因素,造成中國文化史研究的蕭條。1980年代以後(特別是1984年以後),「文化史研究猶如潛流奔突而出」,大量關於文化史的叢書、專著與譯著紛紛出版,使沉寂30年之久的文化史研究局面一轉,呈現出另一波高潮。而在臺灣,受到西方新文化史思潮的影響,1970年代以後,文化史的研究頗有異軍突起之勢。
二
談到風俗,班固(32-92)在《漢書》卷28下〈地理志〉序曾說:「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由此可見,風俗與教化息息相關,故士大夫將風俗賦予道德意義,並據此對社會風俗進行針砭,進而推動移風易俗。曾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意義的「風俗」,可說是美國社會學家薩姆納(W. G. Sumner, 1840-1910)所提mores和folkway的綜合體。薩姆納將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中,基於生活所需、周而復始所產生的行為,所演化成為群體習慣的內容,稱之為folkway。人類社群在無意識中,基於社會「有益」的考量下,對folkway進行選擇與調整的則是mores。而在mores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是思想觀念,透過mores建構的時代精神,所反映的則是那個時代的處世哲學。
中國幅員廣闊,山川地形各殊,氣候差異亦大,生活條件各不相同,因此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早在漢代,就有「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之說(《漢書》卷72〈王吉傳〉)。明人王士性(1547-1598)在《廣志繹》中,對各地社會風氣也有不錯的橫向比較。他對江南蘇州的看法是:
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倣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贋不辨。又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其賞識品第本精,故物莫能違。(卷2〈兩都〉)
而對浙江風俗的評論是:「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鮮衣怒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東俗敦樸,人性儉嗇椎魯,尚古淳風,重節概,鮮富商大賈。」江西的風俗則「力本務嗇,其性習勤儉而安簡樸,蓋為齒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卷4〈江南四省〉)至於華北,河南的風俗「淳厚質直,有古風,雖一時好剛,而可以義感。語言少有詭詐,一斥破之,則愧汗而不敢強辯。」山東的社會風氣,「士大夫恭儉而少干謁,茅茨土階,晏如也,即公卿家,或門或堂,必有草房數楹。斯其為鄒、魯之風。」對於山西,他的觀察是:「晉中俗儉樸,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卷3〈江北四省〉)實際上,這種社會風俗的地域性差異,存在於各朝各代。
在20世紀上半葉,正值文化史開始流行的同時,出現了若干風俗史與社會風俗史的著作。其中,張亮采(1870-?)的《中國風俗史》,撰成於宣統二年(1910),次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張氏自言「夙有改良風俗之志,未得猝遂,乃以考察為之權輿」,該書〈序例〉提到:「前人觀察風俗,其眼光所注射,不外奢儉、勞逸、貞淫、忠孝、廉節、信實、仁讓等方面,而尤以去奢崇儉,教忠教孝,為改良風俗之先著」,「是書亦存此意,故於各章列飲食、衣服、婚娶、喪葬等條,所以覘奢儉也;列忠義、名節、風節、廉恥等條,所以勵忠節也。」除此之外,詩歌、巫覡、言語等,也都在討論之列。全書分為四編,第一編為渾樸時代,由先民至西周;第二編為駁雜時代,自春秋至漢末;第三編為淫靡時代,由魏晉至五代;第四編為由浮靡而趨敦樸時代,起自宋代,迄至明代。整體而言,禮樂教化的史觀頗為明顯。有學者指出:張氏「以民族國家的架構,用風俗為脈絡,將中國歷史貫穿一線,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而隨之西學東漸日盛,中國的社會架構與社會風潮劇變,傳統的風俗觀迅速解體重構,之後的風俗概念已經呈現出不同的內涵。此後出現的風俗研究的著述自然面目大改。張氏的風俗史後無來者,遂成絕響。」
民國初年,瞿宣穎(1894-1973)在讀史之餘,將有關制度、風俗的材料錄下,累積十餘年,後來加以整理,於民國二十五年輯成《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內容包括:衣飾、飲食、建築、居處、器物、經濟、民族、信仰、傳說、婚姻制度、喪紀、社會制度、娛樂、社交、交通、儀物、藝術、職業、語文、雜風俗制度。他在〈題語〉中還說:「更假歲月,當仿容齋,續成五筆,補其闕失」,但不久抗戰爆發,願望未能遂成。民國二十六年,顧頡剛(1893-1980)為此書作序,在序中提到:「史家多於歷史諸現象中特提經濟一觀點,其說風靡一世,社會史遂有取政治史而代之趨勢。」然而,「今之講通史者,所言盡於政治大勢,罕有從事社會狀況者,蓋普通史事憑藉甚富,而社會史則上乏師承,且材料缺乏,避難就易,人之恆情,無足責也。」即使如此,「社會史雖不為前人所措意,而零碎之材料則散見古今記載中,茍見心鉤索,固未嘗不可得也。」瞿氏此書,「取材博而用力深,上自民族經濟,下至衣食住行,及夫一物一事之形態,一時一地之風尚,莫不備焉;此可謂極搜集史料之能事矣。」學者若能據此加以系統化,「中國社會史之著作將造端於是,繼是而作通史者亦將知政治之外有重要者在,而擴大其眼光於全民族之生活矣。」
另外,尚秉和(1870-1950)也編有《歷代社會狀況史》,甲編20卷,以鉛印線裝刊行,出版時間不明。抗戰前夕,又將甲編與乙編24卷合訂,書名易為《歷代社會風俗事物攷》。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於顛沛流離情況下,在長沙出版該書。其弟子杜琨在民國二十六年所撰的〈敘〉中指出:「社會之推移,風俗之演變,一事一物之沿革,可以攷人羣之進化,防弊害於未然,其事雖小,其所關則甚大」,故此書之編著,「真讀古書之管鑰,袪疑惑之蓍龜,而究研古社會狀況之淵海也」。該敘又提到:「自南宋諸儒,倡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而家庭之和樂無。自明初方胡諸儒,揚嚴氣正性之波,而官吏狎妓之風寂,而文化因以低落矣。文化既低,道德亦因以日降,至末世遂生反響,而越軌之事,層出而不窮。此先生所尤痛恨腐儒之說之誤我人羣,蠹我社會,致使有今日悲慘之風俗也。」就此而言,尚氏此書不專重在考史,亦在於以史為鑑。
有趣的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化史著作中,不乏對於「社會風氣」的討論。張亮采的《中國風俗史》,已經開啟這一先河,如書中論及明代,前面幾節的標題為:仕宦驕橫、才士傲誕、勢豪虐民、官民交通、奸豪胥役與詞訟,其餘幾節則是:結社、風節、朋黨、忠義、衣服、喪葬、淫祀與巫覡、奴婢、賭博、拳搏。相較而言,前面幾節所論,實較後面精采許多。
民國二十四年,陳安仁所撰《中國近世文化史》,各章也特別立一節,分別談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的社會風習。談到明代的風俗習慣,包括衣服、婚姻、死喪、巫覡、賭博、拳搏、養奴。論清代的社會風習,則包括婚姻、死喪、俗尚、養奴、賭博、食鴉片。其後,《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的體例相當,討論各朝代時,也有「社會風習」一款。與張亮采的《中國風俗史》相比,陳安仁二書所謂的「社會風習」,反而更接近於「民俗史」的範疇。
學術的研究離不開時代氣氛,特定的論題常與內部的環境因素相聯繫。民國以來對「社會風氣」的討論,雖可往上追溯其根源,但社會風氣的日漸奢侈,於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1887-1975)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或許也是一個重要背景。民國二十五年,王德華的《中國文化史略‧敘例》提到:「轉移中國社會風氣之『新生活運動』」,乃是晚近「中國最重要之歷史」之一,因此在書中特別敘及,故《中國文化史略》第四編〈社會史〉的第三十二章(即最後一章),就專列「社會風氣」加以討論,內容起自古史傳說時代,迄於新生活運動。他在「最近社會風氣與新生活運動」一節提到:「晚近以來,社會風氣益壞,上下人士,莫不精神萎靡昏懦,行為卑鄙,虛偽散漫,思想邪亂,生活奢侈,若全國民族之生命,即將滅亡者然。」而新生活運動之提出,可以「以最簡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國民不合時代及不適應環境之習性,而建設一以禮義廉恥為基礎之合理的生活。」
抗戰以後,中國各地受到空前的破壞,社會奢侈不再是學術界討論的焦點。至1950年代,不少學者注意到中國歷史上對於奢靡的看法,郭沫若(1892-1978)〈侈靡篇的研究〉即是其一。在這之後,楊聯陞(1914-1990)也撰文討論《管子‧侈靡篇》,文末並附錄陸楫(1515-1552)的〈奢靡論〉。另外,傅衣凌(1911-1988)在《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一書中,也提到陸楫關於奢侈的態度,並對照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的《蜜蜂寓言》。
1970年代末,社會風氣的討論逐漸深化。就明清史而言,森正夫對於明末社會秩序變動的討論,無疑最具有開創性。而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與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及「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風氣變遷,激發學者對於過往歷史進行考察,明清時期尤其成為關注的重點所在。截至目前為止,中國、臺灣、日本等地學者,關於明清社會風氣變遷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
以臺灣而言,觸及這方面議題的學者,計有徐泓、林麗月、陳國棟等人。在數量上雖然比不上大陸學者,但就研究取徑而言,還是較為多元。徐泓最早的三篇文章,分別以江浙、華北五省為對象,論述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從明初社會的「儉僕淳厚」、「貴賤有等」,至明代中葉「渾厚之風少衰」,明代後期則「華侈相高」、「僭越違式」。在此情況下,除了生活方式越來越奢侈之外,向來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觀念亦出現變化,使更多人投入商品經濟活動,反過來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有陸楫的〈奢靡論〉出現,而商人財富的增加,也使貴賤的界線出現鬆動。相對之下,在金錢與財富當令之下,政治風氣也隨之惡化,《明史‧循吏列傳》所收循吏,正反映了這個變化的過程。他關心的主軸,仍然是社會經濟史與政治史上吏治的範疇,而非晚近的社會文化史面向。
另一方面,林麗月與筆者均曾針對明代的禁奢令加以分析。此外,林麗月長期關注晚明的「崇奢」思想與「反禁奢論」(特別是陸楫的〈奢靡論〉),探討晚明商品經濟發展、社會風氣變遷與經濟思想之間的互動關係。陳國棟則以清高宗的侈靡論對比陸楫的〈奢靡論〉,並從經濟學的角度,舉曼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進行對話。另外,他又探討明代經濟發展、奢侈風氣,與傳統手工業發展之間的正相關性。要之,奢侈雖為「道德之惡」,但就工商業的發展而言,卻是「必要之惡」。
三
「生活」一詞,最早可上溯至先秦典籍,如《文子》卷上〈道德〉云:「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卷下〈微明〉又提到:「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而《孟子》卷13〈盡心〉亦云:「民非水火不生活。」實際上,普通百姓的需求非常簡單,能滿足最基本的溫飽,也就可以了。但富裕者的欲望無窮,生活內容也複雜得多。而生活方式除了牽涉到階層之外,也可能因地域、種族、宗教等因素而有差別。
自先秦以來,月令行事與農業時序的記載代代相承。先秦時期,《禮記》中有〈夏小正〉、〈月令〉,《呂氏春秋》有〈十二紀〉。西漢《淮南子》則有〈時則訓〉,東漢有崔寔(103-170)的《四民月令》。而就歲時風俗而言,南朝梁朝宗懍(501-565)所撰的《荊楚歲時記》,更成為後代論及風俗時常對照的指標。在此之後,唐至五代又有李淖《秦中歲時記》、佚名《輦下歲時記》、韓鄂《四時纂要》等,宋代有呂原明的《歲時雜記》、陳元靚(1137-1181)的《歲時廣記》、周密(1232-1298)的《乾淳歲時記》。明代有陸啟浤的《北京歲華記》,清代有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顧祿的《清嘉錄》、富察敦崇(?-1921)的《燕京歲時記》。
近世以降,地方志中記載的大量節序內容,則呈現各地庶民生活的諸多面貌。舉例來說,庶民娛樂就相當多樣,如明代嘉靖《尉氏縣志》記載:「闤闠市井,每以賭錢爲事,賽神相聚之日尤衆,有博弈者,有射注者,有闘鷄者,有闘䳺鶉者,有闘促織者,有闘紙牌者,傾家覆產無悔,亦每觸禁被刑。」(卷1〈風俗類‧風俗〉)這一記載雖帶有負面批判,但卻顯見百姓日常生活的某一面向。
實際上,明代各地都有鬥禽類與昆蟲的風俗,如謝肇淛(1567-1624)記載長江以北有鬥鵪鶉之俗,福建莆田則喜歡鬥魚(《五雜組》卷9〈物部一〉)。袁宏道(1568-1610)則說「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又在北京西山見到兒童鬥螞蟻,且提到友人公安龔散木能夠鬥蜘蛛(《袁中郎全集》卷16)。據說明宣宗喜鬥促織,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1388-1442)進貢千隻,一時有「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的諺語,直到萬曆年間仍在流傳。萬曆末年,「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萬曆野獲編》卷24〈技藝‧鬭物〉)。天啟年間,姚旅則說:「鬬鴨之風,今絕未聞。鬬鵝亦惟見於漳州,鵝之佳者,可直五千。」又云:「鬬鵪鶉之風,秦中爲盛」;「鬬促織之風,今惟燕京爲盛。」(《露書》卷9〈風篇中〉)
至於鬥雞,早在先秦已經存在,其後歷久不衰。明末士人張岱(1597-1679)就好鬥雞,天啟二年(1622)曾設鬥雞社於紹興府山陰縣的龍山下,他養的鬥雞是常勝軍,打敗許多對手,讓他贏得不少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品。某日,閱讀野史,「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鬥雞而亡其國」,而他正好也是酉年酉月生,於是不再鬥雞(《陶庵夢憶》卷3〈鬥雞社〉)。其後不到二十年,明朝果然滅亡,但與他鬥雞似乎連不上關係。另外,袁宏道在家鄉山居時,鄰居蔣氏從北京經商返鄉,帶回一隻大雞,「燕地種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許,粗毛厲嘴」;另一鄰居金氏,也有一隻雞,但與巨雞相比,「止可五之一」。兩雞相鬥,本地的雞自然不敵(《袁中郎隨筆‧山居鬥雞記》)。由此可見,北京的雞在體格上要大於南方。崇禎十七年(1644),陸啟浤談到北京的鬥雞提到:
蟋蟀經霜後,懦不復勁,乃有鬪雞之戲。養雞家,經年喂飼,候其燥濕飢飽,不得休息。鬪有主家,名曰樁。滿身淋漓,鬪不倦,不曰負,鳴而出欄,則負。其名有「塞上霜」、「九觔黃」、「鐵爪藜」、「御府班」等號。(《北京歲華記‧八月雜事》)
袁宏道提到的北京巨雞,或許就是「九觔黃」。而與民間八月開始鬥雞不同的是,宮中是在十月。據劉若愚《酌中志》記載:「內臣貪婪成俗,是以性好賭博,既賴雞求勝,則必費重價,購好健鬭之雞,僱善養者,晝則調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雞。」而鬭雞之時,「須燃燈觀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更妙也」(卷20〈飲食好尚紀略〉)。秦元方《熹廟拾遺雜咏》也談到類似的風俗,但未言及月份:「宮人競為鬥鷄戲。屆期登埸,施五色幔于籠上,到場開籠,多者至三、四百。啄勝者,以綵繒結小毬,分纒頸上,入籠迎歸,所獲珠翠不啻百金。」
以上所述,僅是隨便舉例。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關於生活史的材料並不算少,只是分布極為零散。而這些材料在瞿宣穎《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攷》中所在多有。實際上,生活史本就包含在社會史之中,故社會史著作中,多半言及歷史上中國人生活史的內容。在20世紀上半葉,日本關於「生活史」的著作甚多,但就如顧頡剛在《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序所言,中國社會史在抗戰前後猶未興盛,故生活史的研究不多,陳東原(1902-1978)的《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算是少數的作品之一。但陳東原此書的「社會史」成分頗濃,「生活史」的內涵相對反而被沖淡。另外,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書店,1934),也是探討特定人群生活狀況史的一本專著,儘管未標以「生活史」的書名。另外,在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清華大學史學系學生吳晗(1909-1969),在《文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金瓶梅的著者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其中亦略及晚明的社會生活樣貌。
長期以來,學者多半認為生活史的重要性不高,其地位也「妾身未明」。1980年代,馮爾康提出:社會史是研究歷史上人類社會生活的運動體系,以人類的群體生活與生活方式為研究對象,以社會結構、社會組織、人口、社區、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習俗為研究範疇,揭示其本身在歷史上的發展變化及其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而其研究的對象包括:氏族、階級、等級、階層、宗族、家庭、民族、宗教、人口及其結構、職業與就業、衣食住行的習尚、婚喪、娛樂、社交、時令風俗等方面的社會生活。喬志強(1928-1998)則認為:中國社會史應以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為研究對象,主要可分為三方面:(1)社會構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等最基本的社會元素與細胞;(2)社會生活,包括物質生活(衣食住行用的方式),精神生活(價值觀念、倫理觀念、信仰結構等)和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血緣關係及其他人際關係),三者共同組成社會生活主要的網絡式內容;(3)社會職能,包括教育與贍養,社會控制與調節,以及社會病態的防治等。而在民國八十一年,杜正勝也提出「新社會史」的概念,認為其研究領域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或範疇):「一是物質的,二是社會的,三是精神的,這三者皆脫離不了人群,亦即是個人與社會,新社會史就是要對這三者做整體的探討」。
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已經涉及生活史相關的議題,「社會生活史」隱然呼之欲出。且隨著研究取向的轉變,1980年代末以後,以生活史為題的論著也越來越多。而如何在社會史的架構下,呈現生活史的內涵與圖像,成為許多學者所關注的問題。
以臺灣的明清史研究而言,吳智和(1947-2012)是生活史較早的提倡者之一,特別是其對飲茶風尚的探討。他曾針對清初《儒林外史》的內容,歸納茶館的社會功能大約有四:排難解紛、安頓流寓、同行聚會、閒坐敘舊。後來,王鴻泰對此加以衍伸,並指出晚明茶館的幾種類型,一種是「日不能數」的精緻「茶藝」館,客人主要以文士為主;一種是「飲客雲集」大眾化茶館,由於消費額低,故成為眾人皆可前往的一個社交場所,與前此以文士為主的「茶藝」館成為明顯對比。晚近,吳智和所指導的博、碩士生,以生活史為題者亦不乏其人。
在民國八十年以降,其他學者也多涉及這些範疇,並有幾部論文合集出版。就討論的主題而言,林麗月研究晚明服飾流行風尚,與明代的網巾;李孝悌則考察士人的逸樂與宗教生活;賴惠敏研究清乾隆年間北京的皮貨消費,與江南的舶來品流行風尚。另外,王鴻泰研究園林、娼妓、文人文化、城市空間;巫仁恕探討服飾、轎子、旅遊、家具、飲食、園林及婦女消費等;陳熙遠考察節慶與麻將。筆者也有若干論文與生活史相關,茲不贅述。相關研究,王鴻泰有精采的研究回顧。
四
1990年代初,葛兆光曾說:「現在再談『文化史』,不免有明日黃花的惆悵。有人曾引萊弗(James Lever)定律說,『穿著當下流行的服飾:漂亮!穿一年前流行的服飾:邋遢!穿十前流行的服飾:醜陋!』文化在前五年的『熱』勁兒,把如今再談『文化史』的人置於『邋遢』與『醜陋』之間的尷尬境地。彷彿執迷不悟仍在歌廳彈奏前朝曲一樣,恐怕在流行樂聲中只能落個『無人喝采』的結局。」今日再看這段話,是否談「文化史」的人將被置於「醜陋」之後?或許不然,因為文化史似乎又穿上了「新裝」——文化史與社會史的結合,為這十多年的研究取向帶來了新的面貌。
而在生活史方面,或許有些學者覺得社會生活或日常生活的研究是雞零狗碎,但透過對特定時代、個別事物,結合社會、經濟、文化,甚至是制度等層面,對生活的細部內容進行考察,應該還是值得嘗試的。截至目前為止,明清日常生活、物質文化與消費行為方面的研究是方興未艾。
文化史與生活史的範圍包羅萬象,本書所收論著自然難以全部涵蓋,但就各篇所涉及者而言,已經包括日常生活、宗教科儀、京城社會、士人文化、城市空間與城市化、商標與廣告、舶來品等內容。
人類文明發展的初期,物質生活莫不以食、衣、住為中心;其後,才發展出交通工具及其他各種與生活有關的物質文化。許倬雲〈中國古代平民生活:食物、居住、衣著、歲時行事及生命儀禮〉一文,所討論的主軸即環繞這一過程,考察舊石器時代以來庶民生活的諸多面向。另外,正如俗語云:「民以食為天」,王利華〈漢唐飲食與生態環境〉所討論的,就屬於飲食史的領域。文中主要探討漢唐之際飲食結構的轉變,如主食升降、蔬果種植、家禽與家畜養殖、食料加工與醃漬、調味品與烹飪技術,以及飲茶風氣的出現。
以上兩篇專論,內容屬於日常生活史的範疇,另有一文屬於宗教信仰方面。葛兆光所撰〈由俗而聖——中古道教科儀的宗教化〉,接續胡適、楊聯陞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討論中古時期道教諸派對其科儀的清整,對於被詬病的儀式和活動(如塗炭齋、過度儀、廚會等)加以修正與革除,使其科儀從世俗性、生活化轉向神聖性、「超越化」的宗教化,最終使道教科儀有嚴格的規矩可循,並為後世留下有所依據的文本。
此外,有三篇論文涉及士大夫文化或士人文化。甘懷真〈漢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一文,從其提出的「京城社會」概念看來,似乎屬於城市史的範疇,而實際上更多是在論述士大夫的社交圈,與士大夫文化在形塑「京城社會」的角色,以及士大夫如何透過「京城社會」的社交圈以自我高尚化和取得自我認同。另外,陳雯怡〈元代書院與士人文化〉一文,從比較宋元兩代的書院入手,考察書院與士人文化的轉變,並討論書院與儒戶政策、理學正統化、官學化的關係。王鴻泰〈明清的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一文,則綜括其近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呈現明清士人活動的圖像,包括結社、社交、狎遊、文藝活動、生活經營等面向。
費絲言〈明清的城市空間與城市化研究〉一文,則回顧近數十年的明清城市史研究,檢視馬克思(Karl H. Marx, 1818-1883)「階級衝突」觀點、日本學界「官」「紳」「民」互動模式與「共同體」/「地域社會」論、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理性城市社會與工商自治團體」說、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運用「中地理論」的研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的「城鄉連續性」理論等研究取向,最後認為:在對中西城市發展作整體批判之前,應先釐清城市化在各朝代之間的差異與影響。
巫仁恕的〈明清的廣告文化與城市消費風尚〉,則考察明清工商業為宣傳購物知識和促進消費所產生的廣告文化,包括:(1)商標、品牌與字號;(2)招幌與楹聯;(3)社交宣傳;(4)節慶賽會展示。最後,論及士大夫在廣告文化中的角色與促銷作用。筆者〈晚明以來的西洋鏡與視覺感官的開發〉一文,則討論晚明以降所傳入的西洋鏡,如望遠鏡、顯微鏡、西洋景、幻燈影戲、攝影術和電光影戲,與中國社會之間的互動,及民眾視覺感官的延伸與開展。
本書所收論文共計九篇,均係原任主編李孝悌所邀,筆者銜接此一任務,處理後續的審查及編輯程序。由於學識與能力有限,以致延宕至今,對於賜稿的諸位先生實感深歉(包括已經撤稿的沈雪曼教授)。在編輯過程中,劉川豪、李振銘、李聲慶、顏瑞均、江豐兆諸君曾經給予協助,在此特別感謝。
邱仲麟
民國百年十一月於臺北東湖默齋,
翌年七月增補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王源泰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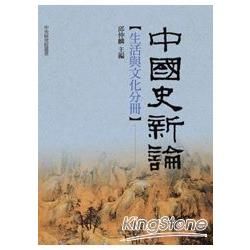 |
$ 465 ~ 585 | 中國史新論: 生活與文化分冊
作者:許倬雲/王利華/葛兆光/甘懷真/陳雯怡/王源泰/費絲言/巫仁恕/邱仲麟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7-25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
本書計收錄專論九篇,內容含蓋日常生活、宗教科儀、士人文化、城市空間、商標與廣告、舶來品等內容。全書從舊石器時代以來的庶民生活展開,論及食物、居住、衣著、歲時行事及生命儀禮等面向;其後則連接漢唐之際飲食結構的轉變,與飲茶風氣的出現。在物質生活之外,精神性的宗教信仰亦不可或缺,中古道教科儀從世俗性、生活化轉向神聖性的宗教化,就讓科儀有其嚴格的規矩可以遵循。漢代以降的士人文化,更是此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漢唐之間,士大夫透過「京城社會」的社交圈,尋求自我高尚化與自我認同。元代書院的發展,則與士人文化、官方的儒戶政策、理學的正統化和官學化,有著極深的關聯。明中葉以迄清初,士人的社交、狎遊、文藝活動、生活經營等面向,更存在「雅」、「俗」之間的辯證與互動。關於明清城市空間與城市化研究,則有一篇專論加以回顧。另外,明清的城市消費和廣告文化的關聯性,與士大夫在廣告促銷上的角色,書中亦有特別分析。而隨著全球化的展開,晚明以來陸續傳入的各種西洋鏡,對民眾視覺感官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本書討論的主題之一。
作者簡介:
邱仲麟
臺灣宜蘭人,1964年生。淡江大學歷史學學士(1988)、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1991)、博士(1997)。曾任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講師、副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副研究員。現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範疇為明清北京史、明清醫療史、明清社會史、明清生活文化史與明清環境史。
章節試閱
導言
——從文化史、社會風俗到生活
一
在中國,「文化」一詞,最早可溯源自《易經》賁卦所說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種「人文」教化的意涵,到了近代開始出現轉變。19世紀末以後,西方意義的「文化」(culture),大量出現在文史學界的論著中,而其背景與中西文化交流愈益緊密離不開關係。
20世紀初,透過一批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的學生的譯述,許多文化史著作被陸續介紹進中國,其中日本的中國文化史論著,如中西牛郎(1859-1930)的《支那文明史論》、田口卯吉(1855-1905)的《中國文明小史》、白河次郎(1875-1915)的《支那文明史...
——從文化史、社會風俗到生活
一
在中國,「文化」一詞,最早可溯源自《易經》賁卦所說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種「人文」教化的意涵,到了近代開始出現轉變。19世紀末以後,西方意義的「文化」(culture),大量出現在文史學界的論著中,而其背景與中西文化交流愈益緊密離不開關係。
20世紀初,透過一批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的學生的譯述,許多文化史著作被陸續介紹進中國,其中日本的中國文化史論著,如中西牛郎(1859-1930)的《支那文明史論》、田口卯吉(1855-1905)的《中國文明小史》、白河次郎(1875-1915)的《支那文明史...
»看全部
作者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
»看全部
目錄
《中國史新論》總序(王汎森)
導言 (邱仲麟)
許倬雲,中國古代平民生活——食物、居住、衣著、歲時行事及生命儀禮
一、前言
二、農耕
三、飲食
四、居住
五、衣著
六、歲時與生命行事
王利華,漢唐飲食與生態環境
一、飲食體系之地域分野及其自然基礎
二、食料結構之調整及其生態背景
三、造食技術和飲食結構與環境的關聯
四、簡短的結語3
葛兆光,由俗而聖——中古道教科儀的宗教化
引言:從胡適和楊聯陞的通信說起
...
導言 (邱仲麟)
許倬雲,中國古代平民生活——食物、居住、衣著、歲時行事及生命儀禮
一、前言
二、農耕
三、飲食
四、居住
五、衣著
六、歲時與生命行事
王利華,漢唐飲食與生態環境
一、飲食體系之地域分野及其自然基礎
二、食料結構之調整及其生態背景
三、造食技術和飲食結構與環境的關聯
四、簡短的結語3
葛兆光,由俗而聖——中古道教科儀的宗教化
引言:從胡適和楊聯陞的通信說起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許倬雲、王利華、葛兆光、甘懷真、陳雯怡、王源泰、費絲言、巫仁恕、邱仲麟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7-25 ISBN/ISSN:978986037165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64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