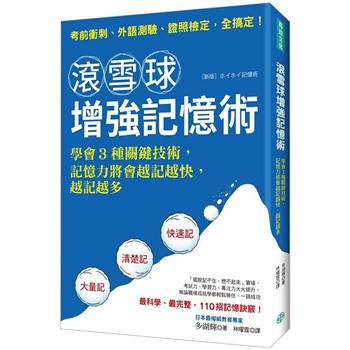一張破碎的面孔,一具破碎的軀體,一口緊閉的棺木,一禎裝在銀質相框裡的畢業照。懷裡揣著工程師文憑,文森卻前往探索事物的另一面。他不去理解自己的人生,或許,倒是理解了自己的死亡。遺體安置室裡空無人跡,菲利浦.拉里維沉默的坐著。古諾的〈萬福瑪利亞〉以微弱的音量播放著。他要求過要獨處。他並沒有在等待任何事或是任何人。他就待在那裡,只是待在那裡。
十三年來,悲傷並沒有離開過他。打從他兒子文森的死一直到現在。打從令他感到難以承受、確認屍體身分的那一刻起。沒有流一滴眼淚。只發出一聲難以形容的叫喊。
一個悲苦絕望的男子,以遠超過自己所有的力氣喊叫出聲。
一聲沒有終點的漸強音。
隨後,一位父親崩潰了。凝重且殘酷的沉默占據了停屍間。無語的年輕警員,下顎顫抖著,一動也沒動。出於對一位頹喪父親的尊重。等待很漫長。非常漫長。菲利浦.拉里維再度站起身來。他蒼白得毫無血色的臉上,那對呆滯的雙眼、空洞的目光,便是這些警員們所預料到的最後答案。一位父親認出了自己孩子可怕的殘骸。
在偏僻的樹林中,一輛車裡,一具毫無生氣的軀體。一把獵槍放在雙腿之間。一具臉部難以辨識的屍體。四散的肉塊。一位男子支離破碎的悲劇。文森的父親沒有流下一滴淚水,因為他還沒有理解。十三年來,菲利浦.拉里維沒有流一滴眼淚。他的妻子蘿珊則是哭得那麼頻繁,她猜想:如果眼淚沒有被哭出來,是會累積還是會乾涸。她望著丈夫的痛苦,心想他們的日子沒辦法再過下去了。菲利浦.拉里維提到文森時從來不用「自殺」這個詞。這個詞太殘酷、太真實了。只用婉轉的說法,比較溫和,沒那麼驚人。拉里維先生說文森出發探險去了,跟他那位在「無國界醫師組織」工作的外科醫生女兒蘿拉一樣。只是蘿拉會定期打電話來。至於文森呢,電話線路斷掉了。他在那麼遙遠的地方,以致於通訊在一個謎樣的漸弱音中減弱殆盡。拉里維先生有時候會脫口而出;他會說:「這件事我得跟文森談談」或是「我等文森回來的時候」。然後他望著她的妻子,後者則裝做什麼都沒聽見。
他全然不知所措。
那是在某個九月份,當時所有人都在談論天氣是那麼地濕熱。大家從來沒見過這種景象。人們會以為還在七月。現在臭氧層推翻了一切,我們不能指望月曆了。拉里維太太在黃楊樹的樹籬上灑著水,一面用手背擦拭著額頭上的汗。拉里維先生帶著某種讚賞望著他的房子。當初就是文森建議他買下一棟老房子的。「我們一起把它翻新。」他買下了房子,一個月之後,文森便偏離正道駛入了一座樹林,帶著那把祖父在過世前送給他的獵槍。他得到獵槍時才只有十一歲。
「這是用來獵小型獵物的,小子,用來獵鴨子,山鶉,野兔,」祖父莫里斯告訴他。
菲利浦當時嚴辭抗議。他反對武器,而且文森也絕對不可以操作它。他把獵槍收進地下室一個舊櫥櫃中,鎖上了兩道鎖。他把這把槍給忘了。有一天,文森問他什麼時候他們才會去獵小型獵物,他父親告訴他說他們沒有獵槍。
「我們有祖父的獵槍,」孩子提醒他道。
「我們沒有獵槍。」文森沒有執意問下去,而且從此再也沒有跟他父親提過打獵的事。他對獵槍失去了興趣,不過在他的腦袋中,祖父的這件遺贈品讓他確信自己再也不是個小孩子了。
菲利浦.拉里維翻新了文森的房子,他是這麼稱呼這棟房子的。用了十三年的時間。不是為了喜好,僅僅只是為了不要辜負兒子的期望。那是一件漫長又仔細的工作。他的肩頭上承載著文森無所不在的目光。他需要這樣的目光。那是對於好好完成的工作的一種評價、一種肯定。文森並沒有死去。
菲利浦當時辭去了工作。他的老闆拒絕了他的請辭。「我理解您的痛苦。」老闆當時一面讀著辭職信,一面對他說。菲利浦瞪著他,什麼話也沒說,他聽不見他在說的話。他輕手輕腳地關上門,便離開了,沒說再見也沒說永別了。他的老闆怎麼能夠理解這種連他自己都不理解的痛苦?蘿珊什麼話也沒說。她眼睛始終紅著。她當時便知道:從今以後,除了文森的死之外,不會再有別的了。
葬禮的第二天,文森最要好的朋友艾彌爾出現了,很不自在地站在門前。
「我必須跟你們談一談。」
「進來坐下吧。」菲利浦握著他的手對他說,然後領著他來到了廚房。艾彌爾在餐桌上坐了下來,一如他以往跟文森一起時總是會做的那樣,不過這次,他覺得自己好像侵犯了一項再也不屬於他的權利。拉里維太太準備了咖啡。她刻意不說話,以免自己又再度哭泣起來。她想到了這兩個孩子變成大人的那一天。在那個值得紀念的傍晚,文森告訴母親說艾彌爾是同性戀者。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蘿珊試探著問他。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這點不會改變,」他這麼說,讓她放下了心。
艾彌爾從他的手提箱裡拿出一個大信封袋,放在餐桌上。他打開信封,展示一份上頭用大寫字體標著「警察」字樣的文件。因為文森是在承保了一份壽險後的第二十六個月自殺的,所以他留給父母一筆三十萬元的理賠金額。「他要我在他死後把這份文件交給你們。」菲利浦禁不住去思索他的兒子在暗中鑄造了自己的離去。蘿珊覺得難以置信。她心想真有這種事嗎?在尋死之前先買下壽險的孩子。菲利浦原本拒絕要這筆錢。蘿珊對他表示,他們不可以違背兒子最後的願望。面對這樣的論調,他只好從命了。
菲利浦和蘿珊賣掉了他們位於郊區的平房。他們搬進文森的房子,已經有好多年了。菲利浦欣賞著他的房子。眼淚開始流下。他明白到自己正在為兒子的死亡哭泣。在十三年之後。
【第一章】
艾彌爾曾經再也睡不著了。惡夢破壞了他的夜。總是同樣的夢境。他被囚禁在一個房間,房間的牆壁和天花板像鉗子一般地收攏。猛然驚醒。氣喘吁吁,渾身是汗,他的樣子看起來像個剛跑完一場比賽的馬拉松選手。他掛著黑眼圈的雙眼,透露出令人筋疲力盡的夜夜煎熬。沒有任何一種花草茶、也沒有任何一種安眠藥能夠平息他的失眠。他再也睡不著了。睡意拋棄了他,宛若一個忘記回來的愛人。某一天,在文森過世很久之後,惡夢淡薄了。艾彌爾終於可以入睡了。無夢的漫漫長夜。只有無垠的空虛。
他經常回想起那痛苦的一年。所有那些夜晚,跟文森和其他人一起,他們回憶起決定命運的十二月六日那天所發生的事件。多少無眠的夜晚?喝乾了的空啤酒瓶,菸灰缸裡滿溢出來的菸屁股。艾彌爾的公寓裡瀰漫著一股小酒館的氣味。為什麼他們什麼也沒做?女生站左邊,男生站右邊。時間太短,無法制服一件如此殘暴的武器。迎上那個滿懷恨意與怒氣的目光,才不過幾秒鐘時間。那般危險的目光。當殺手命令他們離開教室時,為什麼他們就一聲不吭地服從了呢?那是學期末的一個惡作劇嗎?一定是這樣。他們全都這樣以為。那個怪獸對著女性主義者嘶吼他的恨意。那個殺人兇手發射子彈狂掃的時候,他們為什麼沒有破門而入?沒有人明白狀況。凶手先從女生開始,然後才論到男生。他們所有人都這麼認為。他們逃走了,以保住自己的小命。「懦弱」這個字眼浸透了他們的腦海。為什麼不是「驚駭」、「不解」、「害怕」、「癱瘓」、「愕然」、「難以置信」、「恐懼」?知覺的混亂。要怎麼樣才能反應得快過那個瘋狂殺手手中的半自動卡賓槍?九位年輕女孩的軀體散落在地上。有幾個還在呼吸,另外六位則否。槍裡裝的並不是空包彈。怪獸的作為。
艾彌爾、文森和其他人從來不提他的名字。姓,名,會賦予人性。那個怪獸沒有一丁點的人性。他自己清楚這點。他跑過了走道,跑過餐廳,一直跑到另一間教室。他又殺死其他八個人,殺傷了十五個人。他的彈夾裡還剩下一顆子彈。這顆子彈是留給他的。他處決了自己。他的最後一句話,「shit(屎)。」總結了他的整個人生。他最後的念頭是什麼?他的母親?她是女性主義者嗎?他的父親?他是厭惡女性的人嗎?第十五次的槍決。然後就這樣了。怪獸的最後一個念頭是什麼?狂怒,不屑,憤慨,羞愧?艾彌爾、文森和其他人沒有回答。他們太害怕得到答案。他們寧願默默地喝啤酒。
艾彌爾認為只有文森找到了一個答案。那是屬於他的答案。文森,他只說了「懦弱」這個字。「我是個懦夫。」宛如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消失在樹林裡的鳥唱聲中。在二十六個月之後。艾彌爾的世界又崩潰了第二次。失去了文森,他永遠的朋友。
艾彌爾常常躲到拉里維家避難。他們的陪伴阻擋了他沒入漩渦。菲利浦建議他搬進文森的公寓。艾彌爾不太清楚是基於什麼理由,不過他接受了。他在二樓住了下來。文森在這裡只住了幾周。拉里維夫婦賣掉了兒子所有的家具。艾彌爾留下了照片、書籍、CD、一顆羅盤、幾個木質的書架,和一架玻璃小飛機護身符。他學會與文森的回憶一起生活。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了。這間公寓變成怪獸瘋狂行徑的所有觀眾的集會地點。他們在這裡敘述他們遭遇的變故,敘述了一遍又一遍,期待著某個新元素、某段重生的記憶。控訴、罪惡感、沉默、謾罵、爭論、賭氣、眼淚、和解、擁抱、原諒、親近、哀悼與紀念。一種莫大的默契將他們凝聚在一起。一切都被說了又說。時光飛逝。聚會愈來愈稀疏。大家比較少去談論那個撼動他們人生的事件了。要怎麼樣才能從這般的痛苦中安然無恙地走出來?大家盡力繼續過日子,工作、戀愛、生小孩。
工程師的工作讓艾彌爾得以四處旅行。他利用這些出走的機會,發明另一種生活。一種沒有記憶的人生。一種「幸福」這個詞具有意義的人生。總算!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珍妮克.特朗布的圖書 |
 |
$ 110 ~ 220 | 法式小確幸
作者:珍妮克.特朗布 / 譯者:賈翊君 出版社:三采文化 出版日期:2011-12-09 語言:繁體/中文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法式小確幸
儘管它以一個悲劇為開頭,
卻拿幸福回饋了我們。
我們都需要在日常的悲傷後面,看到生命中小而確實的幸福。
文森舉槍自盡了。
菲利浦假裝缺席的文森只是出門旅行。
艾彌爾覺得文森的離開囚禁了他的自由。
熱愛音樂的夏洛特在某天對小提琴失去了熱情;
珍妮的完美男友決定放棄完成博士論文;
獨居的愛德華老太太的愛貓走失;
皮耶在妻子瑪莉離開他後開始酗酒;
芙蘿蘭絲的兒子發現自己並非母親親生。
當初就是文森建議他買下一棟老房子的。「我們一起把它翻新。」他買下了房子,一個月之後,文森便偏離正道駛入了一座樹林,帶著那把祖父在過世前送給他的獵槍。
菲利浦.拉里維翻新了文森的房子,他是這麼稱呼這棟房子的。用了十三年的時間。不是為了喜好,僅僅只是為了不要辜負兒子的期望。那是一件漫長又仔細的工作。他的肩頭上承載著文森無所不在的目光。他需要這樣的目光。那是對於好好完成的工作的一種評價、一種肯定。
一棟父親為緬懷兒子所翻修的出租公寓,十三個心中各有悲傷的靈魂,即將在十三年後文森冥誕的這一天交會,並再度分散。有人終於得到真愛,有人失去真愛。有人選擇離開,有人選擇留下。
有人得到故事的真相,並在巨大的悲傷之後,終於揮別文森留下的陰影,感到一陣有若無的幸福。
作者簡介:
珍妮克.特朗布(Janik Tremblay)
一九五一年出生於加拿大席古堤米(Chicoutimi),在得到法國文學的學士學位之後,她在渥太華地區執教了二十年,在此期間同時繼續進修教學法與傳播方面的課程。她目前居住在蒙特婁,並且從此將全付精力投注在寫作上。她已經出版了三部作品:短篇小說集《我有一座美麗城堡……》(一九九二),《音樂總是縈繞在耳》(一九九八)與《茱莉.德.聖羅蘭》(二○○二)。她自一九九七年起定居蒙特婁皇家山高台區,專事寫作(小說、劇本、戲劇)。
在本書中,她以豐富的同情心描寫出一小群人的小苦與大樂、他們的不幸與微薄的樂趣,而他們的友誼是一切的憑據。
譯者簡介:
賈翊君
文化大學法文系畢,曾從事影視節目工作,後赴法學習電影。目前為自由翻譯,偶爾接觸劇場工作。譯作有《逆流河》、《波戴克報告》、《結婚蛋糕》等。
章節試閱
一張破碎的面孔,一具破碎的軀體,一口緊閉的棺木,一禎裝在銀質相框裡的畢業照。懷裡揣著工程師文憑,文森卻前往探索事物的另一面。他不去理解自己的人生,或許,倒是理解了自己的死亡。遺體安置室裡空無人跡,菲利浦.拉里維沉默的坐著。古諾的〈萬福瑪利亞〉以微弱的音量播放著。他要求過要獨處。他並沒有在等待任何事或是任何人。他就待在那裡,只是待在那裡。
十三年來,悲傷並沒有離開過他。打從他兒子文森的死一直到現在。打從令他感到難以承受、確認屍體身分的那一刻起。沒有流一滴眼淚。只發出一聲難以形容的叫喊。
一個...
十三年來,悲傷並沒有離開過他。打從他兒子文森的死一直到現在。打從令他感到難以承受、確認屍體身分的那一刻起。沒有流一滴眼淚。只發出一聲難以形容的叫喊。
一個...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珍妮克.特朗布 譯者: 賈翊君
- 出版社: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12-09 ISBN/ISSN:978986229590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其他各國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