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二十世代 經典人物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 戴麗娟 推薦
在二十歲的時候,
在成為經典人物以前,
他們如何的思考、迷惘或造就一生的熱愛?
你會發現,那些以天賦為名的靈魂,
曾經也存在在你身上;
或者 現在 也正 依附 在 你身上!
他說:潘朵拉(Pandore)的盒子充滿著人性之惡。在從這盒子冒出來的一切事物之中,古希臘人讓希望排在最後一個,因為它是其中最可怕的。我沒見過比這更令人感動的象徵。因為跟人們所相信的相反,希望等於忍受順從。而活著,就是不要忍受順從。
一九三○年十月,母親是一位文盲清潔婦,父親則在一九一四年大戰時陣亡,即將邁入十七歲的阿爾貝.卡繆住在地中海的阿爾及利亞,和所有男孩一樣,他的生活是在海灘、咖啡店、足球和朋友之間度過的。但是當他感染了肺結核之後,一切都改變了。他開始對文學和哲學產生熱愛,他進入了阿爾及利亞高中的哲學課程。他在這裡遇到了對他人生的決定性人物:尚‧歌荷尼葉,他的老師,同時也是他的精神導師。這一年他開始受到肺結核攻擊,他因此意識到自己的死亡和生命的荒謬。
敏銳的洞察力是卡繆的特點,改革是他的戰鬥,文學則是他的武器。他要完成一部作品──他已經下了這個決定,他尋找可以見證他的童年、他的家庭,以及貝勒庫荷區人們的資料來寫作。他重複地寫了又重寫,誕生出他的第一本書: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反面與地點》(L’Envers et l’Endroit)。
他對文學的品味同時帶領他發現了戲劇的世界,戲劇和足球(他的集體思維、對友情的重視和平等主義)都是他終其一生所熱愛的。他創造了第一個阿爾及利亞劇團,改編和編導過許多戲劇。雖然生病但擁有對生活永不疲倦的精力,他經歷了結婚、離婚,加入共產黨,為了捍衛阿拉伯人而鼓吹暴動,並且變成一名記者。他在由馬侯的一位朋友帕斯卡.皮雅所領導的《共和主義的阿爾及爾》所發表的文章中,因為大力倡導反對不公平待遇,因此被殖民地政府判定有罪。在一九四○年,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卡繆在政府的命令之下被解雇,並且被驅趕出境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在他的行李裡,放著正在撰寫的《異鄉人》的手稿。
卡繆在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宣稱:「每一個世代,毫無疑問地都相信他們注定要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卻認為我們這個世代不會改變世界。但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存在也許更偉大,因為它阻止了這個世界的瓦解。」而事實上,當希特勒握權時卡繆正值二十歲。接著發生西班牙內戰,然後接著是世界大戰。閱讀阿爾貝.卡繆二十歲的時光,可以瞭解這十年如何成為他的那些首發戰鬥,他的作品主題為何偏愛這個時代,同時也可瞭解到為什麼卡繆的一生都遠離他真正的家園,一輩子當異鄉人。
-----------------------------------------------------------------------
透過這套書,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偉大作家的年輕時代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以及他們年輕時候的模樣。每一個年輕人,在二十歲的時候,都會自問自己想變成什麼樣的人,自己有什麼樣的天賦或特殊才能。這套書所描寫的都是改變時代的作家,每一個不同時代的作家都面對著不同的時代問題,每一個人在二十歲時的獨特和不平凡造就了後來的經典人物,也因此改變了世界觀。這套書的文字都很容易閱讀,但又不至於落入教條式的平鋪直敘,也有別於一般的自傳。我們可以在這些書中明顯地讀到一個思想是如何發展而成的,它通常是由實際的親身經驗而來,而不是來自書中的文字。
這套書的內容都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但是有時候也會出現因為欠缺部份資料,導致作家必須自己延伸事實的情況,一種方法是創造事實的場景故事,另一種是化身和假設,但是這兩種都有很確定的證據作為依據,所以也不能算是杜撰。不同的作者讓他們所寫得書具有不同的魅力,雖然都是描寫偉大作家年輕時代的書籍,卻不會讓人覺得每一本都一樣,讀起來不會覺得枯燥。每一本書都是一趟充滿學習的旅行,帶領我們穿越時空回到某一個時代,並且和這些偉大作家相遇。
作者簡介:
瑪夏‧塞希
Macha Séry
從一九九五年開始任職世界報的記者,她著有兩本論文集和兩本小說。
譯者簡介:
郭維雄
一九六六年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歷史學深造文憑(DEA)、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班,目前從是當代史之研究寫作、網路程式設計。
章節試閱
二十歲的卡繆
最初 的 戰鬥
瑪夏‧塞希
Albert Camus à 20 ans
Premiers combats
Macha Séry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將球遠遠地踢到對手那邊。在他前方,馬塞爾(Macel)、阿雷科斯(Alex)、奇奇(Kiki)、多明尼克(Dominique)、喬治(Geoges)、侯瑞(Roger)、摩意茲(Moïse)已汗流浹背。綽號「大塊頭」的黑蒙(Raymond)留在後方。球沒傳好。胡珊玳(Hussein-Dey)之奧林匹克(Olympique)隊的後衛拿回了球。他閃過一個球員,然後兩個。阿爾及爾大學運動協會(Racing universitaire d’Alger, RUA)的資淺球員穿著藍白條紋的球衣,他們顯然已調整回防守態勢。在球場旁,在球場旁,牟希斯(Maurice)教練叫喊著:「該死!」他像鐵道站長般地擺動著雙臂。阿爾貝在木製的球門內戒備。黑蒙為了解除威脅而前進幾公尺。他漏掉了球,但沒漏掉一名前鋒的小腿肚。布法希柯(Bufarik)舉腳準備射門。射偏了,但布法希柯撞到守門員。「孩子,對不起。」這個外號「西瓜」的中鋒老是把這句掛在嘴上。他撞倒對方、傾全身重量壓垮人家,隨即道歉——也就是說,每次都這樣。不是壞人,只是個粗魯的壯漢,加上每次在鞋釘扎到對手的腿骨時裝無辜。黑蒙擔心地問:「阿爾貝,還好吧?」卡繆站起來,沒表示不快。微笑帶著歉意,兩膝疼痛。他大可以抱怨。在這裡,沒人免於這種遭遇。尤其他那一隊的人:幾個高中生與大學生,被對方認為是布爾喬亞、有錢老爸的兒子。幸好,這個禮拜天,RUA的資淺球員在自家的球場比賽。這個球場緊鄰實驗花園(Jardin d’Essai),這個花園位於貝勒庫荷(Belcourt)區的西側。如果是在穆斯林公墓旁的胡珊玳奧林匹克隊主場,那就慘了。只要有肢體衝撞,對方的喊叫、言語恐嚇讓人想到隔壁的死屍。從球到死:總之,人生的目的地。少年們恣意做出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小動作。不過,很少。教練不喜歡這樣。男性氣概十足但正派的他堅定地提醒說,足球不只是一種團體運動項目、一種需要每個隊員互助的運動,它等於是一門道德課。雖然被對手攻進一分,教練今天並未不滿孩子們的表現。的確,自從一九三○年初以來,勝利屈指可數;但是,雖敗猶榮。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RUA隊刊報告說:「本日,我們最大的喜悅」來自於資淺的這一隊。「全隊值得我們毫無保留的恭賀。其隊員包括:卡繆;札塔塔荷(Zataltar)、班布阿里(Ben Bouali);法格蘭(Faglin)、亞塔蓋訥(Yataghène)、卡胡比(Karoubi)、班加納(Ben Gana)、昂胡斯(Amrousse)、多雍(Doyon)、佛洛黑(Florès)。其中最優秀的是卡繆,他只在對方亂來時被打敗,而且整體表現相當出色。」
在大他三歲的長兄陪伴下,「貝貝荷」(Bébert)很小就開始練習傳球與衝鋒射門。在被稱為「演習場」(Champ-de-Manœuvres)的球場上,一些穿著便服的年輕步兵──亦即住在附近的男孩們——追逐著一個布團做成的球以及勝利者的小小虛榮。在震顫著的空氣中,咒罵與呼喊此起彼落。呂希安(Lucien)與阿爾貝一回到家,祖母並不太擔心他們的關節腫脹,而是要求他們高抬雙腳,好檢查他們的鞋子。只要釘子鬆掉或鞋底不正常磨損,她就知道他們犯了不准踢足球的禁忌。她咆哮說,沒足夠的錢買新鞋。在蒙龐西耶(Montpensier)運動協會,這個次子學習到自我要求、策略式的思考、加強韌性。百次重複同樣的動作、同樣的痛苦等待、還有面對危險的臨場反應──危險常來自於射門時出錯腳。有時候,他捨棄射門,轉而擔任中場。在這個位置上,他以控球前進的穩定度而頗受矚目。週四訓練,週日比賽。打從他進入六年級,他在午餐後固定到校內的三個庭院之一練球。由於技術純熟,他受到一些半寄宿生的尊敬。這回兒,他毫不遲疑地出席二軍的比賽,然後還有更多人看的一軍比賽,當時,RUA的支持者一起呼喊著「RUA,好好好,RUA,不不不,RUA死不了。」過多的疲勞酸痛。
法屬阿爾及利亞(Algérie française)一百週年慶祝活動接近尾聲。在連續數月的活動期間,海邊裝飾著綿延不絕的燈泡,富有的殖民者老是戴著禮帽,亡者紀念碑妝點著鮮花。在總督府(Gouvernement)廣場上的閱兵行列中,在自走砲後面的軍隊包括土著騎兵隊、吐瓦黑格(Touaregs )、土著義務役士兵,三種部隊顏色不同,很容易辨認。戰艦鳴放禮炮、阿拉伯馬術表演、駱駝奔馳,這一切使內地來的人們心花怒放。在此,他們發現的是一個慶典、賽馬、音樂會的——一言以蔽之,民俗的——阿爾及利亞。除了記述這些遊行之外,全系列共含十二冊的《阿爾及利亞百週年紀念冊》(Cahiers du centenaire de l’Algérie)也細數阿爾及利亞的富庶、風俗習慣、農產、陸海空交通,以及曾在這片土地上作戰的著名軍人。一位姓波訥瓦勒(Bonneval)的將軍執筆描寫「觀光方面的阿爾及利亞」,而且依循一些極端的老套如「東方」、「魔法」、「法國的穀倉」,最後下結論說:「這是我們的殖民之神最喜愛的孩子,因為這是我們殖民帝國重建後的第一個珍寶。」五月,嘉斯桐‧杜梅荷格(Gaston Doumergue)總統為國立阿爾及爾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es Beaux-Arts d’Alger)揭幕,並且頌揚「殖民與文明在一八三○年至一九三○年期間所實現的美妙成就……」這麼多演講、這麼多裝飾,明信片的藉口……阿爾貝不太注意這些,也不太注意其他那些來自內地、在盛大儀式下登陸的演講者。這些人,這故事、這些話語跟他無關。他出身於另一個阿爾及利亞。
對內行人而言,阿爾及爾的偉大與柔和盡在薩波雷特(Sablettes)的海灘。阿爾貝有自己的泳衣,還有一本小說可讀。對清涼的需求,對海闊天空的想望。陽光使得地平線變白、變得模糊。大海以泡沫啃蝕沙灘,以帶著鹹味的舌頭舔著人們的身體。臉頰上,小水滴取代汗水。在阿爾及爾,人們習慣講「讓洗澡水打在身上」。洗海水浴的人們從休息區躍入海中,他們雙臂成十字狀,就像要飛上天。身手最好的那種人則另外加上困難的跳水動作,也就是帕塔維特語(pataouète)所謂的「蘇仆希俄」(souprieux)——帕帕維特語是阿爾及爾的方言,它的某些字詞源自阿拉伯語與法國南部諸語。有些人因精疲力竭而靠救生圈漂浮著。阿爾貝的身體是乾的,適合奮力衝入波浪中。
從海上望去,接連出現的是:海灘與休息區、小海灣與建築物的突出部、海岸線以及與它交會的鐵路線。薩埃勒(Sahel)山脈由頁岩丘陵構成,丘陵的輪廓線在落日餘暉中變成藍色。阿爾及爾嵌在此山脈的幾個末端斜坡之間,它像一面巨大的扇子,展開於海灣之前。一陣陣風吹拂著這個劇場——但不是個環形劇場——,夏季的熱浪使其氣流擾動不安。這個城市有四個區、五個郊區。在其中,歐式花園住宅與北非式的簡陋房屋相毗鄰。二十七萬居民就這樣地住在這城市中。阿爾及爾工商發達且生命力旺盛。絢麗的花朵到處綻放,阿拉伯商店的貨品所展示的顏色應有盡有。半屬歐斯曼(Hausmann)式,半屬奧圖曼式(ottomane),這個城市隨著一條條寬廣的街道向外舒展,然後動輒岔入繁複的巷弄中。走出按照歐洲型式闢建的大道盡頭之後,這個城市開始爬坡,好似要讓人們更能欣賞它那種跟海天之藍形成強烈對比的白色。舊城(Casbah)的房屋像梯田般地排列,階階是各層的露天陽台,其中還有噴泉帶來涼意。它們宛如這個城市的一條乳牙項鍊。電影導演朱里安‧杜衛維耶(Julien Duvivier)在《莫寇老爹》(Pépé Le Moko)中將這個舊城區描繪得像個迷宮。再往高處,我們看到一些西班牙碉堡遺跡。最遠處則是一整條被雪染白的山脊。
阿爾及爾?它是一些熱騰騰的石頭與夜空繁星。它是不斷沖刷洗滌的大海與負責曬乾的太陽。「其貧窮與獨特的富裕在此」,卡繆後來在《幸福的死亡》(La Mort heureuse)中如此寫道。異於南塔奇(Nantucket)與其捕鯨船——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與《白鯨記》(Moby Dick)的阿夏柏(Achab)船長相繼參加的那一種──,阿爾及爾的海岸不會讓人想逃離。地平線也不會使人夢想著它方。眾多船舶騎在波浪上,小海鷗盤旋其上,而大海鷗則窺伺著它們。它們跟馬一樣,上面有賽馬師顏色鮮明的上衣:黑紅兩色或黃白兩色。在進入停泊區時,它們放聲嘶嘯。塞內加爾(Sénégal)的貨船、挪威的郵輪、巴西的船舶在船艙側邊裝載著咖啡或香料。這些貨物由拿波里來的(napolitains)水手負責卸下。港內晾曬著捕魚歸來的拖網漁船之漁網,而總是在夏天打赤膊的碼頭工人則汗流浹背地扛著一袋袋的小麥與一堆堆的木頭。在這裡,一切都是垂直的,包括桅杆、錨機、吊車;不過,這個城市內佈著電車纜線,且因到處有拱廊而不乏圓弧線條。「大西洋渡輪」(Transat)自海港火車站出發——這渡輪來往於阿爾及爾與馬賽(Marseille)之間,每週三班,每趟耗時二十五小時。
一九三○年八月,阿爾貝咳出血來,然後莫名其妙地變瘦。四個月後,他開始持續咳嗽而且吐血。他的母親述說病情:「我兒子得肺病,活不成了」。喀血,把他緊急轉送到穆斯塔法(Mustapha)醫院的那位醫生如此轉譯。穆斯塔法醫院是個佔地八公頃的特區,儼然是個跟其它城市隔絕而自成一格的城市。醫生、護士、病人,共四千人。他們生活於此地,死於此地。這個寬廣的多邊形區域在圍牆內有數棟對稱式的大樓、多條散步道,還有一個種植著尤加利樹的花園。人們慢慢走入這花園,來看看十二月的微弱陽光。根據雷維瓦朗西(Lévi-Valensi)醫師的診斷,他的右肺患有乾酪性潰瘍結核病。患者可能死於兩年之內,其中有些可繼續存活,前提是身體夠強壯並且小心照顧身體。「隨著時間過去,再加上小心,可以痊癒。」事實上,患者永遠不會痊癒。舊稱為肺癆的這種疾病使人逐漸衰亡,它令浪漫主義(romantisme)作者們著迷,因為他們將這種身體耗損視為受苦靈魂的一種表現。在穆斯塔法醫院,完全沒有小仲馬(Alexandre Dumas)筆下的那個日益蒼白、注定犧牲的茶花女,也沒有拉馬丁(Lamartine)喜愛的那種瀕死者;裡面的人比較像是雨果(Hugo)之《悲慘世界》(Misérables)中的方亭(Fatine),亦即一些呼吸急促、奄奄一息的人,一些營養不良、骨瘦如柴的人。這是一種匱乏狀態下的疾病,而不是那種將貌美、富有、正值青春年華的故事主角擊倒的疾病。在阿爾及利亞,此病的患者大多是阿拉伯人。穆斯林青年樣樣都缺,所以也缺乏油脂。一九二一年的六萬名年輕役男當中,只有一萬兩千人通過兵役體檢。其他人呢?瘦小,不夠強壯。結核病每年造成約一千名阿爾及爾人死亡。在醫院中,人們常提到,病患出院回家後不久即與世長辭。
阿爾貝‧卡繆所受的治療完全免費,因為其父親在戰爭中為國犧牲。為了消除因感染柯霍(Koch)氏桿菌而膨脹的肺部腫脹,他必須接受人工氣胸療法,身體靠左邊側躺,胸部由與床同寬的長枕墊高,並將前臂高舉至頭上。這樣做是為了將空氣注入兩片胸膜之間——這兩片薄膜覆蓋並保護肺腔。這是種高難度手術:刺針必須穿透第一片,但不能碰到幾乎跟它相黏的另一片。
不,阿爾貝不會死,雖然他先前相信自己會死,而且當時在第一位為他做檢查的醫生臉上也看到一樣的答案。他的呼吸狀況已出現改善。然而,他從未感覺過如此嚴重的病痛,亦從未被如此的孤獨包圍。那一夜,他驟然擺盪到另一個世界。他躺在床上,閱讀艾皮科提特斯(Epictète)的著作。這位哲學家曾身為奴隸,而且被主人打斷一條腿。他寫道:「疾病對身體而言是一種障礙,但是對意志而言則不是,除非意志本身變弱。『我跛腳』,這對我的腳而言是一種妨礙;但是對於我的意志而言,一點兒也不是。關於你日後遭逢的任何意外事故,你應當說一樣的話;如此一來,你將會認為它所阻礙的是其它某件事物,而不是你自己。」的確如此,但是阿爾貝的周圍盡是一些阿拉伯人的痛苦表情與蒼白臉色。這些是因貧血而褪色的「小白人」,一些因低沈笑聲而震顫、因咳嗽劇烈而憤怒、臥病在床的肺病患者。太陽的沉落宣告他們的沉落。一到晚上,病情就惡化:發燒、冒汗、氣喘、吐痰。那一夜,阿爾貝無法入睡。「對後續發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在當天夜晚的那個時刻,我在沒想到它的狀況下接受了死亡的念頭,我不再是活著思考,而是作為已被判死的人而思考:如果這繼續下去,那也不重要了」(《沒有明天》〔Sans lendemains〕,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
疾病比閱讀更使他與世隔絕。他的病床是個木筏,一個島民的避難所。結核病初現之時,他的母親並不怎麼擔心,她對將他手帕染紅的痰幾乎無動於衷。這個母親真的愛他嗎?她現在聽不清楚他講話,只能讀他的唇來理解。她可謂是影子中的影子。這個戰爭造成的寡婦以幫傭為業。她臣服於自己的母親,而且,她基於服從,完全將她那兩個小孩的教育託付給孩子們的外祖母。她真的愛他嗎?直到這以前,這樣的懷疑未曾出現在他的心頭。是的,她愛他,雖然他們彼此很少講話。她從不動怒。當他經過她身邊,她習慣性地親他三下,然後目送他離去。然而,他現在獨自面對伺機而生的憂慮,獨自跟死亡為鄰。他剛滿十七歲。所以,他在十七歲時就開始喪命。不一定是今天,未必是明天。不論如何,他已開始喪命。以前慣於奔跑與游泳,如今力量盡失而且高燒在全身流竄,他的身體已不記得何謂健壯。這教他瞭解其他人因無憂無慮而毫無所知的事——對此事,他們比較只是知道,卻未曾親身體驗,就像將日常事物隨意抽象化,所得出的就只是一種理論,且幾乎是一種謬誤。這種關於死亡的鮮明意識很少出現在青少年身上,它將像一個隨身相伴的陰影。若無光明,無法意識到這個陰影。「但畢竟,在此生之中,首先否定我的事物就是殺我的事物。任何事物一旦揄揚人生,即增加其荒謬性」,後來,卡繆在《婚禮》(Noces)中寫道。他繼而補充說:「潘朵拉(Pandore)的盒子充滿著人性之惡。在從這盒子冒出來的一切之中,古希臘人讓希望排在最後一個,因為它是其中最可怕的。我沒見過比這更令人感動的象徵。因為跟人們所相信的相反,希望等於順從。而活著,就是不要順從。」在醫院中,阿爾貝大喊一聲:「我不要死。」
二十歲的卡繆
最初 的 戰鬥
瑪夏‧塞希
Albert Camus à 20 ans
Premiers combats
Macha Séry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將球遠遠地踢到對手那邊。在他前方,馬塞爾(Macel)、阿雷科斯(Alex)、奇奇(Kiki)、多明尼克(Dominique)、喬治(Geoges)、侯瑞(Roger)、摩意茲(Moïse)已汗流浹背。綽號「大塊頭」的黑蒙(Raymond)留在後方。球沒傳好。胡珊玳(Hussein-Dey)之奧林匹克(Olympique)隊的後衛拿回了球。他閃過一個球員,然後兩個。阿爾及爾大學運動協會(Racing universitaire d’Alger, RUA)的資淺球員穿著藍白...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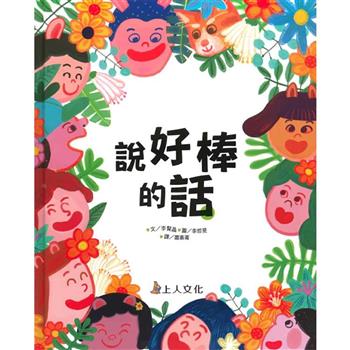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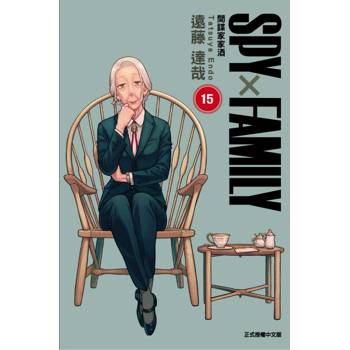

![2026【補充延伸實務趨勢與議題】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二十一版](領隊華語人員/外語人員) 2026【補充延伸實務趨勢與議題】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二十一版](領隊華語人員/外語人員)](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6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