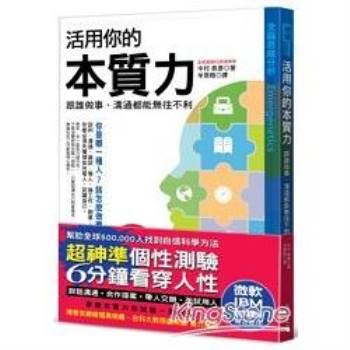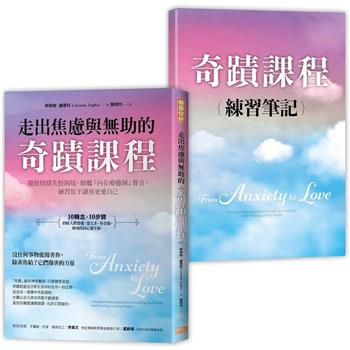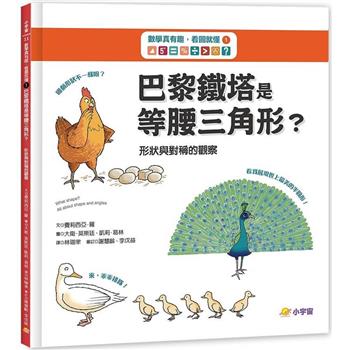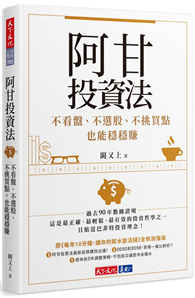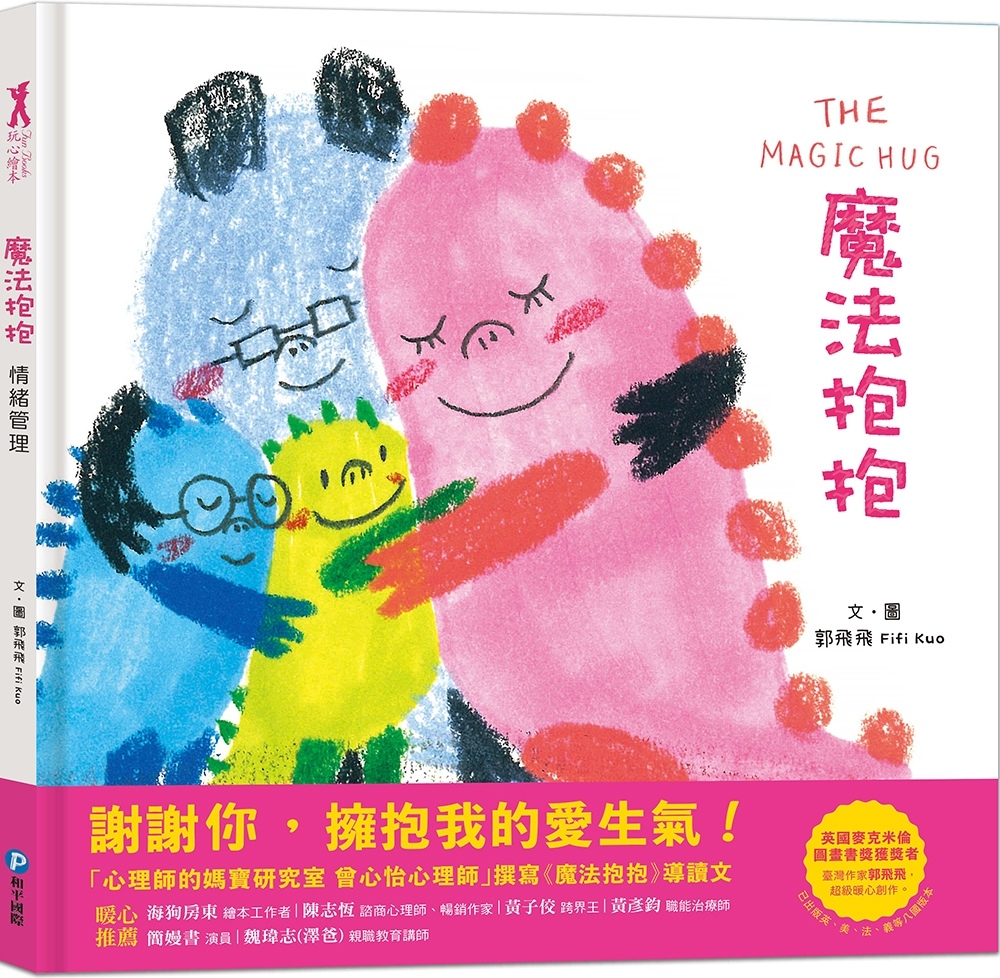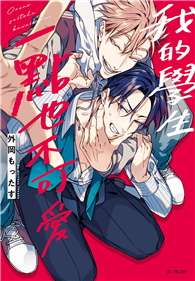◎獲得1982年筆會/海明威文學獎(PEN/Hemingway)和提名普利茲獎。
◎ 小說家翁達傑最喜歡的小說。
◎蘇格蘭導演比爾.福斯電影原作。
無聲無息的潛入心靈深處,如同雪融之後……
一本在最安靜的角落,獻給最安靜的閱讀的療傷之書。
2005年美國國家書評獎、普立茲獎得主──瑪麗蓮.羅賓遜《紐約時報》評選為上個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管家》混合了論文的精省文字、詩意的韻文、強烈的情感、優雅的幽默,以及大量的典故與暗喻,二十多年來已經成為美國的當代經典。
講述在愛達荷州農村的二位小女孩,在失去母親、外婆後,由希薇阿姨扶養的成長故事。作者詩意的文字細膩地描繪出美國西北部森林和湖的圖像,也刻劃出兩位小孤女面對一成不變的生活中內心的沉靜世界。
「希薇抵達那個禮拜,指骨鎮有三天燦爛的晴天,另外四天下著細雨。第一天,冰柱很快地掉下來,屋簷下的碎石因而跳動,發出聲響。雪在陰影下呈粒狀,在陽光下就變軟,溼漉漉地覆蓋在任何東西上面。第二天,冰柱在地上摔碎,大塊沈重的雪懸在屋簷下。露西兒和我用木棍把它們捅下來。第三天雪積得很厚,很有可塑性,我們做了一個類似雕像的東西。我們把一個大雪球放到另一個大雪球上,拿廚房用的湯匙來雕刻,做出一個穿長洋裝,交叉著手臂的女人。露西兒想讓她面向旁邊,我跪在地上削她的裙擺時,露西兒就站在廚房的板凳上塑她的臉頰、鼻子和頭髮。結果我把她的裙子雕得離屁股太遠,她的手臂交叉在胸部很上面的地方。這不過是意外──有的雪較堅硬,有的較軟,雪球有些部份還有被堆進去的黑色枯葉,我們得用乾淨的雪來填補──不過她的姿勢還是逐漸成形了。」--《Housekeeping—管家》
「……當希薇伸手把頸子後面的頭髮綁緊時,她的頭古怪而笨拙地偏向一邊,我母親也是這副模樣。這並不神祕。她們倆跟我一樣,都是瘦長的女人,跟她們一樣的神經行走時舉我的手投我的足。如此的巧合,難道又是感官和世界所共謀的另一項證據?幽靈在明亮而滑溜的表面顯形,像是,記憶和夢。希薇的頭側向一邊,然後我們看到的是我母千雙肩上的肩胛骨,還有她脊椎上方的圓骨。海倫就是鏡子裡的女人、夢裡的女人、記憶裡的女人、水裡的女人,她的神經拉動盲從的手指把希薇所有散開的髮絲全收攏在一塊。」--《Housekeeping—管家》
作者簡介
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
(1943/11/26–)生於美國愛達荷州(Idaho)北部,緊靠Pend Oreille湖附近的城鎮Sandpoint,本姓Summers。一九六六年她畢業於布朗大學,主修宗教和文學創作,畢業後到法國Rennes城Univesite d'Haute Bretagne大學教授英文一年,在此開始醞釀她的長篇小說《管家》(Housekeeping)。然後回美國繼續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其博士論文主題為莎士比亞的《亨利六世》,同時開始將論文的筆法與詩的文字及大量隱喻,以其家鄉為藍本虛構指骨鎮,寫成小說《管家》,於一九八一年出版,榮獲美國筆會╱海明威獎最佳小說,並入圍普立茲獎。在隨後的二十年間,這本小說甚至被認定為上個世紀最好的十本小說之一。
而羅賓遜更被認定為美國當代最好的作家之一。在這段時間內,她亦寫出數篇談論《聖經》的論文。 雖然《管家》早被認為是經典,但羅賓遜並不以小說家自居,隨後並沒有繼續出版新作品,一九八○年代中期隨夫婿與兩個兒子遷居英國,出版她的第二本書《祖國:英國、福利國家與核能污染》(Mother Country: Brita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Nuclear Pollution, 1989),書中深入描述英國Sellafield核能加工廠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破壞,並批評應國政府與綠色和平組織,因而引起綠色和平提出毀謗訴訟,該書在英國遭禁,但在美國卻入圍美國國家書獎決選名單。
就在此時,她的婚姻觸礁,她帶著兩個兒子回到美國,在大學教授創作維生,隨後在愛荷華州愛荷華市的「重要作家工作坊」任教,直到現在。 一九九八年,羅賓遜出版她第三本書《亞當之死:當代思潮文集》(The Death of Adam: Essaye on Modern Thought),書中談論的主題從神學克爾文(John Calvin)到美國清教徒社會、生物演化學家達爾文到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等,檢視批評了文化對當代人的影響。羅賓遜的思緒翻新,本書極受好評。就在大家已經不再期盼她的新小說,而其名字逐漸在文學界淡化時,於二○○四年年底,她出版了相隔二十四年之久的第二本小說《基列》(Gilead),以一個七十六歲的老牧師寫給七歲兒子未來閱讀的長信,於一九五六年,回顧他從祖父南北戰爭以來到他父親等三代的家庭回憶,充滿濃厚的寬恕與愛的宗教情懷,「對我而言,寫作如同祈禱。」這本以愛達荷Tabor小鎮為藍本做虛構的美國基列城,是她寫給愛達荷的情書。在《舊約》中,基列城盛產乳香,治人創傷,醫罪人心,亦是一處戰禍、流血與不義之地。
《基列》不久成為《紐約時報》的年度十大好書,並在四月同時獲得美國國家書評獎與普立茲小說獎,這是美國對他們聰慧而安靜的作家所做的一次相約而同的禮讚。 對羅賓遜來說,她並不是在寫小說,她只是再寫一本書;而其中可以同時展現及其細微的思潮,同時也以其波浪的韻律和節奏,表現出情感的深刻強度。
譯者簡介
李佳純
一九七三年十月生於台北。輔大心理系、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媒體研究系畢業。曾任唱片行店員、電臺和酒吧DJ。返國後專事翻譯,譯有《喬凡尼的房間》等。
譯者簡介
林則良
作家。著有詩集《與蛇的排練》等。



 共
共  2012/06/02
2012/06/02 2011/07/16
2011/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