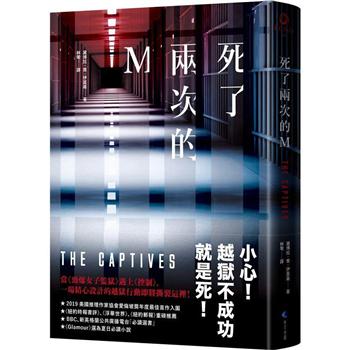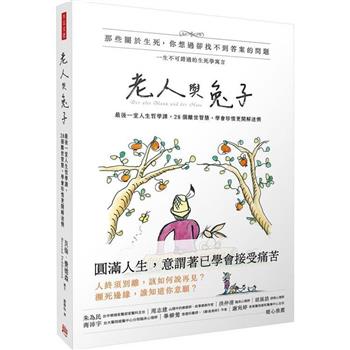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章楷治的圖書 |
 |
$ 255 ~ 270 | 黃沙
作者:章楷治 出版社:三三出版社Empress Culture Sdn Bhd 出版日期:2025-06-06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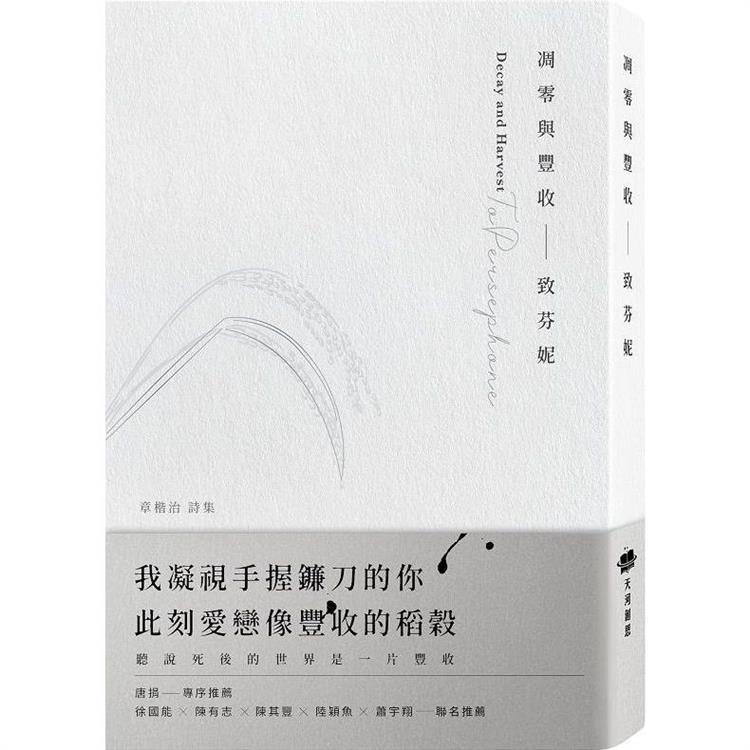 |
$ 300 ~ 380 | 凋零與豐收:致芬妮【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章楷治 出版社:天河創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2-02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