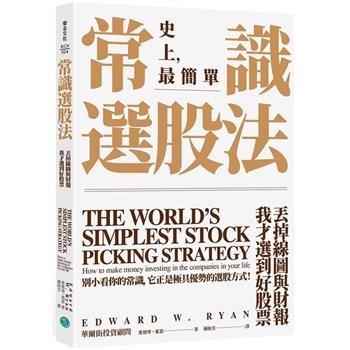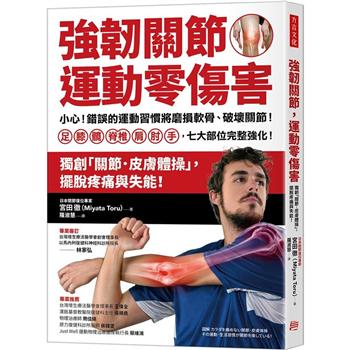身為弱勢者,究竟會對你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響?為了理解他者,你願意付出多大代價?
為了克服歧視,你願意冒多大的危險?
1959年,美國民權運動前夕,
一位白人作家,為了瞭解黑人的真實處境,
做了一個至今都難以被超越的社會實驗……
儘管美國南方的白人堅稱他們與黑人相處和諧,當時全美知名的小說家約翰‧格里芬讀著一份指出南方黑人自殺傾向飆高的報告思索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遭遇與條件,讓黑人對生命失去渴望?
格里芬為了尋求真相,與專門報導黑人議題的雜誌《深褐》合作,並在家人的支持與醫師的協助之下,透過藥物、日光燈曝曬及染色劑將皮膚染黑,剃了光頭,走入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喬治亞等種族隔離的南方州,展開為期七週的旅行。
然而,穿著合宜且受過良好教育的格里芬,為了找工作整日奔走,卻被白人毫不掩飾地告知,他們打算趕走所有的黑人,只要他是黑人,就不可能被雇用。他遭到白人瞪視、惡意驅趕甚至尾隨,讓他搭便車的白人露骨地表現出對黑人性生活的獵奇心理……每件事情乍看之下都是可以隱忍的小事,但種種小事重複發生,逐日累加、堆疊,使格里芬不得不承認:在重視個人人格特質的美國,膚色才是人們用以評斷他人價值的首要依據,而黑色的皮膚所標誌的,是生命的次等。
「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指引我去最近的黑人餐館。
如果我主動要杯水喝,他們也許會給。
但我從來沒問過。黑人很害怕遭到拒絕。」
格里芬並未隱瞞自己的白人姓名或作家身分,但遊走在黑白之間使他深刻體悟,被歧視的經驗會全然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及思維。這趟旅程讓格里芬的內在與外在都脫去了一層皮。化身黑人後,他日常生活的重心都花在解決對白人不成問題的生理需求之上,無暇做更多精神上的思考。他變得成天在擔心是否找得到有色人種專用的廁所,以及服務黑人的餐廳和旅館。他變得神經緊張,常常面露沮喪,甚至夢見白人帶著仇恨的目光,朝他步步逼近,直至尖叫驚醒。無論是現實還是夢境,格里芬都毫無喘息的空間。但格里芬可以返回白人世界,真正的黑人卻無法逃離,也永遠不可能習慣被偏見灼傷的日常。
因為恐懼如此深刻,連陽光都變得黯淡。
因為仇恨如此赤裸,連安慰的言詞都顯得空洞。
《像我一樣黑》是格里芬在南方旅行一個半月的生活省思,呈現出膚色如何成為剝奪人的權利與自由的理由,以及種族主義的思維如何殘酷地區別、隔離你我。此外,他更細膩地指出,若遭到歧視是黑人共同的生命經驗,灌輸給黑人父母、認定黑人先天有所缺陷的自我厭惡便會代代相傳,使黑人孩子的人生從一開始就渺無希望。旅程結束之後,格里芬寫下他的遭遇,並走上全國舞台,疾聲呼籲黑白雙方必須直接展開對話。因為即便民權法案已在1964年通過,這個國家所頌揚的價值與黑人的實際經驗之間仍有著巨大鴻溝。
這是一本承載膚色歧視所引發的絕望與無助的真實日記。格里芬以一己肉身進行換位思考,揭露國家內部的矛盾、焦慮與暴力,期許終有一天,人們能屏棄外在的差異,攜手走向種族和解的未來。
專文導讀
盧令北|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專文推薦
張惠菁|作家
劉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聯合推薦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吳曉樂|作家
林立青|工人作家
房慧真|記者
顏擇雅|出版人
各界讚譽
「世界的各個角落聯繫已是越來越密切,人類仍然在學習『他者不是他者』的智慧。感謝生活在半世紀之前的格里芬,以成為他者的勇氣,穿越人我的邊界。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書,是人類更好的可能。」──張惠菁(作家)
「當我們看見社群網路上另一段黑人被誤殺的影片或者新聞,我們必須想起格里芬筆下的細節,這些跨越時空的姓名與身體,都在指向同一個故事。」──劉文(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這是一本必讀之書……作為第一手社會觀察報告,提供了前所未見的真實紀錄。」──《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本書是對恣意妄行、無中生有的殘暴最尖銳的控訴。讀來令人糾結難受。」──《達拉斯晨報》(Dallas Morning News)
「由一名傑出小說家所著,《像我一樣黑》是一本震撼人心、也讓人深感不安之書,對我們的社會提出了嚴厲的質問。」──《週六書評》(Saturday Review)
「迄今為止,對種族問題最深刻、一針見血的記述。」──《亞特蘭大憲法報》(Atlanta Journal & Constitution)
「卓越的成就往往來自正確且再平凡不過的行動。《像我一樣黑》就是因此而誕生的傑出之作。」──《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of London)
「《像我一樣黑》的道德影響力並未隨著時間消逝,其中有些元素仍能教導我們鑑往知來。」──《德州月刊》(Texas Monthly)
「一部不可或缺且經典的著作,絕對值得重版出來。」──《選擇》月刊(Choice)
作者簡介:
約翰‧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1920-1980)
美國小說家及記者。1920年生於德州達拉斯。在音樂家母親的薰陶之下,於1936年前往法國學習音樂治療。二戰爆發時,人在法國的格里芬加入美國空軍,投入美軍在南太平洋的作戰。大戰期間,他曾兩次受傷,導致雙眼失明。他於是放棄學醫,潛心研究哲學與神學,並從事寫作,結婚、生子,直到1957年1月突然重見光明。
1959年,視力恢復的格里芬與黑人雜誌《深褐》(Sepia)協議進行一項調查南方種族議題的計畫。他透過化學藥品與藥物將皮膚曬黑、染黑,隻身前往南部數州,換上黑人的外貌,親自感受白人的敵意與歧視,見證南方社會安穩和諧之下的黑暗。1959年底,格里芬回到他在德州的家,將其經歷整理成〈羞愧之旅〉(Journey into the Shame)一文發表。文章刊出後,格里芬獲得美國與國際媒體的矚目與讚賞,但在家鄉,象徵他的假人被公然吊在紅綠燈上,宛如公開絞刑,終使他不得不帶著家人前往墨西哥避難。
旅程之後,格里芬雖然遭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威脅,更在1975年遭三K黨圍毆,他仍然為人權運動孜孜不倦,跑遍全國各地,與重要民權運動領導人合作與對話,曾任教於哥斯大黎加的和平大學(University of Peace),並於海內外發表多達上千場演講。1980年9月,格里芬病逝於德州。
格里芬著作無數。在失明期間,著有小說《牆外邪魔》(The Devil Rides Outside)、《裸夷》(Nuni)。非虛構作品另有《高空的土地》(Land of the High Sky)、《教堂與黑人》(The Church and the Black Man)、《隱藏的整體:湯瑪斯.梅頓眼中的世界》(A Hidden Wholeness: The Visual World of Thomas Merton)、《雅克‧馬里旦:以文字與圖像致敬》(Jacques Maritain: Homage in Words and Pictures)、《散落的暗影:關於失明與光明》(Scattered Shadows: A Memoir of Blindness and Vision)等。
譯者簡介:
林依瑩
自由口筆譯工作者。台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與美國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雙碩士。從事公共政策、科技、商業、藝文等類型之會議同步口譯,扮演跨語言文化實質溝通的橋樑。
章節試閱
一九五九年,深南方的旅程
十月二十八日
這個想法已經困擾我很多年,而那天晚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固執地回到我心中。
如果在深南方有個白人變成黑人,他會需要調整什麼?因為膚色而被歧視,遭遇到這種自身無法控制的情況,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舊穀倉所改成的辦公室桌上有一份報告,因為這份報告,再次讓我深思。這份報告提到南方黑人的自殺傾向增加。這並不意味他們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是已經到了一個徹底不在乎自己生或死的境地。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麼慘,儘管南方的白人民代堅稱他們與黑人有著「絕佳和諧的關係」。我窩在辦公室,就位於我爸媽在德州曼斯菲爾德的農場裡。在我五英里外的家中,我的妻子和孩子正睡得香甜。坐在這兒,秋天的氣味從窗戶透了進來,將我包圍,我無法離開,也無法入睡。
希望知道真相的白人,除了成為黑人外,還可以怎麼辦?雖然在南方大家比鄰而居,但兩個種族之間根本早已停止交流。誰都不知道另外一群人的情況。南方黑人不會告訴白人真相。因為在很久以前他就知道,如果說出讓白人不悅的事實,白人將會讓他的生活痛苦不堪。
我看到唯一能彌補我們之間鴻溝的方法,就是成為一名黑人。我遂決定這麼做。
我突然發現自己準備進入一種如謎團般且令人恐懼的生活。當我決定成為黑人,我才意識到,雖然自己專研種族議題,我其實對黑人實際碰上的問題一無所知。
十月二十九日
下午我開車到沃斯堡(Fort Worth)去找我的老友喬治‧列維坦(George Levitan)討論這個計畫。他是《深褐》雜誌(Sepia)的老闆。《深褐》是一份跨國發行的黑人雜誌,風格類似於當時以豐富照片為特色的《形象》雜誌(Look)。喬治是名身型龐大的中年男人,一直以來我都很敬仰他,因為他讓不同族裔的求職者有公平的就業機會,根據能力和未來潛力來選才。透過在職培訓計劃,他讓《深褐》雜誌成為業界模範,從編輯、印刷到發行,都是在這座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沃斯堡工廠進行。
那天是一個美麗的秋日。我開車到他家,下午三點多抵達。他的門隨時都敞開著,我就走進去叫他。
他人很熱情,給了我個擁抱,讓我坐下來,並請我喝咖啡。從小房間的玻璃門望出去,看到幾片枯葉漂浮在他家游泳池的水面上。
他把臉頰埋在拳頭裡,聽我解釋我的計畫。
「這是個很瘋狂的主意,」他說。「你到那邊胡鬧會害死自己的。」但他無法掩飾內心對此計畫的熱忱。
我跟他說,南方的種族問題是整個國家的污點,對於我們的國際形象來說尤其不利。而要釐清我們國家是否有次等公民並了解他們的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但情況會很糟。」 他說。「你會成為全國最無知暴民的眾矢之的。如果被他們抓到了,他們一定會對你不利,以儆效尤。」他凝視著窗外,一臉專注。
「不過你知道的,這是個好主意。我完全可以了解你現在的心情,那我能怎麼幫助你?」
「費用讓你付,我寫幾篇文章給《深褐》,或者讓你採用我書中的幾個章節。」
他同意了,但建議我在確認最後計畫前,先與《深褐》的編輯總監阿黛爾‧傑克遜夫人(Adelle Jackson)討論。我們倆都非常重視這位出色女性的意見。她從秘書晉升成為全國最傑出的一名編輯。
和列維坦先生道別之後,我就打電話給她。起初,她認為這個想法絕不可行。她說:「約翰,你不知道自己給自己挖了什麼坑。」她認為當我的書出版時,我會成為所有仇恨團體怨恨的對象,他們會竭盡所能地抹黑我,而許多善良的白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也不敢對我釋出善意。而且,即使是心存善念的南方人,他們私下也會認為,白人假裝成非白人會降低格調,令人反感。此外人們還會說:「不要惹事生非,就儘量維持平和。」
然後我回家把計畫告訴我的妻子。她從驚訝中回神後,立即毫不猶豫地同意,說如果我覺得真的必須做這件事,那就這麼做吧。作為她對這計畫的支持,她表示願意與三個孩子,共同承擔起這個丈夫和父親皆缺席、不甚美滿的家庭生活。
晚上我回到位於穀倉的辦公室。窗外的青蛙和蟋蟀讓無聲更加寂靜。一陣涼風拂過,使樹林中的枯葉沙沙作響,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泥土味,讓我注意到外邊的田地,數小時前農人才剛用拖拉機犁完田。我在靜謐中感受到大地的生機盎然,感受到在田畦深處鑽洞的蚯蚓,感受到在森林裡尋找夜間發情的配偶或覓食的動物。我開始感受到寂寞,對我決定要做的事情感到畏懼。
十月三十日
這天我與傑克遜夫人、利維坦先生和達拉斯辦事處的三名聯邦調查局探員共進午餐。我知道我的計畫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他們也無法提供任何形式的協助,但我希望提前告知他們。我們討論了詳盡的細節。我決定不更改我的姓名或身份。我只會改變自己的膚色,讓人們自己下結論。如果我被問到說我是誰或我在做什麼,我會如實回答。
「不管我的膚色為何,你們認為他們會把我當成約翰.霍華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來對待?或者,雖然我是同一個人,但他們只會把我看作無名的黑鬼?」我問道。
「你不是認真的吧。」其中一位說。「他們不會問你任何問題。他們一看到你,就會認定你是個黑鬼。關於你,他們不會想要知道其他事。」
十一月一日 紐奧良
我在入夜之後搭機抵達。我把行李寄放在法國區(French Quarter)的蒙特萊昂酒店(Hotel Monteleone),然後到外面走走。
這是個很奇特的經驗。我在失明的期間曾經來過法國區,並在這裡學習用拐杖走路。現在,當我看到失明時曾到過的地方,內心非常激動。我走了好幾英里,試圖用眼睛辨識那些過去只能憑氣味和聲音認得的事物。街上到處都是遊客,我在他們之中漫步,狹窄的街道、鐵窗花的陽台、燈火通明的鋪石庭院裡瞥見的綠色植物和藤蔓,這些都深深吸引著我。無論是人煙罕至、點著盞燈的街角,或是皇家街(Royal Street)閃爍的霓虹燈,每個景色都無比魔幻。
我走過幾家俗艷的酒吧,拉客的簇擁我進去看看那些「美麗女子」擺臀弄姿。他們把門敞得夠開,足以窺見裡面昏暗、藍霧彌漫,粉紅色聚光燈的光束相交灑落,讓半裸的女孩肉體呈現玫瑰色。我繼續步行,喧鬧的爵士樂從酒吧裡傳來。古老石板街道、克里奧料理(Creole cooking)和咖啡的氣味充滿著整個街道。
在布魯薩德餐廳(Broussard's),我在星空下絕美的庭院中享用晚餐,包括炸牡蠣拼盤(huîtres variées)、蔬菜沙拉、白酒和咖啡,就跟我幾年前在這兒用餐時一樣的菜色。我看著眼前的一切──燈盞、樹木、點著燭光的餐桌、小噴泉,彷彿我透過一個精密的相機鏡頭看著這一切。被優雅的侍者、溫婉的客人、精緻的料理環繞著,我想到接下來的日子我將居住在這城市中的另一個區域。在紐奧良,有黑人可以吃到炸牡蠣拼盤的地方嗎?
晚上十點,我吃完晚餐,接著打電話給一位住在紐奧良的老朋友。他堅持要我住在他家,讓我鬆了一口氣。我可以想見,在我把自己變成黑人的過程中,如果住在旅館裡將會遭遇各式難題。
十一月二日
早上我打電話給醫療資訊服務單位,詢問一些著名皮膚科醫生的資訊。他們給了我三個名字。第一個接到我電話的醫生立即讓我約診,於是我就搭路面電車到他的辦公室,向他解釋我的需求。針對這種需求,他沒有相關經驗,但是願意協助我完成計畫。醫生記錄了我的病歷後,他要我等一下,他同時透過電話連繫一些同事,諮詢能讓皮膚變黑的最佳方法。
過了一會兒,他回到診間,告訴我說他們一致同意先讓我使用口服藥物,再讓紫外線照射身體。他解釋說,他們也是讓臉上和身體會出現白斑的白斑症患者使用這樣的療法。在這種藥物研發出來以前,白斑症患者到公共場所都需要上厚厚的一層妝。不過這個療程有其風險,通常需要六週到三個月的時間才能讓膚色變黑。我告訴他,我沒有那麼多時間,所以我們決定嘗試加速療程,並在期間不斷抽血檢查,確認我的身體對藥物的耐受性。
我拿了處方,回到家裡吃下藥。兩個小時後,我用日光燈的紫外線照射全身。
我的房東朋友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我告訴他,我正在進行一項我無法與他討論的任務,而且如果我有天不告而別,他也不用感到驚訝。我知道他沒有偏見,但我仍然不希望把他牽扯進來,因為一旦我的故事開始為人所知,一些偏執者或他的友人可能會因為他當初讓我住他家而報復他。他給了我一把他家的鑰匙;我們同意維持不同的作息,就不必擔心在互動上要像一般主客關係那樣客套。
晚飯後,我搭電車進城,走過了南拉姆帕特街(South Rampart Street)與德里亞茲街(Dryades Street)一帶的黑人區。這裡大多是窮人區,有各種咖啡館、酒吧和小店,接鄰著擁擠的住宅。我在尋找一個讓一切開始的機會,讓我進入黑人世界的門路,或許是某個熟人。但到現在,我還毫無頭緒。我最擔心是我真的要「穿越進入」的那個蛻變的瞬間。在哪裡、又該怎麼做?從白人世界進入黑人世界是件複雜的事。我在牆壁上尋找縫隙,好讓我不被發現地穿越。
十一月六日
過去四天當中,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醫生那兒,或關在我的房間裡,用棉布覆蓋眼睛,然後打開太陽燈照射身體。醫生們進行了兩次血液檢查,沒有發現肝臟受損的跡象。不過藥物讓我精神不振,而且我經常感到噁心。
我的醫生很好心,多次警告我說這個與黑人接觸的計畫實在很危險。現在他有些時間思考了,開始懷疑這個療程是否明智,又或者他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責任。不管怎樣,他提醒我說在每個主要城市都必須有一些聯絡人,好讓我的家人可以時不時確認我的安全。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他說。「我尊重黑人。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當實習生時,有次不得不去南拉姆帕特街幫幾個人治療。他們三、四個人坐在酒吧或朋友家中。他們前一刻顯然是朋友,但後來出了點事,其中一個人就被砍了一刀。我們願意竭盡全力幫助他們,但問題是,您如何告訴他們履行正義的責任?明明你很擔心他們是如此無視於正義,甚而可能殺了你,尤其他們對自己人本身的態度就是這樣。」他帶著真切的悲傷如此說道。我告訴他,我認識的人告訴我,黑人們本身已經意識到了這個難題,他們努力團結同胞,也進而譴責任何可能對整個種族不利的手段、暴力或不義之舉。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他說道,但顯然沒有被說服。
他還告訴我一些黑人曾經跟他說的事:膚色越淡的黑人,就越值得信賴。我很驚訝這麼有智識的人竟然會相信這種無稽之談,也同樣驚訝於黑人竟然會提倡這種說法,因為這會讓膚色較黑的黑人處於劣等地位,同時助長以膚色看人的種族主義想法。
當我沒有躺在日光燈下時,我就在紐奧良的街道上行走著,熟悉自己的所在。每天我都會去法國市場附近人行道的擦鞋攤。擦鞋工是個老人、個子大、聰明伶俐,善於言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了一條腿。他沒有表現出南方黑人卑躬屈膝的樣子,很有禮貌又容易親近。(不過我沒有幻想說我了解他,因為他太機靈了,不會讓任何白人享有那樣的特權。)我告訴他我是個作家,來到深南方考察人們的生活、公民權利等等,但是我沒有告訴他我會以黑人的身分執行這個任務。最後,我們交換了名字。他名叫斯特林‧威廉斯(Sterling Williams)。我認為他可能是我進入黑人群體的連結。
十一月七日
早上我最後一次去看醫生。療程沒有如我們希望的那麼迅速、盡如人意,但我現在的膚色已經夠深,可以完美地塗上著色劑。我沒有自然捲,所以我們決定我必須剃光頭。劑量確定了,隨著時間膚色會更暗沉。接下來,就靠我自己了。
醫生表達了很多次的疑慮,可能後悔在這個變身計畫中跟我合作。他再次嚴正警告,並告訴我,不論是白天晚上,任何時候若遭遇麻煩,都可以跟他聯絡。我離開他的辦公室時,他握了握我的手,嚴肅地說:「從現在起,你將進入遭人遺忘之境。」
寒流侵襲紐奧良,所以那天躺在燈下感覺很舒服。我決定當天晚上就剃光頭,開始我的旅程。
下午,我的房東眼帶善意但不安地看著我。他說:「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但我很擔心。」
我請他別這麼想,並暗示我可能會在晚上會離開。他說他有個會議,會把它取消。我請他不要這麼做。「我不想要我離開的時候,你在這裡。」我說。
「你之後要做什麼?當個波多黎各人還是什麼的?」他問道。
「差不多吧,」我說道。「這可能會衍生一些影響。我寧願你對這件事一無所知,我不想要牽連你。」
他大約在五點時離開。我幫自己弄了一頓晚餐,喝了很多杯咖啡,延後面對這個把自己頭髮剃光、抹上著色劑,以黑人身分走入紐奧良黑夜的時刻。
我打電話回家,但沒人接。我的神經緊張,感到恐懼不安。終於,我開始剪頭髮,剃光頭。花了好幾個小時,用了好幾個剃刀刀片,我才覺得腦袋瓜摸起來很光滑。我被房子的寂靜所包圍。夜漸漸深了,我偶爾聽到電車晃行而過。我塗上一層又一層的著色劑,再把它擦掉,然後沖洗掉多餘的。直到我穿好衣服、打包好行李,我才看向鏡子。
我關掉所有的燈,走進浴室,關上門。在黑暗中,我站在鏡子前,手放在電燈開關上。我強迫自己把燈打開。
光線從白色瓷磚上流瀉下來,一個陌生人的臉龐和肩膀出現在我眼前,他從鏡子裡瞪著我──一個兇猛、光頭、膚色非常黑的黑鬼。他一點也不像我。
整個改造是徹底而懾人的。我原本預期的是喬裝,但這截然不同。我被囚禁在一個完全的陌生人體內,一個我感到毫無關係、莫不相干的陌生人。所有我作為約翰‧格里芬的生命印記都被一抹而去。就連感官上也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讓我苦惱不已。我照著鏡子,看不見任何關於白人約翰‧格里芬的過去。不,鏡中的那人把我帶回到非洲、回到那些破房子和貧民窟、回到黑人徒勞無望的奮鬥。突然之間,幾乎在毫無心理準備、沒有任何預兆的狀況下,那身影變得很清晰,滲透了我的身心。我的直覺是與之對抗。我作過頭了。我現在知道,當那黑色無法被抹去,就沒有所謂的喬裝的白人。無論他曾經是誰,有著黑色皮膚的人就是全然的黑鬼。我是一個剛剛才出生的黑人,必須走出那扇門,去一個對我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生活。
如此徹底的轉變嚇壞了我。這與我本來想像的截然不同。我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是觀察者,另一個則是驚慌失措,感受到自己由裡到外都成了黑人。我開始感受到巨大的孤獨,並不是因為我是黑人,而是因為過去的自己,那個我認識的自己,被埋藏在另一個人的肉體內。如果我回到家中的妻兒身旁,他們不會認得我。他們會打開門,茫然地看著我。我的孩子們會想知道這個高大的光頭黑人是誰。如果我走到朋友面前,我可以想見他們不會一眼就認出我。
我竄改了人類存在的奧秘,迷失了自己。這件事讓我崩潰。以前的格里芬不見了。
最慘的是,我覺得我一點也不想和這位新生之人成為同伴。我不喜歡他的長相。我想,或許這只是第一時間的震驚反感。但改造已經完成,沒有回頭路了。接下來幾週,我就是這個年邁的光頭黑人了。我必須旅行穿過一片敵視我的膚色與皮相的土地。
一九五九年,深南方的旅程
十月二十八日
這個想法已經困擾我很多年,而那天晚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固執地回到我心中。
如果在深南方有個白人變成黑人,他會需要調整什麼?因為膚色而被歧視,遭遇到這種自身無法控制的情況,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舊穀倉所改成的辦公室桌上有一份報告,因為這份報告,再次讓我深思。這份報告提到南方黑人的自殺傾向增加。這並不意味他們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是已經到了一個徹底不在乎自己生或死的境地。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麼慘,儘管南方的白人民代堅稱他們與黑人有著「絕佳和諧的關係...
目錄
推薦序──張惠菁
推薦序──劉
導讀──盧令北
地圖:格里芬遊歷經過的城市
引言
作者序
一九五九年,深南方的旅程
因為膚色而被歧視的感受是什麼?長年關心種族議題的格里芬決心化身黑人,深入種族隔離的深南方,尋找種族歧視的真相。
• 踏入遺忘之境
• 直搗核心
• 被惡夢追趕
• 來回於黑白之間
一九六〇年,餘波未了
結束在南方的旅程後,格里芬回到家鄉,潛心寫下旅行遭遇,並以文章形式刊出。他的經驗與勇氣使他獲得媒體紛紛邀約採訪,但威脅電話與家鄉居民的沉默卻讓他深陷不安。
一九七六年,結語
在《像我一樣黑》再版之際,格里芬為舊作撰寫新結語,講述他十年來對民權運動發展的觀察,並反思白人、黑人與他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九七九年,他者之外
《像我一樣黑》問世十八年後,格里芬重新回顧他的旅程,再次提出他對種族主義的省思。
後記
注釋
謝辭
推薦序──張惠菁
推薦序──劉
導讀──盧令北
地圖:格里芬遊歷經過的城市
引言
作者序
一九五九年,深南方的旅程
因為膚色而被歧視的感受是什麼?長年關心種族議題的格里芬決心化身黑人,深入種族隔離的深南方,尋找種族歧視的真相。
• 踏入遺忘之境
• 直搗核心
• 被惡夢追趕
• 來回於黑白之間
一九六〇年,餘波未了
結束在南方的旅程後,格里芬回到家鄉,潛心寫下旅行遭遇,並以文章形式刊出。他的經驗與勇氣使他獲得媒體紛紛邀約採訪,但威脅電話與家鄉居民的沉默卻讓他深陷不安。
一九七六年,結語
在《...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