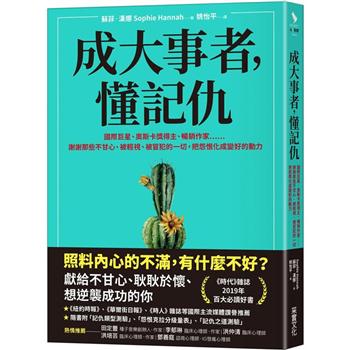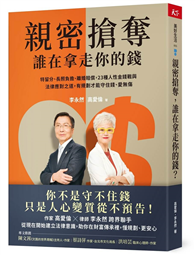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羅伯.史登的圖書 |
 |
$ 276 ~ 333 | 黑格爾與《精神現象學》【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羅伯.史登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3-28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黑格爾與《精神現象學》[1BZ4]](https://img.findprice.com.tw/book/9789571161082.jpg) |
$ 90 ~ 285 | 黑格爾與《精神現象學》[1BZ4]
作者:羅伯.史登(Robert Stern) / 譯者:林靜秀、周志謙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10-12-2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56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