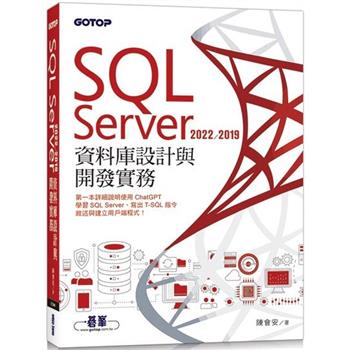社會學大師高夫曼的寫作以公眾為對象,而不局限於學院人士。《精神病院》這本富含人性關懷的扛鼎之作,不僅蘊藏豐富的洞察力及深具啟發性的概念,更具體詮釋何謂「公共社會學」的力量——掀起全美去機構化的風潮,說服政府官僚們同意讓社區重新擁抱「精神病患」。《精神病院》出版迄今超過五十年,早已經跨出了社會學而進入其他各個領域,可說是歷久彌新。環視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各式各樣的全控機構不減反增,高夫曼的睿智揭露,將再次引領我們透視各種被遮蔽的隱藏世界。
本書由四篇論文組成。第一章〈論全控機構的特質〉,針對機構中的社會生活進行總體考察,大幅引用了兩個例子——精神病院和監獄。本章說明其餘章節將仔細發展的課題,也指出這些課題在整體討論中的位置。第二章〈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針對尚未成為被收容者的人,考察「機構化」對於他們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哪些初步影響。第三章〈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關注人們期待被收容者對一個銅牆鐵壁的「家」表現出什麼樣的依戀,也考察了被收容者透過什麼方式讓自己和這些期待保持某些距離。第四章〈醫療模式與精神收容〉,則回到機構人員身上,以精神病院為例,來考察醫療觀點在向被收容者呈現其處境時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簡介:
高夫曼(Erving Goffman)
當代美國社會學大師。1922年生於加拿大愛博他省(Alberta)的曼維爾市(Manville),195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賓州大學。1982年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高夫曼曾是全球薪水最高的社會學教授,但一生不立學派、不願接受訪問,甚至連照片都極少。在量化分析大行其道、鉅型理論稱霸的年代,他的身影穿梭在小島、精神病院、賭場等地,一步步探索從沒人認為重要的「面對面互動」領域,讓這個新的視野誕生、開展,以致影響後世甚巨。著作包括《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精神病院》(Asylums, 1961)、《相遇》(Encounter, 1961)、《公共場所的行為》(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1963)、《污名》(Stigma, 1963)、《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 1967)、《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 1969)、《公共場合的關係》(Relations in Public, 1971)、《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1974)、《性別廣告》(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6)、《談話的形式》(Forms of Talk, 1981)。
譯者簡介:
群學翻譯工作室(翻譯)
萬毓澤(校訂),現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國立中山大學特聘年輕學者。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這些年,全控機構只增不減,我們察覺了嗎?
陳惠敏(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第一次閱讀《精神病院》(Asylums)是1999年就讀清華人類所開始進入療養院急性病房進行碩士論文田野研究時,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著作。當時有幾條線索必須追尋,但直到我讀到了高夫曼的《精神病院》,才恍然大悟,這可不就是我想要進行的研究嗎?高夫曼的提醒,對於當時經常困窘在田野情境和個人生存狀態的自己,有了一個自此安身立命的方式。
如同高夫曼所說,「所有關於精神病人的專業文獻,都是採取精神科醫師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在社會上而言,落在天平的另一端。」(頁3)那麼天平另一端是什麼景致?那便是社會學興趣之所在了。
我想由三條線索來看待高夫曼此書的意義。首先是在方法論上的斟酌;再者是高夫曼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s)研究,所帶出的社會學知識何在?最後,社會學者如何將社會學的知識趣味與信仰同時在面對現實社會時,恰如其分地返身其中,也就是社會學從業員的公共參與/介入(engagement)。
高夫曼認為,想要忠實描述病人的處境,就勢必得呈現片面的觀點。從當時到現在,他都這麼相信:「任何人類團體(囚犯、土著、飛官或病人)都會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是有意義的、合理的,且一旦你靠近它,就變得再正常不過;此外,若想要瞭解這些世界,一個好的方式是讓自己與那些成員為伍,去體驗他們由各種瑣碎的偶發事件所串起的日常生活。」(頁2)他自承這樣的研究方法及其應用有明顯的限制,他並沒有讓自己更為投入(committed);他假定,「若要針對某些命題蒐集統計上的證據,其所需的角色和時間,會妨礙我蒐集病患生活組織紋理的資料。」(頁2)瞧!多麼偏頗而不「客觀」的研究方法啊—既未收集所有相關人士的聲音,取材的樣本母數如此不足,樣本對象如此限定(就是精神病人!),也沒提出什麼宏大理論見解,只用細瑣的互動與生存策略來部署—可這就是「他們」(又何嘗不是我們)活生生的生存處境。
1961年《精神病院》(英文版)出版的同年,在彼岸的法國發行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博士論文《瘋癲與文明:古典時期瘋狂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法文版),兩本書討論的正是同一議題,而後續的學術生產和引發的討論卻大不相同。關鍵的劃異或許正由於高夫曼的繁瑣細節難以被把玩品味結晶成抽象的某些強概念,而他描述出來的全控機構(尤以精神病院和監獄為主)生活,總令讀者有太多與自身生活的聯想—跟我(的職場生活、軍隊生活、學術生活……〔歡迎繼續表列〕)也差不多嘛!
和傅柯在英語世界的流通(含英譯本和二手詮釋)相比,高夫曼顯然被低度評價。高夫曼的思想理路雖以戲劇分析開始(日常生活的表演),不過在他所布置的理論鋪設中,撐開了一個關於結構性和集體的關切,如那些所謂的自我表演所遭遇的是規範(norms)、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並愈來愈著重於社會儀式的重視,強調透過儀式作為一種確立位置的機制,維持了社會結構的正當性。高夫曼理論裡的兩個重要面向是:共同在場(co-presence)和遭遇(encounter),而這是在許多社會裡都能發現的特性,透過高夫曼的著作去透視的是許多世界而不只是一個世界。他的社會互動關鍵特徵分析常會帶出一些以往不被視作社會學關鍵議題(但現在當然是當代議題)的思慮,諸如信任(對緊張的修補等)、親密關係的發生機制、區域化概念在意義、規範和權力之間所構成的複雜關係中運作、對於嘲諷(cynical)的觀點、污名者道德生涯(moral career of stigmatized)等等。高夫曼並非認為權力不重要或不具影響,而是難以離開日常生活來表現。
高夫曼對於細節與經驗的觀察、描述與關切,卻無損其建構整體感與分析的能耐,正是他在社會學知識上的基進意義。全控機構真的如你所想般的容易理解,這種研究不是很好做嗎?(不就是一語帶過的「社會控制」嗎?人都帶到你面前了,方便又簡單,怎麼可能做不好?)高夫曼關心的是個人在特定位置(specific location)與他人進入或傾向於某種社會關係。科學哲學家哈金(Ian Hacking, 2004)曾比較過傅柯與高夫曼的著作思想,他就認為,一般對傅柯的研究裡欠缺了對「論述的形式如何變成一般人生活」的理解,或甚至「如何機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並成為機制結構中的一部分」的作用過程。而對高夫曼的研究裡則欠缺了對「他所描述的機制如何進入人類並內化」和「構成的結構是什麼」的理解。
最後,我想要從社會學從業者如何具有公共性來談高夫曼的啟發。他說:「我為我們學科的狀態辯護……如果要珍視社會學的概念,就必須把每個概念回溯到最適合運用它們的地方,看看這些觀念可以引導到什麼地方,然後迫使它們揭露其他的相關概念。或許就像是拿不同的外套讓孩子們保暖,比讓他們在一個華麗的帳篷裡發抖還要好。」(頁6)高夫曼寫作《精神病院》的過程中,也親身參與了美國對於精神疾病社會改革運動,包括回歸社區與機構化的辯論之中。固然時至今日,這仍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議題,然而,高夫曼在半世紀之前從社會學知識興趣和研究中返身公共參與介入的身影,迄今依然醒目。
社會學者當如是,以此自許,並與同業們共勉之。
參考書目
Hacking, Ian. 2004.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Erving Goffman: Between Discourse in the Abstract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 in Economy and Society 33(3): 277-302.
推薦序:歷久彌新的《精神病院》
陳嘉新(精神科醫師、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我第一次接觸《精神病院》這本書是在念博士班的時候。那一次我去社會醫學討論會報告一個反覆住院的慢性躁鬱症病人個案,我說明這個病人如何在多次住院的過程中,學會用住院這種方式來處理她生活面臨的壓力;而精神醫療中以再住院率或者復發次數做為一種治療效果好壞的指標,對這個病人來說並不恰當。因為這種評估復原程度的指標,可能掩飾掉生病者的努力,無法看見他如何經由住院這種方式去因應生活中的日常暴力與苦難。引入高夫曼對於全控機構與自我形塑的觀點,讓我能夠以更多角度思考生病住院對於一個人的意義。
高夫曼作為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在他另一本著作《污名》(2010年群學出版,曾凡慈翻譯)的導讀裡,孫中興教授已經將他的生平與作品略作介紹,我在這邊就不重複,請讀者自行參閱對讀。
相較於巨觀社會學大開大闔的分析尺度,象徵互動論的微觀切入更像是繡花針法,但是批評力道則不遑多讓。讀者若是細讀本書內文,當可領受這種分析取向的綿密纖細、深入淺出。《精神病院》雖命名如此,不過其分析對象也可以包括監獄甚至寄宿學校等機構。高夫曼觀察並歸納當中的人物在機構的條件下如何形塑自我面貌與發展道德生涯,並據此提出理論。全書的四大章節中,第一章開宗明義地說明了全控機構的操作;第二、三章則說明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與個體調適過程當中的反抗與自我形塑,最後一章則考慮醫療觀點如何將被收容者的處境呈現給他們。高夫曼在本書中以其銳利眼光與分析力徹底拆解了機構內的人類處境,進而提出對於人類自我(self)的洞見:「我們身為一個人的感受,來自於自己被捲入更大的社會單位;我們的自我感來自於我們抗拒拉扯的各種微小途徑。」(頁310)這讓我想到以往還在做心理治療的時候,不時需要處理個案在榮格(Carl Gustav Jung)所謂個體化過程(individuation process)產生的困難;後來閱讀本書時,我不禁拍案叫絕,因為這段話幾乎是闡述個人與群體之間在歸屬感與自我感之間糾結纏繞的最佳描述。
在榮格心理學的學說中,個體化被想像成是以不同象徵標誌的個體發展與整合過程,那是一個不斷向自己前進的內在之旅;然而在高夫曼的社會學架構底下,個體自我的建立卻是個不斷跟外在互動而遞嬗變遷的過程。不同的學術取向,意味著不同的自我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of selfhood),相互對照之下,自我成形的多重面貌便油然而生。
儘管是微觀出發,但是高夫曼這種由下而上的象徵互動論取向並沒有落入以管窺豹的困局。讀者如果細讀本書,當可感受全控機構裡的人如何在體制規範的限定下反應、協商與抗拒,並在這些展現能動性(agency)的行動中塑造了樣貌繁多的自我,開展了軌跡互異的生涯。這樣的分析筆法將個人與群體細膩地疊繡在一起,具體地展現社會性與結構如何在個人互動中逐漸成形的過程。對照社會學家史特勞斯(Anselm Strauss)闡述的概念—「協商而成的秩序」(negotiated order),當可窺見此取向的學者如何在理論上調和結構與能動性之間的張力。
高夫曼在《精神病院》中具體地提出了象徵互動論對於自我、體制、機構、調適過程等等的分析,也經由這樣的分析,批判了當時的精神醫療實作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體制。因此這本書不只應該被社會科學的學生閱讀,也應該被這些受指涉的專業閱讀,包括精神醫療工作者、監獄工作者等等。事實上,《精神病院》出版迄今超過五十年,早已經跨出了社會學而進入其他各個領域,可說是歷久彌新。
最後給讀者一點小小建議,如果您想要對偏差狀態的社會控制更進一步了解,也應該將本書與傅科(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與《規訓與懲罰》對讀,相信更能夠領會這種現代性區隔正常與異常的機制,並且反思這些機制在當下以怎樣的面貌影響著我們作為一個人。
名人推薦:推薦序:這些年,全控機構只增不減,我們察覺了嗎?
陳惠敏(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第一次閱讀《精神病院》(Asylums)是1999年就讀清華人類所開始進入療養院急性病房進行碩士論文田野研究時,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著作。當時有幾條線索必須追尋,但直到我讀到了高夫曼的《精神病院》,才恍然大悟,這可不就是我想要進行的研究嗎?高夫曼的提醒,對於當時經常困窘在田野情境和個人生存狀態的自己,有了一個自此安身立命的方式。
如同高夫曼所說,「所有關於精神...
章節試閱
第二部 醫院的地下生活
資源
現在我要另外說明的是,被病患拿來當成次級調適的資源和材料。
Ⅰ
首先我所要提到的是代用品/權宜之計(make-do)的盛行。在每個社會機構中,參與者使用可取得的物品的方式及其目標,並不是官方所樂見的,因此更動了為這些人計畫好的各種生活條件。其中涉及的,可能是具體改造一個物品,或只是不正當的使用脈絡,而兩者都為魯賓遜漂流記式的主題提供了簡單的例證。監獄裡有一些明顯的例子,包括把湯匙鎚製成一把小刀、把墨汁從《生活》雜誌裡榨出來、把習作簿拿來當成賭注條、用各種方法點燃香煙—比如從電燈插座、手工鐵盒、拆成四段的火柴引出火花。雖然這種轉變過程是許多複雜實作的基礎,但當實作者不涉及他人的時候(除非是學習或教導這方面的技術),也就是當實作者自己消耗他生產的東西的時候,這種過程才最為明顯可見。
在中央醫院裡許多簡單的代用品,是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的。例如,病患往往把直立式的暖爐拿來烘烤他們自己剛在浴室的洗手台洗完的衣物,這構成了一道私人的、原本只有機構在乎的洗衣循環。在有硬板凳的病房裡,有時當他們躺著的時候,會把捲起來的報紙擱在脖子和木頭板凳中間。有時他們會用同樣的方式捲起大衣和毛巾。住過其他收容機構的病人,在這個情形之下會使用更有效的物品:鞋子。在病房之間的移送過程中,病人有時會把私人物品裝在枕頭套裡,再把枕頭套上端打個結,而在某些監獄裡,這種做法算是半正式的。有些面臨老化的病患幸運地擁有私人臥房,他們可能會把一條毛巾墊在洗手台底下,把洗手台改造成一個書桌,那條毛巾就可以用來保護雙腳,以免接觸冰冷的地板。假使有些較老的病患不情願或者不方便移動,有時候就會運用策略去規避如廁的任務:在病房裡,他們會在蒸汽式的暖爐上小便,這樣便不會留下太多擦不掉的痕跡;在每週兩次到理髮師那邊剃鬍子時,他們會趁病房人員不注意,把毛巾桶當成尿壺使用。在後段病房,各個年齡層的病人,有時會隨手拿著紙杯,把它們當成痰盂和煙灰缸,因為與其制止他們吐痰或是抽煙,病房人員有時更在乎地板的整潔。
在全控機構裡,這些代用品的焦點往往會聚集在某些特定的範圍。其中之一便是個人的打扮—透過各種手段伎倆,以合宜的面貌呈現給別人。比如,據說修女會把黑色圍裙披掛在窗戶玻璃的後面,就變成一面鏡子—修女可以用這面鏡子來進行平常被禁止的自我檢查、修正及認可。在中央醫院裡,衛生紙有時候會被「妥善處理」(organized);它們會被整齊地撕下來、疊好,然後讓人攜帶在身上。講究整潔的病人會辯解這樣一來衛生紙便會變成好抽取的「舒潔」。同樣地,在炎夏的幾個月裡,一些男性病患也會把醫院分發的卡其褲整齊地裁剪成夏季短褲。
Ⅱ
以上所提到這些簡單代用品的特色是,一個人不需要投入場所的正式環境中,就可以運用它們。以下我要說明的這套操作方式,在機構的正當環境中,多少意味著更多的活力。可以維持正當活動的精神,但有時候會超過它們所被要求的程度。我們看到的是延伸和應用一些原本被拿來獲得正當滿足感的既有資源;或是為了私人的目標,利用整套例行的官方活動。在此我所要闡明的是「搬弄」體制("working" the system)。
在中央醫院裡,或許搬弄體系最基本的方式,展現在後段病房裡那些一直不斷稱病、拒絕遵守紀律的病人身上。他們這樣做,顯然是為了吸引病房人員或是醫生的注意,這樣一來就可以與他們產生社會互動,不論這樣的互動是多麼紀律嚴明。
然而,醫院裡大多數搬弄體系的技巧,似乎都和精神疾病沒有密切的關連。有的技巧是一整套和取得食物有關的精巧操作模式。舉例來說,在一間大自助餐廳裡,九百名男性慢性病患必須輪流用餐,有些人會攜帶自己的佐料,替自己的食物調味;他們會把裝了糖、胡椒、番茄醬的小瓶子放在夾克的口袋裡。如果咖啡是用紙杯裝,有些病人就會把裝了咖啡的杯子裝到另一個紙杯中來保護自己的手。有些日子裡有香蕉可吃,他們就會從牛奶罐裡面舀一杯牛奶,這原本是用來補充奶製品的飲食,但這時候他們就會把香蕉削成一片片,撒上一點糖,開心地吃一道「像樣的」甜點。有時候,病人會先把一些受歡迎又方便攜帶的食物(像是法蘭克香腸或是豬肝)用紙巾包起來,接著回去拿「第二份食物」,然後把〔包起來的〕第一份食物帶回病房當宵夜。有些病人會在供應牛奶的日子帶著空瓶子去填裝,也同樣會外帶一些牛奶回病房。如果想多吃一點菜單上某些特定的食物,有個伎倆就是只吃那樣東西,然後把剩餘的飯菜全部倒進便桶裡,再回去(如果被允許的話)盛滿滿的一盤飯菜。有些准假的病患會被指定在自助餐廳裡先用餐,然後在夏天晚上,把起士夾在兩片麵包中間包起來做成三明治,然後在病患餐廳外面舒適地享用,還可以買杯咖啡。准假到城裡的病人有時候更過分,會在當地的藥店購買派餅和冰淇淋。在另一個醫院較小的餐廳裡,有些病人(正確地)深怕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拿不到第二份食物,便會把盤上的肉塊拿出來夾在兩片麵包裡,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然後立刻回去排隊等第二份食物。有時候,當這些有遠見的病患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時,才發現其他的被收容者已不費吹灰之力地帶著他們留在桌上的第一份食物逃跑了。
為了更有效地搬弄體制,必須充分瞭解體制。在醫院裡面,很容易看見這些知識怎麼被運用。例如,很多准假放風的病人都知道慈善義演的戲院戲碼結束,人們魚貫湧出戲院時,大門外面可能有人會分送香煙和糖果。如果感覺戲碼無聊,有些病人就會在結束前幾分鐘到門外報到,以免和其他病患人擠人;而有些人還會設法排好幾次隊,讓整個場子比普通時候更值回票價。工作人員當然知道這些伎倆,醫院舉辦全院病患舞蹈活動的時候,遲到的人會被鎖在外面,這個措施是因為料到他們算準時間來,分明只是想要來吃個東西就走人。猶太人福利會的女工作人員在每週禮拜後提供早午餐,有個病人宣稱「只要在對的時間來,便可以錯過禮拜,拿到午餐」。另一名病人則注意到一項鮮有人知的事情,即醫院裡有一裁縫團隊專門修補衣服,他會把自己的衣服拿去給他們修改合身,然後奉上一兩包香煙或是小錢當成回饋。
時間掌握(timing)對其他搬弄體制的手法來說是很重要的。比如紅十字會捐贈的舊書和小冊子,會被卡車載到醫院廣場上的活動中心,然後圖書館經手把這些讀物分發給病人或是病房。有些熱衷閱讀的病患知道卡車確切例行停靠的地方,會到那個地方去等待,為的是拿到他們的首選讀物。有些病人知道中央病房烹調給慢性病房的地下食物在何時運送,有時會蹲在幾乎快到卡車底盤的地方,希望可以搶到桶子裡一部分的食物。另一個例子和資訊的取得有關。在大型的病患餐廳,餐點會優先供給那些年老不能動彈的病患。能夠走動的病患如果想知道當天有什麼吃的,要去自助餐廳還是從病患食堂買些三明治,就會不時地往這些病患的病房窗戶探頭,在對的時間獲悉菜單的內容。
撿破爛則是另外一個醫院裡搬弄體制的例子。一些病患會在垃圾收集時間之前,到附近的垃圾場四處走動。他們會掀開傾倒在大木箱垃圾的最上面那一層,在裡面翻找食物、雜誌、報紙,還有各式各樣因為供不應求、或是必須畢恭畢敬要求病房人員或其他高層才能得到(這些都是取得這些物品的正當方式),因此對蒐集者來說有意義的東西。在辦公室的走廊裡,院方人員會把茶碟當成煙灰缸使用,病患也會在這些茶碟裡面翻找還可以用的煙屁股。在開放的社區裡當然也有這些撿破爛的人,而似乎任何一個蒐集並銷毀用過物品的大型系統,都能提供管道讓人從中勉強過活。
搬弄體制可能會導致一些擅於利用伎倆的病患吹噓自己的英勇事蹟,這樣便很難讓人視之為典型的次級調適。若某種醫療服務提供了兩種恢復病房,一種是上鎖的,另外一種是開放的,一個病人便會宣稱他設法從上鎖的病房換到開放病房,因為開放病房裡的撞球桌桌布比較好;另一個病人的宣稱則剛好相反,因為他覺得上鎖的病房裡的社交性比較強,因為有些病人被強迫留在那裡;另一個准假放風的病人,說自己會定期找藉口從醫院的工作崗位上離開,甚至可以拿到一些車資到鎮上去;他宣稱只要到了鎮上,他就可以閒晃一個下午、看場電影。
我也想要額外說明,擁有其他剝奪經驗,或是比較會動歪腦筋耍詐的病人,通常很快地就會透露出他們知道怎樣搬弄體制。舉例而言,一個有待過列克星敦(Lexington)的病人,在入院的第一個早上就拿到了捲煙草的材料,取得鞋油並且幫自己的兩雙鞋子拋過光,他也發現哪個夥伴蒐藏了一堆偵探故事,會利用即溶咖啡和熱水龍頭讓自己有充足的咖啡可喝,他也會為自己在團體治療時間中找到一個位置,挺直腰桿等待幾分鐘,準備開始把自己塑造成團體治療裡面的積極角色。
目前我所提到搬弄體制的方法,只限於對操作者有利,以及和他們關係密切的人有好處的那些。在許多全控機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為了集體利益而設計的操作手法,但是在精神病院裡,集體搬弄體系的方法卻似乎不那麼常見。在中央醫院裡面,幾乎都是從機構內部那些像監獄一樣的機構(「監獄大廳」〔Prison Hall〕—專門用來收容那些有刑責的精神病患)出來的人在維繫集體的次級調適。例如,一個都是前囚犯的病房,在用餐時間之前會送其中一個成員到廚房去,端回盛滿熱食、遮蓋起來的托盤;否則經過緩慢的地下通道,食物早就變涼了。
在思考「搬弄體制」過程的同時,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考慮到「住院治療」這件事本身也會被設計。比如說,醫院員工和被收容者有時會雙雙宣稱,某些病人之所以入院,是為了躲避家庭和工作職責,或是為了獲取免費的醫療和看牙醫的機會,或是躲避刑事責任。但我無法說明這些聲明的可信度。也有些准假到城裡放風的病患會說,他們在幾回豪飲之後,會把醫院當成拿來讓自己清醒的水缸,這樣的說法顯然會被宣稱可治療急性宿醉的鎮靜藥物所助長。還有其他放風的病人願意拿比一般人最低工資還低的薪水,打半職的工,以免費的醫院食物和住宿為基礎,確保自己的競爭位置。
還有一些較不傳統的搬弄醫院體制的方法。每個社會機構都會盡可能讓參與者能夠面對面接觸,或者至少增加這類接觸的機會,在醫院還有其他機構之中,這樣的接觸機會提供了次級調適的基礎。有一種會利用醫院的各種社會可能性(social possibilities)的病患,就是前囚犯:從監獄大廳釋放出來的犯人。這些人相對上都比較年輕,也往往具有都市工人階級的背景。一旦被釋放、回到真正的醫院裡,他們便獲得了更多愉快的工作,還有他們認為有吸引力的女病患。在另一個機構裡被稱作「院區老大」(campus wheels)的男人,多數都來自這樣的階層。另外一群這樣的團體便是黑人:他們之中有些人會非常渴望能夠跨越階級和膚色的界線,和白種病人打交道甚至交往,從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員那裡獲得一些他們在外界會被拒絕的、中產階級式的專業對話機會。第三個團體則為同性戀者:他們因為自己的癖好而被監禁,發現有單一性別的宿舍生活正在等著他們,也伴隨著性的機會。
某些病患搬弄醫院體制的其中一種有趣的方法,和他們與外界人士打交道有關。病患對與外界互動的關注,似乎和他們在醫院中所身處的類似種姓制度的位置,以及和「瘋狂」這種污名標籤聯繫在一起的種種迷思有關。雖然有些病人聲稱沒有辦法和非病患自在地相處,但其他病人的表現卻像是一枚錢幣的另一面,他們覺得和非病患來往事實上是比較健康的,而且會建議這樣做。再者,跟機構人員相比,外界的人也比較不會攻擊、冒犯他們的身分;外人不清楚病患的位置有多麼低下。最後,有些病人受夠了和其他病患談論他們監禁生活的日子,而期望和外界的人對話,藉此遺忘病患文化。和外界人士的關連可以確保一種自己不是一名病患的感覺。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醫院的廣場和活動中心,會出現某些「蒙混掩飾」(passing),使病人覺得自己和神智正常的人真的沒什麼區別,而且神智正常的人也不是那麼聰明。
在醫院的社會系統裡有若干策略性的地點,可以讓病患和外界產生接觸。有些住院醫師青春期的女兒,會和那些佔據醫院網球場的放風男病患和實習護士形成小的交際圈。在網球比賽正在進行或是結束的時候,這群人會坐在附近的草坪上玩起騎馬打仗,總而言之,他們維繫著一股非醫院的調性。類似的狀況是,在醫院舉行慈善舞會的晚上,會吸引外面來的一些年輕女性,一兩個男病患便會親近這些女生,表面上從她們身上獲得非醫院的回應。因此,實習護士們理應在住院病房裡接受護理訓練,但是有些年輕的男病患會時常和她們打牌或玩其他遊戲,這時候維繫的便不再是護理的精神,而是約會交往的關係。而在一些比較「高級」的心理治療之中,像是心理劇或團體療法,有些來訪的專家會列席觀察最新的治療方法;這些人也提供了病患一些資源能夠和正常人互動。最後,被選為醫院裡明星棒球隊的病人,當他們和社區隊伍比賽的時候,能夠享受在兩個敵對的隊伍間發展出來、使雙方和觀眾分離開來的那種同袍般的特殊情誼。
第二部 醫院的地下生活
資源
現在我要另外說明的是,被病患拿來當成次級調適的資源和材料。
Ⅰ
首先我所要提到的是代用品/權宜之計(make-do)的盛行。在每個社會機構中,參與者使用可取得的物品的方式及其目標,並不是官方所樂見的,因此更動了為這些人計畫好的各種生活條件。其中涉及的,可能是具體改造一個物品,或只是不正當的使用脈絡,而兩者都為魯賓遜漂流記式的主題提供了簡單的例證。監獄裡有一些明顯的例子,包括把湯匙鎚製成一把小刀、把墨汁從《生活》雜誌裡榨出來、把習作簿拿來當成賭注條、用各種方法點燃香煙—比如從...
目錄
推薦序:歷久彌新的《精神病院》/陳嘉新
推薦序:這些年,全控機構只增不減,我們察覺了嗎?/陳惠敏
序
導論
論全控機構的特質
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
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一間精神病院中的各種生存之道
醫療模式與精神收容:一些關於修補式行業變遷的筆記
註釋
推薦序:歷久彌新的《精神病院》/陳嘉新
推薦序:這些年,全控機構只增不減,我們察覺了嗎?/陳惠敏
序
導論
論全控機構的特質
精神病患的道德生涯
公共機構的地下生活:一間精神病院中的各種生存之道
醫療模式與精神收容:一些關於修補式行業變遷的筆記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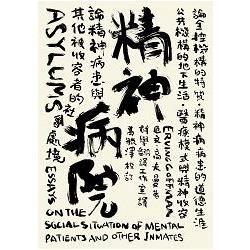

 共
共  工作室,是一處創意生產和工作的空間,不單只是辦公室,通常規模又不比工廠般非人手大量生產。工作室的名稱,可以是: 電腦軟體或網絡平台的名稱,例如:Macintosh Programmer's Workshop 視覺藝術工作室,例如:觀塘藝術工作室 軟體生產商,例如:微軟遊戲工作室 多媒體工作室,例如:動畫工作室: 工畫堂工作室 日本動畫工作室列表 四葉草工作室 皮克斯動畫工作室 全效工作室 吉卜力工作室 西木工作室 亞婆井工作室 卓音工作室 拉拉資推工作室 雲雀工作室 黑名單工作室 黑島工作室 螢火蟲工作室 藍天工作室 漫畫家與其助手群的工作場所 小規模的傳統工藝的工作場所,又稱為工坊,例如:陶瓷、琉璃
工作室,是一處創意生產和工作的空間,不單只是辦公室,通常規模又不比工廠般非人手大量生產。工作室的名稱,可以是: 電腦軟體或網絡平台的名稱,例如:Macintosh Programmer's Workshop 視覺藝術工作室,例如:觀塘藝術工作室 軟體生產商,例如:微軟遊戲工作室 多媒體工作室,例如:動畫工作室: 工畫堂工作室 日本動畫工作室列表 四葉草工作室 皮克斯動畫工作室 全效工作室 吉卜力工作室 西木工作室 亞婆井工作室 卓音工作室 拉拉資推工作室 雲雀工作室 黑名單工作室 黑島工作室 螢火蟲工作室 藍天工作室 漫畫家與其助手群的工作場所 小規模的傳統工藝的工作場所,又稱為工坊,例如:陶瓷、琉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