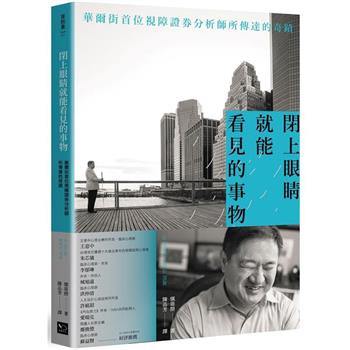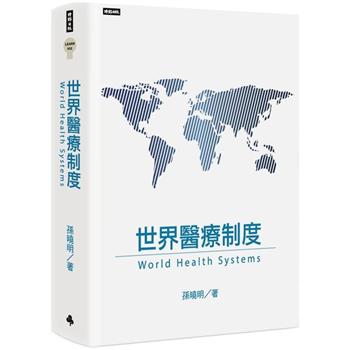序
他是瘋狂的戰慄者,他是太空人
(一)
除非這世界又要誕生另一位巨星,除非這個物質的時代將要關閉最後一道想像之門,否則麥可.傑克森的死實在太令人惋惜。當年,傑克森以一張《瘋狂》(Off The Wall)橫空出世的時候,流行音樂的偉大偶像「貓王」提前兩年成了仙人;隨後不久,另一位神,也是那個時代的預言者
—約翰.藍儂中了地獄之彈。
麥可.傑克森是伴隨MV誕生的巨人,也是唱片工業製造神話的寵兒,更是打破性別極限的不可複製的稀世珍寶。
再過十七天,就是他復出江湖的日子;再過五十年,他依然是最偉大的流行音樂的標記。
他的突然逝去,留下了很多令人難以證實的疑惑,就像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只給他畫了一張黑色的臉。他是更愛卡通世界裡的孩子,還是現實世界的孩子?他聚積了雌雄共體的輝煌,他偷走了太空舞者的舞鞋,他把愛釋放了又偷偷地帶走,麥可.傑克森的眼神也從桀驁不馴逐漸向中性般的乖戾過渡。注定要在揮霍才華與能量之後面對夕陽,也注定要在驚恐的人生經驗中嘗遍痛苦的滋味。麥可.傑克森從來不是一個人文意義的預言家,他更是一個編織改變人生命運故事的強者,他不會給你帶來後工業時代的憤怒,他是流行殿堂裡的詠歎調,他用唱片銷量和 MV 收視率來樹立神話。他的誕生,給青年文化帶來了無窮的節奏快感和征服欲望。他為色彩絢爛的夢幻世界贏得了高分貝的迴響。二十世紀八○年代,瑪丹娜的出現和以「壞女孩」為標記的女性主義文化有關,而麥可.傑克森則是黑人文化回潮的象徵,人類挑戰太空的流行印記,高成本 MV 革命中的冒險符號,以及衝擊種族主義枷鎖的又一次凱旋之音。
他少年時代在「摩城之聲」的錄音也許過於遙遠,我們現在很少再提那些錄音的真正價值。那是一張張從黑人靈歌向迪斯可流行轉變的唱片,「傑克森五兄弟」是唱片界陰謀的一個環節而已,黑人的焦灼不安被一種虛幻的快感所取代,這是馬丁.路德.金的吶喊失敗後,在迪斯可舞廳裡被喚醒的燈紅酒綠的迷醉。但這一切是時代的華麗轉身。整個二十世紀八○年代流行樂的第一個關鍵字是—絢爛。終於需要一個人在舞步上和雷.查爾斯的鋼琴比滑動的速度,也需要一副能打破陰陽界限的嗓音。他的太空舞步,他的水晶手套和金屬裝飾的演出服,他那無與倫比的征服性令整個世界為之顫慄。從此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人間極品:麥可.傑克森的輝煌是工業的輝煌,是MV成為音樂家族成員後的里程碑。
麥可.傑克森的出現,是繼安迪.沃荷畫了一連串夢露和「貓王」之後,是繼黑人街舞和塗鴉藝術成就了一段交媾狂歡之後,西方流行文化最輝煌的一個座標。這個熱愛米開朗基羅的受難的身體更敏感於狂歡的意義,他的旋風式的舞臺表演,他那種將天真和邪惡同時迸發出光芒的才華,是二十世紀八○年代時尚文化變革中的絕妙一筆。
二十世紀八○年代,沒有人再在乎精神負荷對流行藝術的影響,差不多和麥可.傑克森同時影響這個世界的《星際大戰》意味著一次文化的痛快的撤離和逃避。我們注意到狄倫式的寓言和披頭士式的童話被翻了過去,在二十世紀七○年代的整整十年,西方流行音樂被享樂主義的思潮侵襲,人們更願意避世,而不願意複述現實的殘酷。他屬於那些在少年時代接受青春期變化的年輕人,他也屬於在二十世紀九○年代被卡通文化與西方流行樂侵蝕的中國年輕人,他給那些追求超酷的一代帶來了驚歎的想像,他也給獨生子一代帶來了傑克森式的叛逆和愛的洗禮。
他的胯部的抖動,也終於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成了黃色氾濫的代名詞。他和瑪丹娜同時被釘上了搖滾的十字架。
如果說,米克.賈格爾曾經代表了—聲音與憤怒,那麼,麥可.傑克森永遠是聲音與神話。
(二)
他有一半以上時間並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愛,他被傷害得越深,藏得也越深。與其說是麥可.傑克森製造了魔鬼般的神話,還不如說是可惡的媒體不斷地讓一個遠離舞臺中心的王者陷入深淵。他是那樣矛盾,永遠受困於肌體和靈魂的黑白之爭。他連續更新著唱片與演出報酬的紀錄,卻對曾經不為物質所動的中國心存嚮往,在二十世紀八○年代麥可.傑克森的音樂已經進入中國大陸的時候,他說:這是一個在精神上和自然統一的國度。
總是有太多人議論這個人後期的怪異與不端,想想唯有他自己才能永遠面對一身鬆弛而坍塌的肉體。這就像外星人的裝備套在了一個有呼有吸的人類一員的身上,流行文化的帝國大廈無法轟然倒下,也需在面具後面抽走光芒。他製造了把兒子舉出窗外的神經質行為,他也讓孩子們戴著口罩,戴著眼套走進一個帶有各種「細菌」的世界,他即使想與世隔絕,也無法隔絕自己存在的影子。
麥可.傑克森的打扮,還有他那尖利的嗓音,無不都在隱喻對性別以及人性的重塑。至於,他那著名的太空舞步也是從《星際大戰》到《 ET 外星人》,再到《回到未來》的升空體驗的綜合。這個一輩子喜歡彼得.潘的偉大藝人終究沒有離開他的加州「夢幻莊園」私人宮殿。
不知道那麼多被麥可.傑克森征服了的歌迷中,有多少人真正明白:麥可.傑克森是最不適合成為聚光燈下的寵兒的。他的童年更多地被殘暴的父親所統治,而那種出人頭地的少年夢想是以鞭打和母愛的隱退為基礎的。在日後麥可.傑克森最愛交往和心儀的女藝人中,往往都是年長的,從戴安娜.羅絲到凱薩琳.赫本,再到伊莉莎白.泰勒,她們給了他足夠的安全感,也給了他兒時缺憾的彌補。我們也確信,那個曾經雷厲風馳一般的「怪物」把自己包裹得很深,他是身體的影子,卻是靈魂的好奇者,而他的內心感受其實並沒有傾訴的地方。在音樂領域,他扮演了機器人時代的英雄,也擔當了物質揮霍時代的驕子,但在愛的領域,他只有失落與失敗。如果說,一個人的堅強表現在他的始終如一,那麼麥可.傑克森的生命音符的確是強大的。他只是把注意力從異性的身上更多地轉向孩子們,他知道,他可以和他們玩沒有欺騙的遊戲,可以和他們一起對未來世界充滿好奇。他是孩子們的小飛俠。
麥可.傑克森坦言,他曾對自己的臉充滿自卑。上帝就是這樣壓迫著任何一個試圖尋找完美的人的,一個世紀出一個的音樂天才,卻有一副虛弱到絕望的身體,他在皮膚上唱起了一段月光曲,他也在墨鏡的後面流淌出一條河。當青春年華不再是鏡子裡的常客,他身後那些不友好的鏡頭開始描摹他,把他形容為黑暗?的妖魔。這個在2001年或者2009年漫遊過太空的地球人,在聽到盧卡斯的女兒學會說的第一個詞是—麥可.傑克森時,激動得飛了起來。我終於明白,這個聲音?有飛翔感的男人為什麼顫慄的理由了,無論是超速的宣洩,還是委婉的抒情,他生命的根不在地下。在深夜的鏡子?,他那張臉一定美到不存在。上帝只讓他一個人去接近這份真實,就像他喜歡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弗洛斯特的那句詩:「從一片葉子可以看到整個世界嗎?」是的,從一片愛的葉子,我們看到了整個西方流行世界的飄零。
孫孟晉
2009年6月26日於滬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