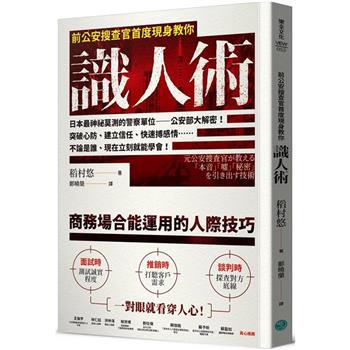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艾克絲頓‧貝茲-漢彌爾頓的圖書 |
 |
$ 110 ~ 359 | 愈少人認識我們愈好:一個關於背叛、家庭祕辛與身分盜竊的未解之謎 (電子書)
作者:艾克絲頓‧貝茲-漢彌爾頓(Axton Betz-Hamilton) / 譯者:朱崇旻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1-08-0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從十一歲起,便有人操控著我的身分──我的社會安全號碼、信用評分,甚至是我的名字。
在每一個真實生活層面上,我都被那名隱形的犯人擺布。
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個人」不只改變了我判斷的視角、我的日常生活,還包括我整個人。
犯人形塑了我的內在……
當被害妄想成了義務,沉默便成了對家庭破碎的責任。
她矢志要揪出父母口中的「身分盜竊犯」,人生更因此出現180度的轉變!
★2020年愛倫坡獎「犯罪實錄」得主。★
★真人真事改編,作者親自追查,在最難解的親子糾結之外,一樁最離奇的家族懸疑緝凶案。★
一位身分盜竊專家,
一場生命中最難以面對的背叛與創痛,
一個無論身體或心靈都孤立無援,卻奮力求生、不放棄追查真相的女孩。
她人生中輝煌亮眼的成就是因此而起,
與此交換的,是一場耗時半生、遊走在道德與倫理間的犯罪。
從孩提時代到長大成人,她始終走在一段驚弓之鳥般的逃亡旅途上,
而這幾乎摧毀了她。
╱╱╱
當家中郵件接連不翼而飛,取而代之的是法院和銀行通知,甚至是無預警斷電,
年幼的艾克斯頓腦海裡就時常迴盪著父親的叮嚀:
「如果有人進到院子裡,妳要想辦法保衛家園。」
母親則對艾克斯頓耳提面命:
「愈少人認識我們愈好。犯人很可能就是我們周圍的某人。」
◇◇◇
十一歲時,艾克斯頓的身分首度被偷。
十四歲時,為了把身分盜竊犯繩之以法,她不惜持刀追出家門。
十六歲時,厭食症狀開始找上艾克斯頓,接著是恐慌症。
十九歲時,她首次收到銀行專寄給她的報告,發現自己已信用破產。
二十二歲時,艾克斯頓申請上研究所,決定以「兒童身分盜竊」作為論文主題。
她心想,或許,只要以此為志業,她終能找出這個毀了她全家的罪犯……
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家庭的帳單不翼而飛,接著是個人身分遭到冒用。在網路普及前的六、七○年代美國,這並非新鮮事,卻會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偷走帳單的人輕易就能假冒當事者辦理信用卡或詐領財物,但這類案件卻因地界廣大、州法管轄差異而難以查緝。十一歲那年,艾克斯頓家裡的郵件開始失蹤,她與家人的身分被盜、信用破產,無論在何處都無法貸款,還有從天而降的追債人緊跟在後。艾克斯頓一家因而成了警局和銀行眼中永遠的詐欺犯。他們為此難以安居,白天若遇見熟人,便竭盡全力假裝一切毫無異狀;到了夜間,則用厚重的窗簾將世界隔絕在外,家中終年昏暗,甚至在庭院周圍加上木欄與掛鎖,只怕有外人潛入。但身分竊賊彷彿知道他們的行蹤,無論如何防範,竊賊總會再利用他們的個資犯案。最終,艾克斯頓一家完全切斷外界聯繫,而艾克斯頓的成長過程也因背負了太多無法為外人道的扭曲祕密,而形塑了她與眾不同的性格,甚至因此度陷入強烈的憂鬱與厭食。多年後,艾克斯頓成了身分盜竊的專家,矢志要抓到使家庭分崩離析的兇手......
作者簡介
艾克絲頓‧貝茲-漢彌爾頓Axton Betz-Hamilton
身分盜竊專家。因為從小就遭不明人士盜用身分,信用破產,影響她一生甚鉅,故而轉向研究相關犯罪主題,以破獲身分竊案為職志。她經常在會議上發表相關主題的演講,並因其研究、教學和服務獲得多項獎項。
艾克絲頓擁有消費者科學與零售產業研究(Consumer Sciences and Retailing)的碩士學位,以及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的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兒童身分盜竊和由家庭成員所進行的老年人金融剝削。她如今在南達科他州立大學任教。
譯者簡介
朱崇旻
曾在美國居住九年,畢業於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是以小說為食的謎樣生物,時時尋覓下一本好書。喜歡翻譯時推敲琢磨的過程,並認為無論是什麼題材的書,譯者都應該忠實傳達作者的立場。興趣包含寫小說、武術、室內布置和冬眠。聯絡請洽:joycechuminmin@gmail.com
|
 約翰·米爾頓,英國詩人,思想家。英格蘭共和國時期曾出任公務員。因其史詩《失樂園》和反對書報審查制的《論出版自由》而聞名於後世。
約翰·米爾頓,英國詩人,思想家。英格蘭共和國時期曾出任公務員。因其史詩《失樂園》和反對書報審查制的《論出版自由》而聞名於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