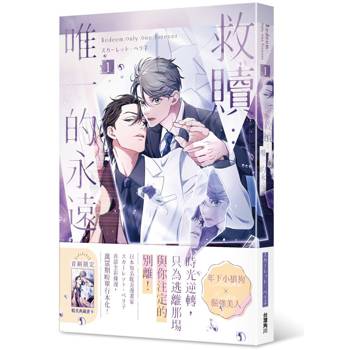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范容瑛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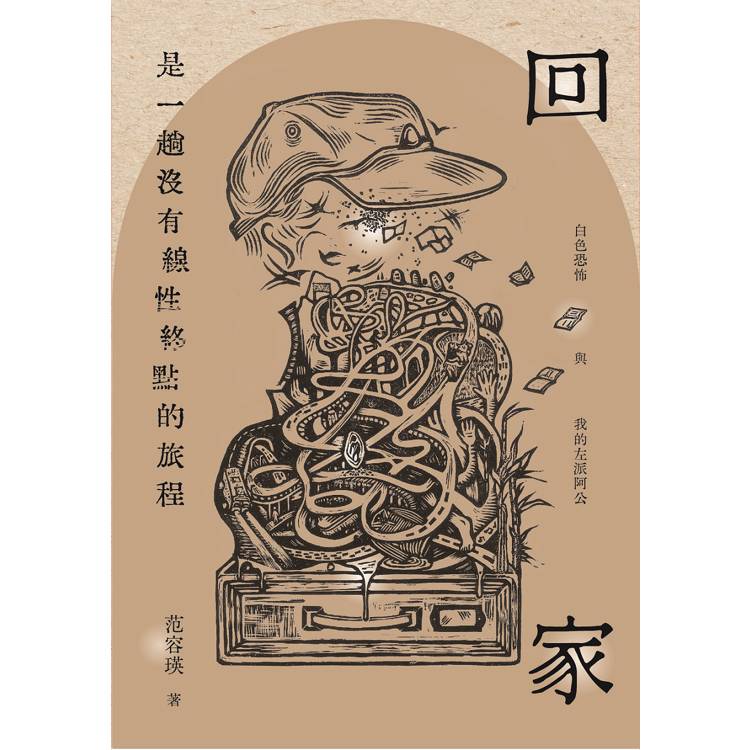 |
$ 283 ~ 414 | 回家是一趟沒有線性終點的旅程:白色恐怖與我的左派阿公【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范容瑛 出版社: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2-28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322 電子書 | 回家是一趟沒有線性終點的旅程:白色恐怖與我的左派阿公
作者:范容瑛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2-18 語言:中文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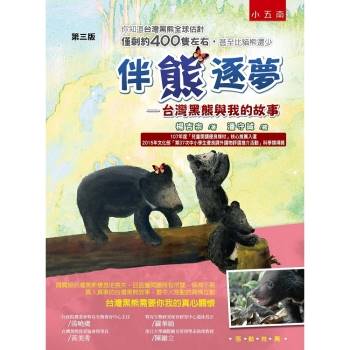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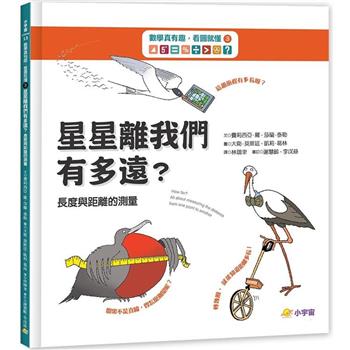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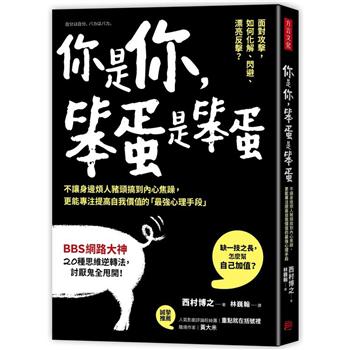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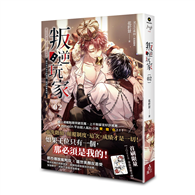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