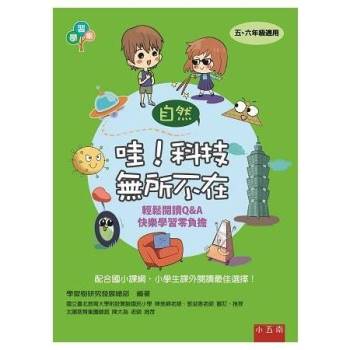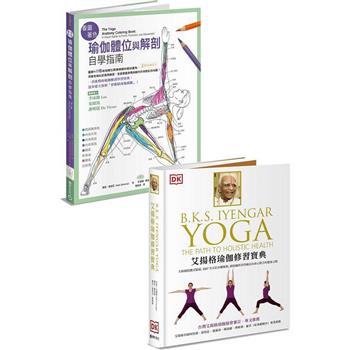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莉莉.布魯克斯-達爾頓的圖書 |
 |
$ 69 ~ 326 | 永夜漂流(二版):喬治.克隆尼執導電影原著小說,Netflix即將上線!
作者:莉莉‧布魯克斯-達爾頓(Lily Brooks-Dalton) / 譯者:康學慧 出版社:悅知文化 出版日期:2020-10-2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0頁 / 13 x 19 x 1.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二版  3 則評論 3 則評論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47 ~ 350 | 永夜漂流
作者:莉莉.布魯克斯-達爾頓 / 譯者:康學慧 出版社:悅知文化 出版日期:2018-12-03 語言:繁體/中文  10 則評論 10 則評論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達爾
 達爾,是鳥山明的原作漫畫《七龍珠》系列及其改編原作的動畫系列中登場的虛構人物。
達爾,是鳥山明的原作漫畫《七龍珠》系列及其改編原作的動畫系列中登場的虛構人物。 達爾是賽亞人民族的王子。在「賽亞人來襲篇」初登場,是侵襲地球的主要敵人。在「娜美星篇」為敵對的友方角色,其與弗利沙對抗的劇情屬於另一條的主線故事。「娜美星篇」完結後更隨著劇情發展逐漸融入成為主角群,並與同為賽亞人的主角孫悟空維持亦敵亦友的關係,在故事後期重要性近於第二主角。其名字的源自蔬菜。他的目標是超越孫悟空,成為宇宙最強的賽亞人。
在日本動畫版的聲優是堀川りょう,從《七龍珠GT》開始以「堀川亮」的名義表示。英語版則是克里斯托佛·沙巴特。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