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秋天,蘇.米勒開始照料她那被阿茲海默症侵襲的父親。她自認在所有兄弟姊妹中她是最不適合照顧父親的人,因為她始終無法從當中抽離開來,以致於那段期間發生的種種以及父親的一生,在日後都時時刻刻縈繞在她的心頭。
在書中讀者會發現,蘇.米勒腦海中清晰地殘存著最後照料父親那幾個月的時光,以及她父親生活的大量記錄。伴隨著憐憫、自我檢視、渴望從遺忘中搶救對父親的記憶……蘇.米勒藉由她的觀察天賦和精準的文字,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極為私密的個人歷程,但是最後讀者也會發現,這樣的歷程同時也是全天下父親與女兒共同的故事。蘇.米勒的父親詹姆斯.尼可斯( James Nichols)是一位牧師,也是普林斯頓神學院的退休教授。蘇.米勒在書中將父親的過往生活,包括宗教信仰、對孩子的無私奉獻與耐心、對週遭可笑的事物仍展現興趣、願意當個忠實聽眾、在最後的時日中仍謹守宗教生活的規矩……等,皆鮮明地記錄在本書當中。
她回憶起看著父親經歷痛苦的諷刺情景——一個宗教歷史學家,受到病魔無情的對待,摧毀了一切,包括他的時間概念、過去的生活以及存在價值。她敘述在父親患病的過程當中她獨自對抗冷漠的醫生、獨自做決定時的猶豫與徬徨,以及她隨著父親的病症越來越嚴重、不斷地發現阿茲海默症是如何地摧殘一個人原有的個性特質……。她後來藉由記憶陷入反覆的思考,想要從父親漸漸消逝的生活中的各項軸線,交織出一份完整且真實的敘事。
蘇.米勒在書中也剖析自己寫作本書的心路歷程。在追憶父親的過程中,她不僅扮演著作家的角色,也是書中主角的女兒,她提到:「寫作的確是種樂趣,而且寫作也確實聯繫了我和父親。寫作把父親帶回我身邊,即使我是用寫作去描述父親的消失。」回憶父親病痛過程的種種固然讓人心痛,但某種程度也是蘇.米勒釋放、療癒以及對抗恐懼的過程。
希望本書能撫慰同樣也在掙扎對抗的為人子女,期盼他們能從這樣的悲傷與矛盾中走出來。
作者簡介:
蘇.米勒( Sue Miller)1943生於美國芝加哥,為美國暢銷小說作家。蘇.米勒出身於一個學術與宗教氣息濃厚的家庭,從小就很喜歡閱讀和寫作。她大學就讀於哈佛大學的雷德克里夫學院,畢業不久後就結婚了,當時她只有二十歲,之後她做過許多奇奇怪怪的工作。
1971年她與丈夫離異,接著住在麻州的劍橋市,扮演單親媽媽的角色長達十三年,在這段期間,她除了工作、學習鋼琴,更專心地寫作。
由於獨自一人照顧孩子,蘇.米勒能夠寫作的時間並不多;她的第一個故事於1981年出版,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就在波士頓地區教授寫作課程。
1983-84年間,她獲得哈佛大學雷德克里夫學院的 Bunting Fellowship,這也是她的第一本小說 The Good Mother於1986年出版的契機。接著她在九○年代陸續出版了 While I Was Gone、 The World Below、 The Distinguished Guest、 For Love、 The Good Mother等書。
從蘇.米勒的第一本書 The Good Mother出版後,她的許多作品皆是在記敘一種喧鬧的、衝突不斷的美國家庭生活,因為蘇.米勒覺得在家庭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末是所有人類社會與經濟活動中最具吸引力的題材。
蘇.米勒於1985年與作家 Douglas Bauer結婚,目前兩人離婚。在波士頓住了十二年之後,她回到劍橋市,因為她覺得這裡聚集了最多的書店。
譯者簡介:
史茵茵
台大外文系學士,哈佛教育碩士。因為興趣廣泛,嘗試過許多不同的跑道,最終發覺唯有歌唱和文字才是最愛。喜歡歌曲 The Girlfrom Ipanema的慵懶,小說 Norwegian Wood、冷静と情熱の間的錐心。想念波士頓的春天,也擁抱每個新的契機。
章節試閱
一九八六年六月的某個早晨,明亮的陽光灑滿了房間,我仍舊沉沉睡著。從這一天開始到接下來十七年間所發生的事件,讓我不再能發揮這種熟睡的天賦。但那天早上,當我聽見房門打開的時候,還正享受著先醒過來一下、然後又陷入夢鄉的那種晚起溫存;我感覺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便張開眼睛。是我先生彎身站在旁邊,他下半邊的臉上沾滿了刮鬍泡沫,於是那種泡沫的味道便突然間包圍了我。他的臉頰在一片白色當中有一兩條深色的痕跡,顯出他刮鬍子刮到一半被打斷了。他看起來神色有異——當然一方面是因為臉上刮鬍中斷的痕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面露恐懼。跟我說話的時候,他刻意控制著語氣,緩慢而小心翼翼地把消息傳達給我,但他講的內容在我聽來卻一點道理也沒有。
是關於我父親的:警察和我父親,父親在警察那邊;我父親,在麻州西部的某處;警察正在電話上,他們想跟我談談。我幾乎是立刻清醒了過來,抓了衣服穿上,一邊問著沒有條理的問題——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什麼警察?麻州西部?我衝下樓到廚房的電話旁。樓上沒放電話,因為我那十七歲的兒子——班——的朋友,每星期至少有幾個晚上會在十一點以後打電話來,有時候甚至還十二點多打來,而我和我先生在那個時間早就已經上床睡覺了。廚房牆上電話的話筒懸在電話線上,晃來晃去的,幾乎要碰到地上。我把話筒拿起來說了聲喂,報上名字,然後就站在那兒,怔怔望著窗外美麗而陽光燦爛的早晨,一邊試圖從電話那端男子的聲音中去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現在記得最清楚的一點是,警察告訴我,那個他們拘留中的男子詹姆士‧尼可「聲稱」是我的父親。警察說,他們是在凌晨三、四點左右,在接近鄉間的某處,父親敲了某戶人家的門說他迷路了之後,將他帶回警局的。我當時非常憤怒,他當然是我父親!詹姆士‧尼可斯?他是我的父親啊!他就是這麼說的,不是嗎?那些人有什麼毛病,為什麼不相信他?當時我並不知道父親所同時「聲稱」的其他事情:他說他在到處遊蕩的時候遇見了一群奇怪的小人兒;還說他原本開著一輛小貨車,但車子卻不見蹤影(警察搜尋了那附近的區域都沒找到)。
在那種情況下,父親所說的其他事情也都因此令人難以置信——例如他是普林斯頓神學院退休教授的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是當時他們用「聲稱」這個字眼讓我心裡覺得很不舒服,因為這個字意謂著對父親的說法表示存疑和蔑視。後來在父親的病情日趨嚴重的同時,我也越來越常聽到別人用這個字描述父親的行為:他聲稱做了某件事;他聲稱看見某樣東西;他聲稱那是「他的」房間。只是在當時,我第一次聽見一個陌生人這樣說父親的時候,心情是既驚訝又備感傷害。我請他們讓我跟父親說話,但那名警官不答應,他要我直接過去那裡接父親,我到了之後他們自然會放人。警官想知道我要多久才會到那兒,但我完全沒概念,他們到底位於何處呢?他告訴我大概的方位後,我就回答他我預估所需要的時間。我掛上電話,換成先生開始問我一連串同樣無濟於事的問題。然而就在我快速刷牙、喝咖啡、洗臉準備出門的同時,我們一起編出了一個彼此都覺得合理的故事。前陣子,在我們這些子女們的催促之下,父親終於同意把他在紐澤西的房子給賣了;因為我們都覺得他在母親去世後的六年來,獨自住在那兒太過孤單。
妹妹和我幫父親把他的東西分好:一部份送到妹妹在丹佛的住家附近的一處公寓,因為父親打算要在那兒住上幾年;一部份則送人——我們要的就給我們四個兄弟姊妹,或送給慈善團體;還有一部份,我用一輛大租賃卡車,把它們運到父親位於新罕布夏的避暑小屋。不過原來紐澤西的老家裡,還是留了幾樣東西,讓父親可以使用到交屋為止,而他也在電話上跟我們說,他自己會租一輛小貨車,把剩下的東西一起搬到新罕布夏去。
我和先生當下的結論是:父親八成是在這個來回搬家的過程中,於西麻賽諸塞迷路了,他也因此顯得困惑不知所措,而導致被警察拘留——如果這還算不上是逮捕的話。從波士頓到麻州的另一端大概要兩個多鐘頭,時間長得足以讓我在腦中想像這個故事的各種版本,並描繪其他可能導致這種結果的劇情。但是在整段路程中,我始終無法理解的情況,是父親處於這齣戲的中心位置。劇中主角的心情和他在做出種種行為時的想法,對我來說是個謎團,他到底想要什麼呢?父親並不高大,外表整齊而乾淨,有著溫柔而近乎帶著歉意的嗓音;他常會清喉嚨,那是習慣動作,也是長年喉嚨乾啞所致;很不會說服人,也鮮少直接了當說出他的想法——他是如此的謙遜、甚至是抹滅自己到了一種好笑的地步,總是希望不會給別人帶來麻煩。所以,我真的很難想像父親會做出如警察所描述的行為:在鄉間遊蕩試著吵醒別人、半夜按人家的門鈴。打擾別人——那真的不像是我父親會做的事。
當我透過一扇警察指著的玻璃門看到父親時,我嚇了一大跳。父親獨自坐在一間有數張椅子的等候室裡,看起來像是睡著了;但是當我進入那房間時,他隨即睜開雙眼看著我,像是如釋重負,卻又沒有看到熟人時的那種光采。父親看起來糟透了!他沒刮鬍子,穿著又破又皺又褪色的舊衣服,還戴了一頂他自己很喜歡卻特別難看的帽子,那是他釣魚時常戴的一頂帆布帽,既破舊變形又很髒,活像個遊民似的——雖然事後我才想到,即使父親平時穿著那些衣服、甚至戴著那頂帽子,他看起來也絕不會像個遊民,而是像是個準備好要穿上防水靴去釣魚的戶外活動者;或是一個要進行野外採集的黴菌學家;或是準備登亞當山或傑佛遜山的登山者。我想,嚇到我的並不是父親的穿著,而是他眼神裡的空洞——那種無法辨識我抑或周遭世界的空洞——讓父親看起來無家可歸並且深層而永久地迷失,這種迷失重新定義了他的穿著,像是在說:「我不屬於任何地方、也不屬於任何人。」父親對事情的反應也毫無深度可言。他的確為了所造成的麻煩跟我道歉,但語氣卻是清描淡寫的,好像我只要開車經過幾個巷口就能接到他似的,「不好意思讓妳來接我。」就這樣短短一句話。我對自己說,他一定是累了,真的累壞了。警察把父親的皮夾和其他幾樣隨身物品交給我,他們說還是沒找到父親開的那輛貨車,並當著父親的面,宛若他是無關的第三者一樣,表示懷疑是否真有這輛車的存在。我因他們的無禮舉動深感受辱,就在父親身邊回了他們一句:「他住在紐澤西,總得有個交通工具才會來到這裡吧!」那名警官聳了聳肩,他其實是個好人,在我見到父親之前,他就跟我說,半夜被吵醒的人都被父親嚇了一大跳,因為他看起來很激動;警官還告訴我,父親會一直「看到東西」(也就是「幻象」)。
然後我跟警察們約好,他們找到貨車之後會打電話給我,我就載著父親回家了。父親在車裡很沉默,看起來比原本更瘦小又疲憊。我問他上一次吃東西是什麼時候,他說他不記得了。我開始問他更多問題,吃早餐的時候問,隨後在車上也繼續問,試圖藉以拼湊出父親的行程和事情發生的時點,但那真的很難。父親既不知道他究竟在什麼時間從紐澤西出發前往新罕布夏,也不記得他是走哪條路,更不認為曾在新罕布夏睡過覺或吃過東西。他記得是自己把行李卸下(他不想麻煩別人),然後就開始往南開回頭。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幾點?白天還是晚上?他都不知道。但在那天晚上,不知怎麼的——確定是晚上嗎?他就是搞不清楚——他轉錯了一個彎。那時候我才發現,父親大概至少有二十個小時甚或更久的時間沒睡覺,也可能都沒進食。我幾個星期前才到過新罕布夏的屋子,把紐澤西大部分的家具搬過去。
我回想當時屋裡有如洞穴一般冷清的狀況:沒插電的空冰箱、空氣中瀰漫著前屋主留下的貓味、老鼠的糞便到處都是。一想到父親獨自在那兒,又累又餓,我就覺得好難過。然後父親開始對我說,路旁的停止標誌在晚上的時候會變成人,也就是活生生的人,假裝成是停止標誌。他一邊說一邊描述那個景象。突然間,他的臉上比我剛剛看見他時多了一份生動,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欣喜——那是在他提到那些小人在夜晚對他說話的情景時。
「你是說,那些停止標誌的頂端看起來像人的頭對嗎?」我試著改編他的故事,想讓它聽起來比較像是我自己可以想像的情節。
而我也能夠了解這樣的情形:當你開車行駛在暗暗的公路上,迎面而來的停止標誌,的確有可能會看起來像八邊型的大頭杵在瘦巴巴的身體上。父親似乎覺得我說的話很好笑,甚至對我的缺乏想像力感到有些輕蔑,「不是,他們是真的人。他們有身體——還有手臂和腿。」我繼續開著車,不知該如何回應。父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還跟你說話是嗎?」我終於這麼問。他微笑說,「是的。」然後,我就不再問他任何問題了,因為我沒辦法承受即將聽到的答案。
顯然警察並沒有錯誤解讀任何一件事:父親的確是他們口中那個腦袋不清、方向不明的人。在沉默中,我繼續開車向前走,過了一會兒,父親睡著了。我想,這就是他需要的:睡眠和食物。一切都是疲憊惹的禍,也可能是他的飢餓和疲倦造成體內某種化學物質的不平衡,進而讓他產生了幻覺。我一邊開車,一邊不時轉過頭去看他。父親整個人陷在椅子裡、靠著車窗張著口睡著了,帽子懸在他的後腦勺。我突然覺得離他非常遙遠,甚至對他有些生氣——因為他不像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今晚的遭遇和行為有多麼異常。我想要他變回原來的自己,我要我的父親回來。這個古怪的老頭令我發火。到家以後,我幫父親弄了另一份點心,然後幫他在班的房間裡鋪好床,他很高興可以小憩片刻。當他在睡覺的時候——他睡了好幾個小時——我試著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眼前的問題是,不到一星期後,我和我先生就要出發到法國去待上兩個月。父親顯然需要人照料,但我沒辦法去紐澤西陪他;我也不能讓他自己在這種狀態下回紐澤西、獨自做最後的清理和打掃工作;還有他的狗,現在一定在父親朋友家等著,要不就是在狗籠裡,和貨車一起迷失在荒郊野外。我是個會把各種該做的事表列出來的人——沒有工作表我沒辦法生活——在我的表單上,已經有許多事情得在出國前完成,但是現在,單子上的當務之急卻該是父親;而緊接在父親之下、凌駕在我其他應該完成的事項之上,還應該有一份給父親安排的工作單。我覺得這一切實在令人難以招架,我沒法獨自處理這些事,兄弟姊妹當中得有個人來幫我,或者父親得去投靠他們。要不然我就必須延後去法國的時間;我先生可以自己先去,等事情處理完之後,我再去跟他會合。待我先生回到家後,我告訴他父親的情況。我們討論了各種可能性,而他願意接受任何一種安排,但當然比較希望我最終能和他一同出發前往法國。我們說了好幾次將會視情況而定,看父親醒來之後的狀況如何,我們會見機行事。
父親睡覺的地方,也就是班的房間,是地下室後半部一大區整修過的空間,天花板不高。要從那裡爬樓梯到一樓,必須經過地下室前半部沒有整修過的部份,那塊區域大致上被一個老舊的鐵製火爐及管線所佔據——過去用來燒煤,現在則改用瓦斯;洗衣機、乾衣機也擺在那兒,還有不要的家具跟十二年來住在這屋子裡所累積的廢物——因為我們沒有閣樓可以擺那些東西。下午稍晚,我聽見地下室的前半部發出一些奇怪的噪音。我對著地下室喊父親,過了一會兒,他出現在階梯下端昏黃的燈光中。父親神采奕奕的臉上帶著微笑,他看起來比較像自己了,我心裡這麼想,因為他看起來沒有心不在焉,也似乎很高興見到我。
「上來吧,」我說,「喝點咖啡或是其他的飲料什麼的吧!」我一邊煮著咖啡,一邊和父親輕鬆地對話。我問他睡得好不好、談他可能是怎麼迷路的、還有他認為貨車可能丟在哪兒。父親和我先生有一陣子沒見到對方了,於是趁此機會閒聊彼此的近況。他似乎一切正常、一切都好,我因而開始放鬆下來。我們端著自己的咖啡走到客廳時,父親說了:「你知道嗎?我跟地下室裡的小朋友們說話時,他們都不發一語,怎麼就是不回答。」他看來很疑惑、甚至有些受傷。我沉默了一會兒,和先生四目相交。聽到父親的話,我覺得就像是冷不防被打了一下。
「你說的是什麼小朋友?」我問他,盡量用純屬好奇的語氣問著。
「就是剛才啊!在樓下。班和他的朋友們。」他看來很困惑,「也可能班不在那裡吧。但我跟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都不理我,自顧自地走開了。」過了一會兒,我說:「你說的是班嗎?」
「嗯……我不確定有沒有班。或許只是一些其他的小孩子。」
「爸,班現在已經十七歲了,他的朋友也都大了。這裡已經沒有小孩子了。」父親沒看我,我們只是靜靜地在那兒坐了一會兒。我喝了一口杯裡的咖啡,我先生開始溫和地跟父親說話,說他真的不覺得——「在那裡!」父親說,「那裡有一個!」他的聲音裡帶著勝利的歡喜。
「哪兒?」我說。
「那裡啊!」他指著一個方向說。我起身穿過房間,往他指的方向四處張望。我們的客廳相當開闊——我買下這間房子的時候,把一樓內部的牆都給拆了,所以那裡並沒有任何角落之類的可供躲藏,只有空氣和置身其中的我。
「那裡沒有任何人啊!爸。」我說。他看來是真的很困惑,「他一定是下樓去了。」父親說。於是,過了一會兒,我提議我們也下樓去——到樓下去找那些小朋友們。我們下了樓,站在那個堆滿各種物品的空間裡。一個裸露的燈泡懸掛在天花板上,淡淡的光線灑在那些棄置的東西上。
「他們在哪兒啊?爸?」我問他。他穿過火爐前面,開始在成堆的盒子跟廢棄物中間找人,把東西移過來搬過去的,一臉狐疑。
「這裡現在沒有人啊!」我說。
「是沒有,」父親同意我的說法,「沒有人。」突然間他似乎又累了,精疲力盡,但他並未看著我。過了一會兒,我們沉默地上樓去,到客廳坐下。
最後,我開口了:「爸,我不認為樓下有小孩子,甚至之前應該也沒有,這個屋子早就已經沒有小孩子跑進跑出了。沒道理這裡有小孩子在,而我卻渾然不知;他們也不可能有辦法自己跑進來,我們卻沒聽到或看到有任何孩子離開。」他點點頭,「沒錯。」他說。我試著用更輕的語調說,「老天知道,我是希望這裡還會有小孩子到處跑來跑去,可惜早就沒有了。這裡沒有小孩子啊!爸。」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說:「那我猜我是看到幻覺了。」
「我想也是。」我說,「你看,你幾天沒吃沒睡,就生理上的化學作用來說,那是會影響你的。我想你應該是因為筋疲力盡,所以才會有幻覺。」我們在沉默中坐了一會兒。終於,父親哀怨地笑著說:「該死,我從來沒想過我會變得神智不清。」其實這句話當中還隱含著一句沒有明白點出來的弦外之音——我已經試著揣測各種老化可能會帶來的後果,但萬萬沒想到——但在我聽來,這隱含的部分和父親實際上明白說出的部份一樣清楚。我猛然了解到,父親早已想過老化及死亡將可能如何影響他,然而現在,當它們以這種意料之外的方式接近時,父親便手足無措了。當時我驚訝地發現,原來父親已事先考慮過這種種問題。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家族當中和他同一個世代或之前世代的長者也都已經不在了,輪到我該去思考死亡的事,而我也的確在思考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死亡會以什麼方式降臨,但和父親不同的是——這大部分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我時常會想到喪失自我心智的可能性。而當我思考這個可能性的同時,也常會憶起這段和父親的對話;父親也是從那時開始得知關於他的命運,以及後來生命會如何結束的訊息;並從那時起接受了他的命運,且在同一時間裡以他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此命運的興趣;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我的眼前。那一刻對我而言,是非常能代表父親的,同時呈顯出他的勇氣。那是父親高貴的情操,真的,我越來越這麼覺得。然而在當時,我並沒有這麼想。我根本不想去思考這個問題,不想去看父親所見到的世界,也不想去接受那一幕所帶來的深層含意。我開始找藉口解釋給父親聽——一方面也是為了他自己——那些我這一整天用來解釋給我自己聽的藉口。父親似乎也接受了這些藉口,而讓我鬆了一口氣,他彷彿就此得到安慰。也或許這只是父親表示禮貌的方式。畢竟他已察覺到我的苦惱,而他或許只是在回應我的情緒;也許他知道我是多麼需要他來同意我的說法,所以他就順著我的話。他同意我的看法是他仁慈的表現,好讓我不會持續被這件事所困擾,或為這件事感到心煩。我不知道。無論如何,我們決定繼續原先的計畫。我兒子那時也回到家了,帶著一身青少年的精力,因為外祖父的突然來訪而驚喜不已。我們一起吃晚餐、聊天,彷彿父親這次的來訪跟往常沒有兩樣。我們談到一些等著解決的問題;父親提到他必須把狗找回來,我也說到那輛還下落不明的貨車;我先生還說會找一些盥洗用具給父親,因為父親已經有好一陣子沒刮鬍子也沒刷牙了。基本上還是談天的成份居多。那天稍晚,父親上床睡覺之後,我先生和我討論我們該怎麼做。
最後,我決定打電話給妹妹尋求她的協助。
當然在那之前已經有跡可循。六年前母親去世之後,我們就慢慢察覺到父親逐漸衰弱的意志,像是一種方向感的缺乏。但其實也有其他的跡象。一次我到紐澤西探望父親,可是他卻絲毫不記得我們有約——雖然他跟往常一樣還是很高興見到我。另一次是他在夏日度假的小鎮教堂裡做了一段五分鐘的短講,但實際上他原本是預定要講十五到二十分鐘的——他的演說雖然聽起來很流暢,但是整體而言卻沒有什麼意義,而且一下子就結束了;當演說結束的時候,會眾一陣錯愕,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打破尷尬,靠到我身邊說:「這就是我們所喜歡的:短而美。」過了一會兒,父親的一位老朋友問了我一個之後我將一再聽到的問題:「妳想妳父親到底是怎麼了?」課堂上也發生了一些問題,那是父親生平第一次遇到的情形,他自己會跟我傾吐工作上遇到的困難。還有一次是父親去拜訪他最小的妹妹,距離家裡大約四十五分鐘的車程,他跟我姑姑說,在那段路上,他的記憶一度陷入空白,記不得自己在哪兒,也不知道該往何處走。姑姑打電話給我,問我知不知道父親怎麼了。也是因為這些事件,我們才會督促父親把紐澤西的房子給賣了,然後搬到丹佛我妹妹家附近,因為他退休後自己在那兒會太孤單。不過其實一般說來,父親並未過得那麼可憐。他在母親死後獨自生活,而且剛開始的幾年還過得相當不錯。例如,我每次去拜訪他,父親總是一個很好客的主人,幫我們做簡單而美味的飯菜,還幫我們把乾淨的毛巾擺好、把床也鋪好;他和我們幾個孩子們也時時藉由信件及電話保持聯絡;更重要的是,他在母親去世後一年內,自己安排好在退休後到加州的一處神職人員退休社區去居住(那是他在母親生前絕不會考慮的——光是提到這個地方就會讓母親咬牙切齒:她可不想在一群神職人員當中度過餘生!)父親搬去丹佛的原因之一是,那兒是他正式搬到加州前的一個緩衝地:要搬進那個神職人員退休社區通常得等上兩三年,而父親也同意在他搬到加州之前,需要多和人群接觸,也需要多一點日常生活上的協助。剛好妹妹家附近有一棟新完工的「老人公寓」,她和她的先生打算之後也安排她公婆搬去那裡住,所以我們就建議父親在這段過渡期先搬去那裡,而他也同意了。家族裡就是妹妹和我覺得父親應該搬家,大哥和弟弟都不覺得父親有什麼問題;而且每當我表達出對父親的關心時,兄弟姊妹裡通常也只有妹妹會回應我;母親去世後,負責整理她的遺物分給其他人的也是我和妹妹;父親搬家前的那個春天,她和我還一起幫父親把東西分好。況且妹妹也在等父親去新罕布夏過完夏天之後,於秋天時往西搬過去她那裡,因此現在向妹妹求助是再合理不過了——基本上就是請她早幾個月迎接父親過去,照顧他直到一切恢復正常,或是直到有人可以去新罕布夏陪父親——大哥和弟弟都計畫在夏天去探望父親——總之,就是需要有個人在旁照顧父親。當我打電話給妹妹並提出我的建議時,她立刻就答應了。很快的,我們決定好工作分配的方式:父親會去找妹妹,而妹妹會視父親的康復情況決定是要讓他自己回到東岸,或是親自帶他回來;而接下來的幾天,我會到紐澤西去把那裡的房子做最後的整理、處理父親仍停在車庫裡的自用車、把狗帶回來、再處理那輛失蹤的租用貨車。這樣就大功告成了。隔天,我故做若無其事地把我們的計畫告訴父親:「爸爸,你知道嗎?我們何不……」但是父親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他對我們的提議表現得很漠然——當然他還是像往常一樣有禮貌——不過態度是堅決的:不,不!我當然不能這麼麻煩妳,沒有這個必要。他自己可以上路;那輛車終會自己出現;要不他也可以搭巴士或是飛機回去,然後自己處理好所有的事。總之沒有必要麻煩我。我試了好多次,但父親仍然不為所動;那天我也請妹妹打電話給父親,邀請他過去妹妹那邊住,當作是一整個忙碌春季後的休息。我在這一端聽著父親在電話上對妹妹的回應,就和他之前跟我說的一模一樣。喔,不,那樣太麻煩了,沒有那個必要,他已經在蘇的家好好休息過了,而且在他還沒完全恢復體力之前,也不會貿然上路。他不能、也不會這麼麻煩妹妹。我猜我那個時候是希望,父親最終會覺得累了而放棄跟我們爭辯。無論如何,我在那一天當中持續嘗試說服他,我想如果有人聽到我們的對話,那個人應該會覺得很有趣——我們兩個都極有禮貌、在言語上鞠躬作揖,但是態度上卻都是十分頑固而堅持。
「你何不考慮……」
「不不,那樣太麻煩了。」
「爸,我真的覺得你應該……」
「妳真的太好了,但是我不能……」諸如此類的對話。我們的性情是如此相似,以致於事情毫無進展。終於,我領悟到,我必須誠實說出我的想法,態度也要更強硬,否則父親是不會聽我的。我必須堅持。我從來沒有堅持過要父親做些什麼,也不知道是否曾有任何人堅持要他做什麼事。而這一刻,在稍晚的午後來臨。我的先生之前已經跟我說過,等我決定採取行動時,他會留在家裡給我精神上的支持,而他那天剛好也在家。那時我們都在廚房裡,父親開始說起我們對他是多麼地好,他又給我們添了多少麻煩,還有他覺得隔天就應該上路。我對他說我不認為他應該獨自前往紐澤西、我不希望他自己一個人去,而認為他應該去丹佛。我先生也同意我的看法。父親指出在紐澤西他還有好多事得處理,所以他必須回去那裡,他想要把事情全都解決後,再北上到新罕布夏避暑。我跟父親說我會處理紐澤西的事。他說他不能這樣麻煩我。後門是開著的,在我們的沉默之中,可以聽到後面的公寓裡傳來陣陣音樂聲、隔壁鄰居的談話聲、還有穿過樹梢的風聲。接著他又提起了狗的事。我說我會去接狗,我會幫狗找到一個安身之處,直到父親回到東岸為止。他說他當然不能讓我這麼做,他已經麻煩我太多了。雖然他還是維持一貫的禮貌,但聲音裡卻隱隱透露出一絲非常抑制的、隱約的憤怒。我吸了一口氣,「爸,我不能讓你走。」我說。我的心跳聲清楚地在耳際迴盪。
「恐怕妳別無選擇,妳必須讓我走。」他似笑非笑地說。
「不行,爸,我不能這麼做。你真的是病了,是一種身心衰竭之類的毛病……」接著是一陣可怕的沉默。我先生率先打破了沉默,一方面表達他對我的支持,同時也再次提出我們的論點。父親一向比較願意聽男人的話,他點著頭,像是在認真考慮我先生說的,但父親終究沒有答應,終究沒有說好。父親和我面對面坐在餐桌的兩側。我先生說話的時候,我望向一旁午後陽光映照下的模糊葉影,之後又把注意力轉回父親身上。我把身子向前傾,「爸,聽我說。你想,要是我們現在的角色互換,」我說,「如果是我出現在你家,又累又不時看到幻覺,」現在輪到父親把眼光移開了,「你也會覺得那是你的責任和義務來確保我會平安無事,不是嗎?」我停頓了一會兒,「你絕對絕對不會現在讓我自己一個人單獨上路的,不是嗎?」又是一陣漫長的沉默。在這段時間裡,我想父親似乎終於看清了自己的處境,而我也才第一次有了相同的領悟。
他懂得而我們也懂得:我們正一起朝著他的疾病——不管那是什麼病——邁出第一步。我們從現在開始要為他負責。沉默在數秒鐘後結束。父親回頭望著我,又把目光往下移,「不會,」他靜靜地說,「我不會。妳是對的,我不會讓妳走。」
隔天我先生幫父親買了個旅行包,借給他一件乾淨的襯衫,然後我們就載著他——一個身材瘦小、衣著奇特的老人、依然戴著那頂他很喜愛卻難看的帽子——到機場搭機前往丹佛。我自己則飛到紐華克機場,從那兒搭巴士到普林斯頓,然後再轉搭計程車——從勉強可稱為「鬧區」的地方,乘車到父親位於森林裡的屋子。我在那兒花了好幾個小時,把垃圾和零碎的物品用袋子裝起來,把最後的一些東西打包好,用吸塵器打掃屋內,又清理廚房和浴室。我看著父親這一陣子的生活空間,心裡既難受又憐惜——屋子裡沒有家具、只有一張床墊放在地板上、四處都是狗毛。下午過了一半,我也差不多把能做的都做完了。我開父親的車去狗旅館,把他的狗娜歐米帶出來;再開車到康乃狄克州,把狗安置在姑姑那兒——她之前就說過她願意照顧那隻狗。等我回到家的時候,早就已經天黑了,我把車停在一位鄰居的車道上,他們同意讓我們把車暫停在那兒,直到我妹妹和父親來把車開走為止。隔天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打電話。那輛小貨車終於出現了!它被拖吊到麻州西部一處停車場。我跟在紐澤西的租車公司通了電話,希望能請他們北上去領車,然後我再補貼他們一點費用,但談判不成。我最後只好安排一位在該停車場工作的員工幫我把車開回紐澤西。由於那名員工知道我只能靠他,便漫天開價,還跟我在電話上閒扯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說他喜歡我的聲音、說他想見我、還問我的長相如何、穿什麼樣的衣服等等。我對他非常非常有禮貌,因為我覺得必須這麼做,不過,這讓人覺得荒謬而莫名其妙的難堪,似乎是必須跨越的最後一道關卡。儘管發生了這一切,我們最後還是趕上預定的時間,出發前往法國;父親也在幾個星期後,由妹妹陪同回到東岸,並在新罕布夏度過夏天。
那個秋天,我拿到新罕布夏麥克道爾藝術村的寫作研習獎助金。我們的工作室裡沒有電話,我坐在公共電話間裡唯一的一盞亮燈下,隔著一扇門,耳邊猶聽見主研討室裡其他研習者的模糊談話及笑聲。電話中,我從妹妹那兒確知了這個早已了然於心的答案——父親已經被診斷出患有「疑似阿茲海默症」。
一九八六年六月的某個早晨,明亮的陽光灑滿了房間,我仍舊沉沉睡著。從這一天開始到接下來十七年間所發生的事件,讓我不再能發揮這種熟睡的天賦。但那天早上,當我聽見房門打開的時候,還正享受著先醒過來一下、然後又陷入夢鄉的那種晚起溫存;我感覺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便張開眼睛。是我先生彎身站在旁邊,他下半邊的臉上沾滿了刮鬍泡沫,於是那種泡沫的味道便突然間包圍了我。他的臉頰在一片白色當中有一兩條深色的痕跡,顯出他刮鬍子刮到一半被打斷了。他看起來神色有異——當然一方面是因為臉上刮鬍中斷的痕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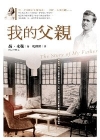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