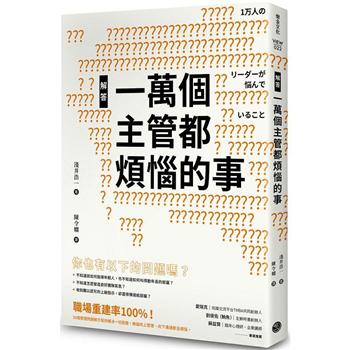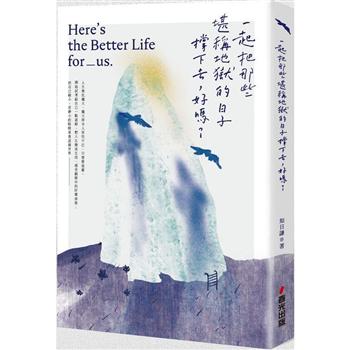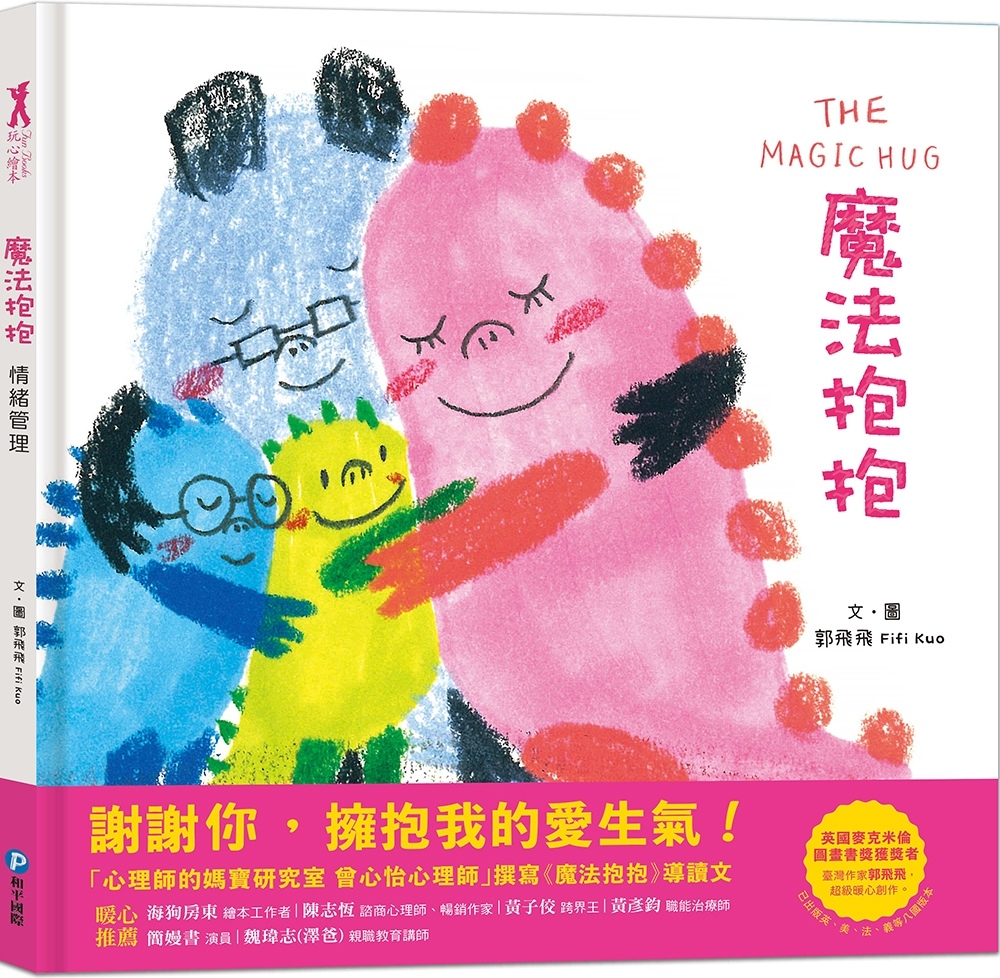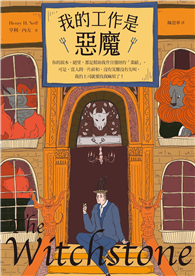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6 項符合
褚幼義的圖書 |
 |
$ 361 | 褚民誼紀實全傳 第一卷--立志求真
作者:褚幼義 出版社:獵海人 出版日期:2025-07-23 語言:繁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494 | 褚民誼紀實全傳 第五卷--求仁得仁
作者:褚幼義 出版社:獵海人 出版日期:2025-07-23 語言:繁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665 | 褚民誼紀實全傳 第三卷--強國健民
作者:褚幼義 出版社:獵海人 出版日期:2025-07-23 語言:繁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665 | 褚民誼紀實全傳 第二卷--踐行主義
作者:褚幼義 出版社:獵海人 出版日期:2025-07-23 語言:繁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665 | 褚民誼紀實全傳 第四卷--捨身濟世
作者:褚幼義 出版社:獵海人 出版日期:2025-07-23 語言:繁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449 ~ 459 | 重行傳: 褚民誼生平紀實
作者:褚幼義/ 主編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2-05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