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學西班牙語必讀文本,曾譯成英法德義捷克等16國文字,並多次拍成電視片、電影(包括琥碧戈柏主演的《大亨也瘋狂》)。
作者藉股市沸騰,書寫人性深層,諷刺崇洋媚外,凸顯當代小說詐騙的議題,股市成功的案例:用英美人姓名撐場,合組公司模式。主角胡亮年輕時充滿幻夢,寫過詩;現在做房地產,因生意清淡,常找人調頭寸,卻屢遭「問合夥人」為由拒絕。後來為婉拒投資邀約,也拿虛擬「合夥人」作擋箭牌。不意從此命運大轉:廁身股市,進場就贏。這個「影子」是他縱橫商場、成功發跡的貴人,但後來卻也成了揮之不去、一敗塗地的夢魘。本書對話鮮活,情節起伏,人物刻畫入木三分,處處流露出作者的詼諧反諷,但褒貶之間亦不乏同情。
這本小說出版將近八十了,寫當時智利中產階級的生活,映現出升斗小民謀生的心酸,以及人心欲求的難以滿足;其中無論情境敘述或個人對話,都穿插了不少智利歷史文化風土民情及當時政治實況,足證作者書寫的並非完全出諸想像,大部分仍活生生的現實。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政治文化;但這些性格和文化,不論其間差異多大,也必然有些共通的地方。小說中精采細膩的描述,讓人讀了不僅不會有時空隔離的感覺,彷彿事件的發生就在周遭。
本書特色
本書為國家科學委員會經典譯注計畫之一。
作者簡介
赫納羅.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 1889-1946)
生於智利聖地牙哥。大學研讀法律,但一生未執業。曾任報社主筆,歷時三十餘年。批評時政,直言不諱,辛辣中不失幽默。除時論集外,並出版多本小說,以《合夥人》最受推崇。後短期從政,當選過眾議員。
普列托多才多藝,寫評論、小說和戲劇外,猶從事油畫(作品為智利國家美術館典藏)、漫畫、雕刻創作;一生閱歷豐富,當過股票經紀人,這也是他寫《合夥人》的根源。1946年病逝後,遺作相繼出版:《斗煙繚繞》(Humo de pipa, 1955)、小說《老屋》(La casa vieja, 1957)、《幽默選集》(Antologia humoristica, 1973)、《愚島上》(En Tontilandia, 2007)。
譯者簡介
曾茂川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系副教授。擁有淡江、馬德里大學文學碩士,南非金山大學、菲律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早年服務於行政院新聞局,曾派駐智利、菲律賓,巴拿馬(任大使館新聞參事);後出任台北市政府新聞處處長、行政院文建會第三處處長。著有《傳媒與智利對華政策》、《華西分類詞典》、《瑪麗雅.路易莎.龐芭兒:女性本質的追尋》(Mar?a Luisa Bombal: La b?squeda de la esencia femenina)、《實用西班牙語彙》(2003)、《合夥人》中文注釋本(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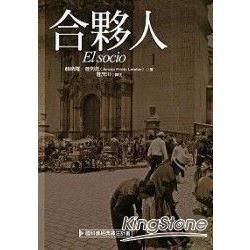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