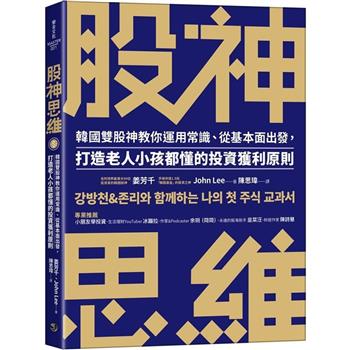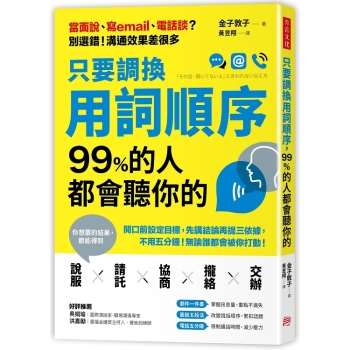背向暴風的核心——訪陳建成
張敦智
外頭天氣寒涼,隨時都要飄起陰雨。下午兩點的咖啡廳人不多,我與攝影師提早到場後不久,陳建成頂著他冬天常戴的灰色毛帽與招牌黑框眼鏡出現,眼神既內斂又目標明確地尋找著什麼,使初次見面的我一眼就認出來。
眾人入座後,作為暖場,我們首先談起跨入劇本創作這門專業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其實在進入研究所前完全是一張白紙。若未考上北藝大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創作組,可能就會直接去當兵,再另作打算,說這些話時的語氣十分淡然。但是,命運的拼圖終究把他嵌入進這片風景,成功踏入許多人心目中藝術創作最高殿堂裡,從零開始學習。
一、形式本身,就是一種意義
在研究所時期的期末劇本〈清洗〉獲得2010年臺灣文學金典獎後,陳建成以其為基底大幅度地變動,更名為〈新天使〉作為畢業製作。兩者主要差異,在於前者更接近新文本形式,所有角色各自對讀者/觀眾呢喃;後者則找到更靠近寫實光譜的表達途徑。無獨有偶,陳建成的許多劇本也都經歷類似過程。 2014年收錄於《阮劇團2014劇本農場劇作選II》的〈解〉、以及2017年獲得第二十屆臺北文學獎舞台劇本優等獎的〈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皆曾有前後兩個不同版本。談到這點,陳建成露出苦惱的表情,說這是他最近在反省的事。「我好像很容易後悔」,他接著補充,這種不斷反省的習慣,在博士論文研究英國劇作家Edward Bond之後變得更加深刻。Edward Bond的創作生涯從1960年代橫跨至二十一世紀,過程也不斷思考為什麼要創作、以及自己的創作在社會上的定位。這樣的精神深深影響陳建成,造成他不斷內省,於是不同時期對創作的看法很容易不同,因此老是忍不住回頭修改舊作的習慣。
聊起舊作,我注意到他這次提供的參考劇本裡,並沒有網路上可見資料中寫於2012年的〈芒草原〉與〈山居〉(後者入圍2012年臺灣文學金典獎決選)。談起為什麼不提供這兩個劇本?是不是因為版權問題?或有其他考量?陳建成連忙搖頭說沒什麼,只是因為在自己心中,它們還沒完成罷了。順帶一提,他說,〈芒草原〉與〈山居〉其實也是同一部劇本,現場又幫自己增添了一筆「一作兩寫」的案例。照這個情況看來,身為「二世」的〈山居〉應該還會有第三代被孕育出來。儘管有這樣不斷修改舊作的習慣,且自稱是身為劇作家的「惡習」,不過另一方面,他也認為創作者應該抗拒第一時間的寫作衝動,拒絕去寫那個「首先從腦海浮現」的靈光,而是不斷琢磨,尋找最適合的載體,最後才穩建地下手。從〈清洗〉到〈新天使〉,儘管都處理2003年SARS和平醫院封院事件,但陳建成意識到,同一個題材可以用完全不同形式來說。最理想的形式可能是寫實,也可能是寫實外的任何手法。對他而言,寫實是個基底,和非寫實不是二元對立或光譜兩極的關係,後者更像從前者繼承、累積、外加上去的想法與結構。因此,尋找最適合的形式,成為劇作家必須不斷自我檢視的問題。
這樣的認知套用在他對新文本的看法上也是相通的。他認為,所有劇本形式的變化,最後都要回過頭檢視其必要性。「一定是發現了什麼寫實語言難以承載的東西,可能是精神性的、可能是身體性的,所以必須從結構下手,來製造更大的容量。」他舉莎拉.肯恩(Sarah Kane)最後一部劇本〈4.48精神崩潰〉為例,它的形式跟內容緊緊相依,因為所要呈現的精神狀態已經超乎寫實語境,所以不得不從形式下手,找到另一種可以承載該狀態的結構。而究竟時下所謂「新文本」只是曇花一現,還是將淵遠長流?他沒有絕對判斷。只知,身為劇作家的責任,就是必須讓形式與內容合而為一,「因為形式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另外,他也舉自己在〈解〉當中「網路留言板」的橋段設計,裡頭模擬不同角色在論壇留言板上各說各話,不同角色的對話時而謾罵、時而交集、多數時候又都如散沙般各自宣洩,這也不是一般認知中的寫實對話,但他認為卻反映出了另一種真實,即現代社會的某種精神狀態。
二、暴力的本質,是抗拒被再現
現代社會一直是陳建成致力寫作的對象。從最一開始發表的〈清洗〉與〈新天使〉;到寫於2013年、並於2014年獲得臺北文學獎首獎的〈日常之歌〉,受到日本311大地震後的福島核災影響,描寫倖存下來的人如何維繫餘生;2014年的〈解〉關注隨機殺人事件;2017年獲獎、2020年首演的〈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關注轉型正義與白色恐怖;2019年的〈解離〉揉合了當代性別、權力等不同議題,在乍看寫實、肌理魔幻的設定下展開敘事。儘管如此,陳建成並不否認,除了〈清洗〉和〈新天使〉算是置身事件現場外,自己的多數作品,確實都展現了一個特質,那就是:以一個劇本中不可見的重大事件為核心,去描寫它的前因或後果,而不直接觸碰那個最具戲劇張力的爆炸性核心事件。為什麼這樣選擇?陳建成表示,這對他而言並不是可以一概而論的,可能還是要回到各別劇本的狀況剖析。例如〈解〉的隨機殺人與〈在世界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的白色恐怖,其實它的本質都蘊含極致的「暴力」,但陳建成認為,暴力的本質,就是抗拒被再現的。一來,在本質上,所有已遂、巨大的暴力事件,只要試圖在舞台上呈現,都必見其偽。因此,面對暴力現實,劇場有必要尋找新的美學來反映它。其次,所有透過虛構被再現的事物,其實都蘊含生者對它的期待,劇目中出現鬼魂,意味著生者某種程度希望這樣的事物存在。但暴力卻非如此,它總是取消自身,這樣的困難可能正是因為:追根究底,生者並不希望那樣的事情再度重複,因此情感上,這件事已經被拒絕,技術上也就更加無法探索出門道。
這也關係到陳建成近來思索的創作哲學:是否應在作品裡放入一種「正向」的能量。這裡的正向,並不是指要正向思考、一味追求積極、光明、與圓滿,而是在令人絕望的現實裡,透過虛構,打開另一種可能性。換句話說,即透過劇本驗算:事情是不是非得如此不可?嘗試指出另一條具有相同背景脈絡,結果卻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這樣的寫作之道一定是對或好的嗎?他還沒有答案,只能說這是他不斷思索「虛構」應該在世界上扮演什麼角色的階段性提問。
以〈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為例,常見處理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題材,會以特定人物為原型發想,但陳建成沒有這麼做。讀畢資料後,他截取的是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氛圍,來查找歷史中的一種可能性,因此黃父這個角色屬完全虛構,沒有任何參考對象,此舉反映了想透過劇本,驗算史實脈絡下其他現實情境的理念。之所以不以任何對象為原型,也因為認為觀眾若是想接觸史實,最好的方法應是閱讀第一手資料,更詳細、也更衝擊。虛構的任務不應只是轉述,他在意的,是史實中難以描寫的人物立體性,希望透過劇本補足那一塊,讓裡頭的人躍然舞台,不只有片面印象,更是有血有肉地被認識。因為此重點,加上暴力拒絕被再現的本質,所以就算選擇此主題,也沒有要讓故事回到白色恐怖事件現場,而是始終讓情節保持在暴力的外緣,描寫創傷後世界的日常。
三、勾勒「人」的極限與兩難
談及〈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陳建成表示,黃父其實是整齣劇本構思過程首先浮現的形象。一切始於2014年的318事件。那時,〈日常之歌〉剛寫完不久,正在接著寫〈解〉,同時準備出國攻讀博士,但突發的318卻帶給他巨大的震撼,影響後續創作。是從318起,他認為歷史對當下具關鍵性影響,於是開始對臺灣近代史饒富興趣,著手查找資料,發現因受過刑訊而變得精神異常的人們,開始希望有個故事能圍繞這樣的人而展開。那是〈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比較明確的起點,也就是後來成形的黃父這名角色。
然而,黃父作為白色恐怖事件直接受害者,他的追求、身世、與政治態度,雖然可以從劇中關注陳水扁選舉、以及曾被審訊等細節略窺一二,但整體角色設定似乎還是偏向隨著暴力的核心一起背景化的狀態。為何選擇把作為全劇主要癥結的角色,其背景做如此模糊的處理?陳建成答道,這個問題其實可將黃父與〈解〉中的小智做一番對照來回答。書寫這兩個角色時,他都刻意維持角色之於自己的陌生感。因為角色內心已存在某種異於常人的東西,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所以在創作上,他希望把這份不了解留存於劇本,不做僭越的猜想與補充。這其實也是創作上的一個矛盾,即,同時必須追求角色的立體性,但卻又需在必要處適當留白,這也是他不斷試圖調整、掌握的平衡。
當然,這種留白並非一定要出現在所有角色。綜觀他的劇本,有幾個角色的設定反而非常深入,以至於讓人好奇作者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例如,同樣是〈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女主角心怡的設定是:由於年幼時曾誤以為父親想性侵自己,所以就算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第二代,仍採取對這件事不聞不問,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態度。反而是退休軍法官蘇父的第二代,也就是男主角彥博,更積極地想釐清真相,雖然最後仍被蘇母以佛法曉以大義一番,獨自宣洩完情緒,便放棄原本的追求。男女主角的設定,在劇作家佈置的因果推演下,讓全劇距離白色恐怖議題本身,又更遙遠了些,這些設定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其實這是一件很主觀的事,」陳建成說。會如此設定,是因為自己原先對這段歷史感受到疏離,因此決定讓劇中年輕一代採取相近立場,來反映自己這一代(至少自己)的狀態,讓現實中既存的歷史距離感,可以被留存於劇本當中。
而關於角色設定,〈日常之歌〉中也有一特別現象,發生時芬這名角色身上。時芬的父親死於核污染,她也因此背負核污染者家屬的標籤。劇中她遭遇最嚴重的事件,即她男友的母親因此堅持否決這本早已敲定的婚事。到了劇末,原本一度要認同自己不該繼續生存在世界上的時芬,轉念一想,開始認為她可以「不再屬於誰」,切斷跟所有外在世界的羈絆,不屬於母親,不屬於父親,且永遠不會有小孩,不能有小孩。只要如此,那麼她就有活下去的立足點,因為她可以不再是核爆事件受難者的家屬,她只是她自己,孑然一身,上無繼承,後無子嗣。如此,有因有果地,時芬完成了一場獨特的「自我療癒」方案。相較之下,其他劇本的角色或轉變微小、或沒有轉變,為什麼唯獨在〈日常之歌〉裡設計了如此獨一無二的時芬?陳建成思考半晌,表示這個問題難以回答。對他而言,那是時芬直面創傷後的反應,之所以被解讀出所謂的「自我療癒」方案,可能是因為自己下意識想寫人的韌性,因此有這樣的劇情。如果硬要說為什麼,應該就只是為了讓時芬在那樣艱難的環境裡,還能繼續活下去,而發明出的一種可能吧。
從角色設定談到創作方法,陳建成表示,沒有一定的標準流程。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處理過白色恐怖議題,但自己卻從未因任何創作而去訪問任何人。心中有道坎始終過不去,就是將他者的人生經驗工具化這件事。在學術上,有嚴謹的標準流程處理訪問來的材料,決定哪些該公開、哪些該匿名,都已有明確的倫理規範。但創作不是這麼回事。它更自由,只能倚賴每個人心中的那把尺來拿捏資料的使用方式。對他而言,如果資料本來就公開,則沒問題,但為了創作特地去挖掘他人隱私,美其名為訪問或田野調查,但他卻始終沒能找到說服自己的方式。他也強調,自己並不反對其他人這麼做。對許多創作者而言,田野調查、訪問是很重要的環節,他們會有自己心中適當的處理方式與轉化手段。這種「反田調工作方法」,只是身為創作者,自己仍在面對的倫理難題。如何透過劇本深入了解、並摹寫「人」,成為陳建成心中巨大的矛盾,同時有巨大的嚮往,又時刻敲響著將他人經驗工具化的警鐘。
四、尾聲:給下一輪劇本創作者的備忘錄
談完個人創作理念與細節,最後,如果要給未來的劇本創作者一個意見,那會是什麼?陳建成聽了向後往椅背一靠,說這真是道困難的題目。「有沒有別人的答案可以先參考一下?」他開玩笑,「因為感覺答案很珍貴啊。」儘管如此,他仍設法在短時間內歸納出兩點:第一,確保形式與內容的緊密關聯;第二,精讀契訶夫。為什麼是契訶夫?能不能因此,將陳建成目前為止的創作,定位為繼承了契訶夫壓抑、平靜的寫作路線?他搖搖頭,否認了這樣的推測。「其實契訶夫是我最近才開始感興趣的對象。」他坦白,大學與研究所時代雖知其重要,卻往往只是看過,沒有特別體會。但近日細讀,發現契訶夫其實非常擅長處理隱性的暴力,這跟自己的創作不謀而合,都試圖在日常氛圍裡勾勒出恐怖事件的醞釀或蔓延。例如,〈海鷗〉整部劇本,其實描繪了男主角特列普勒夫邁向自殺的全部過程,讀來卻雲淡風輕,不著痕跡;〈三姐妹〉則是所有人被娜塔莎傷害的故事,但讀來毫無批判性,甚至可以讓人理解她的思維。契訶夫的劇本能包容現實中可能令人不適的角色,不流於功能性,拿捏各種平衡恰到好處。在這樣新的平衡裡,隱性的暴力並未消失,而是殘忍、安靜地,延續於日常生活的蛛絲馬跡。透過這樣的重新細讀,陳建成找到了一名新的導師與知己。
至此,礙於時間因素,談話必須告一段落,但雀躍分享的氛圍仍瀰漫在空氣間。臨別之際,陳建成慷慨表示,此次對話也幫助他釐清了一些自己正摸索的問題。我們在外頭不知何時飄起的寒冷細雨間道別。當下那種感覺,比起結束,整個下午更像幾人共同推開了一道大門。這名劇作家背向暴風核心的旅程,似乎正準備好,推進至下個篇章。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趙偉丞的圖書 |
 |
$ 264 ~ 285 | 本行1
作者:張敦智/陳建成/林運鴻/趙偉丞/詹傑/魏明毅/尹懷慈/林孟寰/陳栢青/吳曜愷 出版社: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出版日期:2021-08-31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本行1
《本行》為收錄國內華語劇本創作之專業叢書。
首期收錄三位資深與三位年輕創作者共六部劇本、三篇由年輕訪談資深創作者的專訪及三篇特邀文本評論。
章節試閱
背向暴風的核心——訪陳建成
張敦智
外頭天氣寒涼,隨時都要飄起陰雨。下午兩點的咖啡廳人不多,我與攝影師提早到場後不久,陳建成頂著他冬天常戴的灰色毛帽與招牌黑框眼鏡出現,眼神既內斂又目標明確地尋找著什麼,使初次見面的我一眼就認出來。
眾人入座後,作為暖場,我們首先談起跨入劇本創作這門專業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其實在進入研究所前完全是一張白紙。若未考上北藝大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創作組,可能就會直接去當兵,再另作打算,說這些話時的語氣十分淡然。但是,命運的拼圖終究把他嵌入進這片風景,成功踏入許...
張敦智
外頭天氣寒涼,隨時都要飄起陰雨。下午兩點的咖啡廳人不多,我與攝影師提早到場後不久,陳建成頂著他冬天常戴的灰色毛帽與招牌黑框眼鏡出現,眼神既內斂又目標明確地尋找著什麼,使初次見面的我一眼就認出來。
眾人入座後,作為暖場,我們首先談起跨入劇本創作這門專業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其實在進入研究所前完全是一張白紙。若未考上北藝大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創作組,可能就會直接去當兵,再另作打算,說這些話時的語氣十分淡然。但是,命運的拼圖終究把他嵌入進這片風景,成功踏入許...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導讀)
編輯室報告
當代劇場重視現場性,此外一切文本,可能無非事關記憶保存。記憶保存並非不重要,只因若記憶消亡,也反向否證了那稍縱即逝之現場的實存。《本行》劇創期刊因應而生,期望促成否證的否證,一年一期,為臺灣當代舞臺劇作保留一席發表平臺,裨益研究與展演。
我們規劃兩個欄目。其一,為「臺灣當代劇作選刊」。在創刊號中,我們選刊陳建成、詹傑與林孟寰等三位極具代表性之青年劇作家的作品。每部作品之前,並附本系所同學,對劇作家的專訪。我們期許藉由訪談,激發現場對話,並留存劇作家個人,就創作思維與技藝的...
編輯室報告
當代劇場重視現場性,此外一切文本,可能無非事關記憶保存。記憶保存並非不重要,只因若記憶消亡,也反向否證了那稍縱即逝之現場的實存。《本行》劇創期刊因應而生,期望促成否證的否證,一年一期,為臺灣當代舞臺劇作保留一席發表平臺,裨益研究與展演。
我們規劃兩個欄目。其一,為「臺灣當代劇作選刊」。在創刊號中,我們選刊陳建成、詹傑與林孟寰等三位極具代表性之青年劇作家的作品。每部作品之前,並附本系所同學,對劇作家的專訪。我們期許藉由訪談,激發現場對話,並留存劇作家個人,就創作思維與技藝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編輯室報告
專題:陳建成
背向風暴的核心──訪陳建成 / 張敦智
劇本〈日常之歌〉/ 陳建成
國民默許的輻射怪物、國民宣判的「例外狀態」:讀陳建成〈日常之歌〉 / 林運鴻
專題:詹傑
劇場,人和人的連結──訪詹傑 / 趙偉丞
劇本〈像我這樣的查某人〉 / 詹傑
溫柔尚且不足以靠近:評〈像我這樣的查某人〉/ 魏明毅
專題:林孟寰
夢想及麵包──劇作家林孟寰訪談 / 尹懷慈
劇本〈同棲時間〉 / 林孟寰
同志吾祖國,同志無祖國──讀林孟寰〈同棲時間〉 / 陳栢青
妖山新秀
尹懷慈
作者簡介、創作自述
劇本〈泰迪熊...
專題:陳建成
背向風暴的核心──訪陳建成 / 張敦智
劇本〈日常之歌〉/ 陳建成
國民默許的輻射怪物、國民宣判的「例外狀態」:讀陳建成〈日常之歌〉 / 林運鴻
專題:詹傑
劇場,人和人的連結──訪詹傑 / 趙偉丞
劇本〈像我這樣的查某人〉 / 詹傑
溫柔尚且不足以靠近:評〈像我這樣的查某人〉/ 魏明毅
專題:林孟寰
夢想及麵包──劇作家林孟寰訪談 / 尹懷慈
劇本〈同棲時間〉 / 林孟寰
同志吾祖國,同志無祖國──讀林孟寰〈同棲時間〉 / 陳栢青
妖山新秀
尹懷慈
作者簡介、創作自述
劇本〈泰迪熊...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