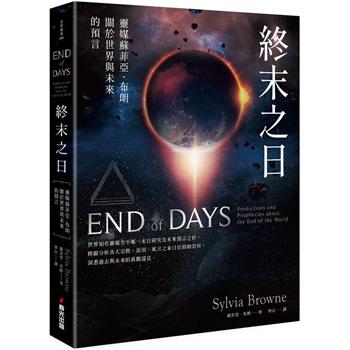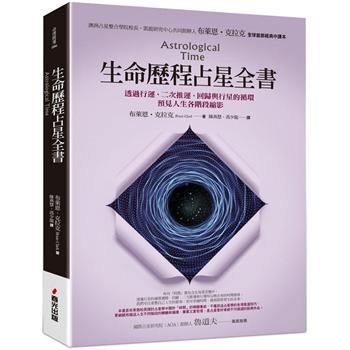內容簡介
一個不被時代窒息的見證者
和他獨守家園20年的妻子
二十年獄中筆記、書信、文件 完整史料首次披露
仍然有一些政治受難者,以自身的苦難作見證,讓我們聽到時代所窒息的名字,聽見來自墳地深處棺木迸裂的聲音。他們也許並非文學家,不是詩人,但他們彌補了文學家、詩人不在場的見證。
國家文藝獎得主 李敏勇
至今我已接近九十之年,回顧自己不過是默默無聞一個平凡的百姓,但一生遭受的種種風波及壓迫,應該將其記述下來供我家子孫或世人的參考,我認為應是一種義務,如能對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有所助益,那就超乎我的期望了。
自序 鍾興福
鍾前輩珍藏這些豐富物件,印證他在軍法處獄中從難友身上或自己所思所想裡,警覺到再怎麼困難的環境下都要存活下去,更要運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留下紀錄,總有一天,歷史會說出他們那個世代為了生存下去,熱切關心土地的理想和胸懷。
採訪後記 曹欽榮
作者簡介:
作者
鍾興福
1921年5月15日出生於坪林鄉(魚逮)魚堀,以工農為業。1955年34歲因涉及王忠賢案被捕入獄,先後在在軍法處、安坑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監禁二十年。1975年54歲依減刑條例釋放,幾經轉折後至南山開墾果園,目前與妻邱採霞長居南山務農為生。
採訪者
曹欽榮
曹欽榮
台灣游藝設計負責人,曾參與規劃台北228紀念館、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長期從事台灣人權文史採訪、博物館規劃工作;目前就讀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這本書是由許多人協助整理,希望透過團隊協力,讓我們的歷史更加鮮活、接近事實。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為了見證,活了下來
李敏勇
在我的文學之路,巡梭了許多時代見證的心靈。其中,又以東歐一些國家在二戰後共產黨統治體制被壓迫的聲音,印象最為深刻動人。
捷克詩人塞佛特(J. Seifert, 1901-1989,198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他的〈河畔公園〉裡,說「到了老年/我學到寧靜的可愛/有時它比音樂更刺激/寧靜中會出現顫抖的信號」。接下來的行句,更是觸目驚心:
「在記憶的叉路口
你會聽到
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夜晚的樹林中
我甚至聽到鳥的心跳
有一回我還在墓園裡
聽到棺木迸裂的聲音
來自墳地深處」
捷克這個國家,在1980年代末期,經由動人的絲絨革命,結束了共產黨統治體制,走向自由化。整個東歐的國家,毫無例外地,也都走向非共的民主新時代。相同的時期,台灣解除戒嚴統治,但國民黨中國體制仍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也沒有結束。
二戰後,東歐各國從納粹德國控制下解放,走向共產黨統治體制。而台灣,則從日本殖民統治,走入國民黨中國以祖國之名的類殖民統治。從二二八事件到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及長期化的戒嚴,塞佛特詩裡的見證,一樣血跡斑斑。但是文學的見證呢?詩的見證呢?
因為從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不只政治困厄延續,語言更從不同的國語轉換情境中,讓跨世代跨時代的人們瘖啞化。失去了語言,找不到語言的出口。再加上,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長期壟控,以及人民的心靈被宰制,扭曲的社會病理,轉型正義即使政黨曾經轉替執政,也未充分實現。
沒有豐富的時代見證心靈反映在文學作品裡,沒有歷史的清洗,沒有像塞佛特一樣的詩對不公不義政治的控訴,沒有足夠的社會觀照力量,沒有足以顛覆一黨統治長期化的覺醒條件……,但是,仍然有一些政治受難者,以自身的苦難作見證,讓我們聽到時代所窒息的名字,聽見來自墳地深處棺木迸裂的聲音。
他們也許並非文學家,不是詩人,但他們彌補了文學家、詩人不在場的見證。鍾興福前輩──這是曹欽榮的稱呼。鍾興福回憶錄──是一個曾經被判無期徒刑、被監禁了21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告白,也是時代的見證。他的患難「同學」盧兆麟前輩,曾是我三十年前職場「同事」,蔡焜霖前輩也是。
蔡焜霖前輩、盧兆麟前輩都有文采,他們從日文而中文,顯露的是知識人的形跡,著書立說自然而然。而鍾興福前輩,自述為一介凡夫,但特殊的人生經歷卻使他不能不舉筆為文,書寫下在政治困厄下苦難的見證。我翻閱著他的回憶錄書稿,對照著曹欽榮在「採訪後記」中的〈認識因緣〉,看到了一位沒有被時代窒息的政治受難人形影。
回顧2008年春,盧兆麟前輩在二二八當天,於馬場町為青年朋友講解白色恐怖歷史而突然倒地。過逝。我在一首詩:〈春祭.馬場町〉紀念他,寫下「彷彿永遠矗立在馬場町/你的形影將冷風轉化成自由的空氣/呼喚青春之歌/那是消失時代裡你的身影」。在2010年春,更從鍾興福前輩的回憶錄書稿裡,看到「我活了下來,為了見證,國家暴力『永不再犯』」的相對性側面。
作為一個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出生的台灣詩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死滅歷史的生之體驗。在我成長的時代,鍾興福前輩及許許多多政治受難者在政治困厄的處境裡印記了歷史。這樣的歷史應該被觀照、不能被抹滅。回憶之書留下見證,記憶著壓迫者罪責的歷史,也提醒錯誤不要再犯。
「書寫──以便記憶
並讓死去的人復活」
敬謹地為鍾興福前輩的回憶錄為序。
名人推薦:推薦序
為了見證,活了下來
李敏勇
在我的文學之路,巡梭了許多時代見證的心靈。其中,又以東歐一些國家在二戰後共產黨統治體制被壓迫的聲音,印象最為深刻動人。
捷克詩人塞佛特(J. Seifert, 1901-1989,198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他的〈河畔公園〉裡,說「到了老年/我學到寧靜的可愛/有時它比音樂更刺激/寧靜中會出現顫抖的信號」。接下來的行句,更是觸目驚心:
「在記憶的叉路口
你會聽到
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夜晚的樹林中
我甚至聽到鳥的心跳
有一回我還在...
章節試閱
當年我被捕時,正當人生青壯黃金時期,那時費盡精力建立的創業途徑全部被毀,離妻離子被關進黑牢,身不由己,拘押期間更是生死未卜,嘗盡人生煎熬,悲憤而痛苦。尤其出獄後,還受情治監視人員的百般刁難,找事工作都處處受到干擾、限制,這中間所受委屈及艱辛的過程,在本書裡都敘列出來。這種折磨及困苦,幸虧獲得賢妻多方鼓勵及支援,才得以克服及度過。
我打聽過,丈夫被判無期,妻子等了二十幾年的,這樣的女人全台灣島只有三位而已,一個是我太太,另外就是高鈺鐺、陳水泉的牽手。我很感激她,我這一生第一遺憾的是耽誤她這麼久,心裡有一些難過。假使是她去坐牢,我可能不會等她二十幾年,以我的見解我會再娶。她能夠等我二十幾年、照顧這些孩子、這個家的完整,我感謝。現在不論任何對或不對的,我都不會跟她反對。
我離家二十年,有關身體健康和家事都靠寫信連絡。我坐牢每週有兩次發信機會,但信要不要發則操之於政治幹事手裡,他心情好就寄出去,心情不好放進垃圾桶。我二十年每週都有發兩次信,無話時也買張明信片畫畫漫畫報報平安,家裡也同樣每週寄兩次。我在泰源九年,孩子生病到死,過程寫了多少信息,一張都沒有收到。父親的事也是,到死都沒有信息,祖父也病到死寫了多少信,隻字都沒收到。
當年我被捕時,正當人生青壯黃金時期,那時費盡精力建立的創業途徑全部被毀,離妻離子被關進黑牢,身不由己,拘押期間更是生死未卜,嘗盡人生煎熬,悲憤而痛苦。尤其出獄後,還受情治監視人員的百般刁難,找事工作都處處受到干擾、限制,這中間所受委屈及艱辛的過程,在本書裡都敘列出來。這種折磨及困苦,幸虧獲得賢妻多方鼓勵及支援,才得以克服及度過。
我打聽過,丈夫被判無期,妻子等了二十幾年的,這樣的女人全台灣島只有三位而已,一個是我太太,另外就是高鈺鐺、陳水泉的牽手。我很感激她,我這一生第一遺憾的是耽誤她這麼久,心...
目錄
目次
006 序 為了見證,活了下來 李敏勇
010 自序
012 改版補述
015 一介凡夫
016 出生時家境
019 阿公的印象
020 從小養成賺錢的念頭
022 小學畢業開始當粗工
024 十八歲經營茶園
025 日本以「軍夫」名義調我去訓練
027 日本警察罵我「清國奴」跟他格鬥
031 結婚成家
032 結婚
032 為盡孝道隨父母離家
035 到宜蘭工作
036 養家的困境
037 日本特別志願軍險些錄取
038 撿取流木死裡逃生
040 妻子桂花死亡的慘劇
045 終戰生活
046 終戰後物價暴漲生活困苦
048 失去女兒富美及續弦
051 組織活動
052 北峰區長葉敏新
052 在松羅坑的活動情形
057 潘溪圳與王忠賢
058 山雨欲來風滿樓
063 逮捕
064 第一次被捕
064 第二次被捕
067 問訊判決
068 押送保安處跟王忠賢對質
071 王忠賢被槍殺經過
073 軍法處判決經過
076 保安處與軍法處的押房
077 軍法處虐待政治犯
079 如果不服上訴會越判越重
079 軍法處戒備森嚴仍有人逃獄
080 軍法處幾則趣聞
085 難友見聞
091 罐子歲月
092 新店安坑軍人監獄
094 獄中的學習
099 一九六二年押送綠島新生訓導處
104 移送泰源監獄坐牢
111 一九七二年送回綠島監禁
113 寫家信及家人接見萬般刁難
121 歸來
122 減刑回家變成陌生人
124 獨吞霸佔,兄弟都不可靠
130 拓墾南山,種梨為生
138 親友趁機侵占,錢財人情債一本
142 陳震東是台灣人當官典範
143 前世福份,太太等我二十年
153 後記
155 邱採霞(鍾興福妻)口述訪問紀錄
191 採訪後記 曹欽榮
213 鍾興福、邱採霞年表
目次
006 序 為了見證,活了下來 李敏勇
010 自序
012 改版補述
015 一介凡夫
016 出生時家境
019 阿公的印象
020 從小養成賺錢的念頭
022 小學畢業開始當粗工
024 十八歲經營茶園
025 日本以「軍夫」名義調我去訓練
027 日本警察罵我「清國奴」跟他格鬥
031 結婚成家
032 結婚
032 為盡孝道隨父母離家
035 到宜蘭工作
036 養家的困境
037 日本特別志願軍險些錄取
038 撿取流木死裡逃生
040 妻子桂花死亡的慘劇
045 終戰生活
046 終戰後物價暴漲生活困苦
...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