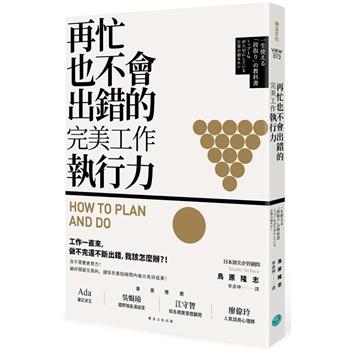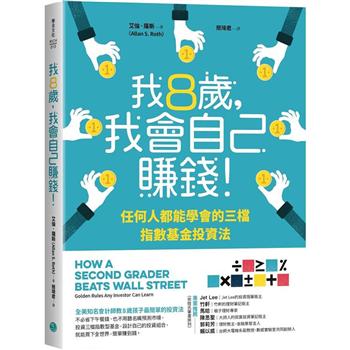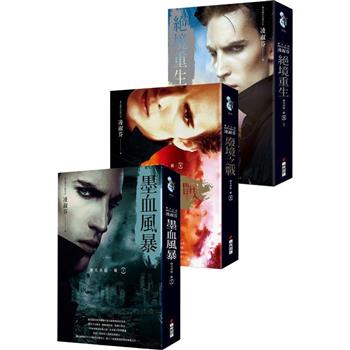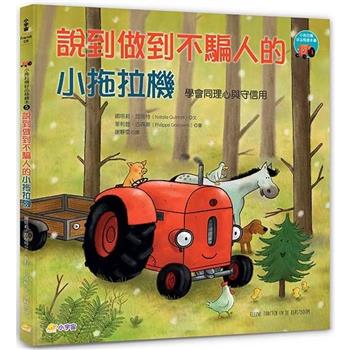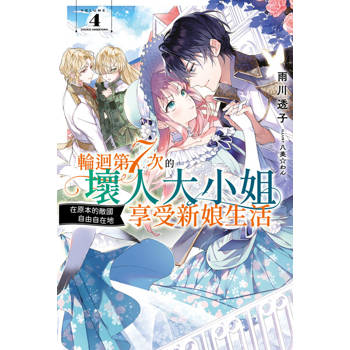古特曼教授在《運動項目與帝國》書中,以九個篇章提供敘述:板球、英式足球、棒球、籃球、美式足球、奧運會、體操、傳統運動、文化帝國主義。
現代運動的發展基本上起源於不見硝煙的帝國運動的擴散和滲透,經過幾百年從涓涓細流到波瀾壯闊的發展,尤其是大眾傳播工具的媒介,已然遍佈世界各角落,深植現代社會經濟的每一層面,成為人類教育和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古特曼教授娓娓道來各運動項目發展的起源,精闢的分析其發展脈絡,在宏觀的了解這些背景故事後,也讓我們對運動的價值和趣味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阿倫.古特曼的圖書 |
 |
$ 316 ~ 360 | 運動項目與帝國:現代運動與文化帝國主義
作者:阿倫.古特曼(Allen Guttmann) / 譯者:彭廣揚 出版社:河中 出版日期:2025-04-2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24頁 / 15.8 x 23.2 x 2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運動項目與帝國:現代運動與文化帝國主義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阿倫.古特曼(Allen Guttmann)
於1932年10月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出生,1953年從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畢業,1953年到1955年之間在美國陸軍服役,1956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1961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博士,2005年歐洲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古特曼是美國麻州阿默斯特(Amherst)學院英文講座以及美國研究榮譽退休教授。
譯者簡介
彭廣揚
大學時代研究英美文學及戲劇,四十年來,一直採訪美國暨國際運動新聞及人物,並且在運動報導平台撰寫專欄。
丁廼靜
大學畢業後從事專職翻譯,曾翻譯中西文化書籍多種。
阿倫.古特曼(Allen Guttmann)
於1932年10月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出生,1953年從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畢業,1953年到1955年之間在美國陸軍服役,1956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1961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博士,2005年歐洲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古特曼是美國麻州阿默斯特(Amherst)學院英文講座以及美國研究榮譽退休教授。
譯者簡介
彭廣揚
大學時代研究英美文學及戲劇,四十年來,一直採訪美國暨國際運動新聞及人物,並且在運動報導平台撰寫專欄。
丁廼靜
大學畢業後從事專職翻譯,曾翻譯中西文化書籍多種。
目錄
致謝
引言—現代運動之發明與傳播
第一部分 傳播
1. 板球
2. 英式足球
3. 棒球
4. 籃球
5. 美式足球
6. 奧林匹克
第二部分 抗拒
7. 體操
8. 傳統運動
第三部分 評鑑
9. 文化帝國主義?
註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引言—現代運動之發明與傳播
第一部分 傳播
1. 板球
2. 英式足球
3. 棒球
4. 籃球
5. 美式足球
6. 奧林匹克
第二部分 抗拒
7. 體操
8. 傳統運動
第三部分 評鑑
9. 文化帝國主義?
註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序
引言
現代運動之發明與傳播
語言提供探究文化史一道簡便的線索。軍事用語中常見的法文(lieutenant 「副官」、reconnaissance「偵察」),以及音樂術語常見的義大利文(aria 「詠嘆調」、allegro 「快板」),皆是舊時政治或藝術強權遺留於語言上的痕跡。我們暫且忽略如tennis「網球」與judo「柔道」之類的例外,用稍加誇張的說法,現代運動語言,即是英語。德國足球迷們表達讚賞時,會高喊einen guten Kicker「了不起的球員」;法國短跑選手們在le starting-block「起跑架」上,緊張地等待;拉丁美洲人民為futbol「足球」而瘋狂;日本人也透過對supotsu「體育」的熱愛,展現他們的現代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現代運動算是英國的發明。於是,世界各地的人們便自英語借用前述及其他的運動術語;1現代運動也因而從不列顛群島開拔,前進征服全世界。
關於現代運動起源於英國的主張,誠然有些誇大。畢竟,棒球、籃球和排球皆發明於美國,且由美國人廣為傳播,而非英國人。法國人亦扮演重要角色;西元一九○三年,為提升體育報L’Auto的發行量,亨利.戴斯格朗傑(Henri Desgrange)創辦頂級國際自行車盛會,Tour de France「環法自行車賽」,啟發了西元一九○九年的Giro d’Italia「環義大利自行車賽」以及其他許多艱難的賽事。2(在現行的術語中,法國影響力可見一斑,如,velodrome「自由車室內、外比賽之場館」、peloton「比賽中的主集團」以及derailleur「變速器」。)儘管如此,自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相較其他國家,大不列顛王國對於現代運動之發展,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才取代英國人,成為現代運動傳播主要推手。
現代運動之發明與傳播
語言提供探究文化史一道簡便的線索。軍事用語中常見的法文(lieutenant 「副官」、reconnaissance「偵察」),以及音樂術語常見的義大利文(aria 「詠嘆調」、allegro 「快板」),皆是舊時政治或藝術強權遺留於語言上的痕跡。我們暫且忽略如tennis「網球」與judo「柔道」之類的例外,用稍加誇張的說法,現代運動語言,即是英語。德國足球迷們表達讚賞時,會高喊einen guten Kicker「了不起的球員」;法國短跑選手們在le starting-block「起跑架」上,緊張地等待;拉丁美洲人民為futbol「足球」而瘋狂;日本人也透過對supotsu「體育」的熱愛,展現他們的現代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現代運動算是英國的發明。於是,世界各地的人們便自英語借用前述及其他的運動術語;1現代運動也因而從不列顛群島開拔,前進征服全世界。
關於現代運動起源於英國的主張,誠然有些誇大。畢竟,棒球、籃球和排球皆發明於美國,且由美國人廣為傳播,而非英國人。法國人亦扮演重要角色;西元一九○三年,為提升體育報L’Auto的發行量,亨利.戴斯格朗傑(Henri Desgrange)創辦頂級國際自行車盛會,Tour de France「環法自行車賽」,啟發了西元一九○九年的Giro d’Italia「環義大利自行車賽」以及其他許多艱難的賽事。2(在現行的術語中,法國影響力可見一斑,如,velodrome「自由車室內、外比賽之場館」、peloton「比賽中的主集團」以及derailleur「變速器」。)儘管如此,自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相較其他國家,大不列顛王國對於現代運動之發展,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才取代英國人,成為現代運動傳播主要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