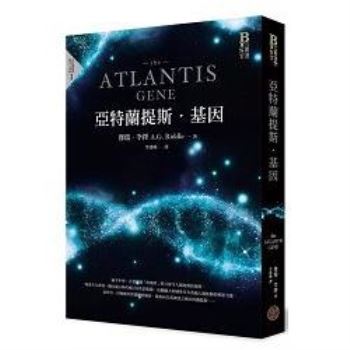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陳芳珮的圖書 |
 |
$ 280 電子書 | 回家:在社區得到復健與支持,精神病患也能安居樂業。當生活過得好,生病又如何?
作者:陳芳珮 出版社: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8-28 語言:中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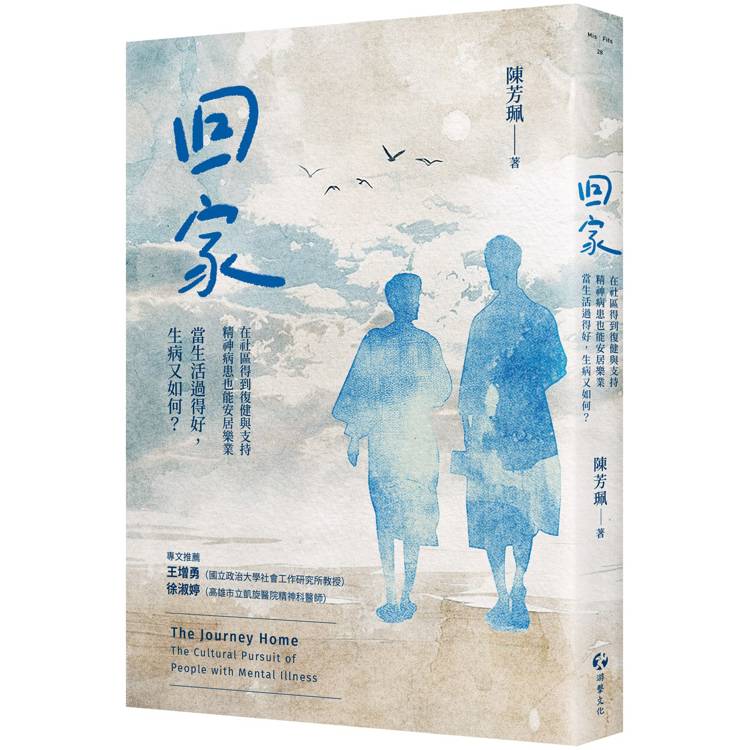 |
$ 280 ~ 378 | 回家:在社區得到復健與支持,精神病患也能安居樂業。當生活過得好,生病又如何?【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陳芳珮 出版社: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8-28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陳芳
|
 陳芳字國芬,廣東省香山縣黃茅斜村人,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華僑商人,夏威夷王國貴族。
陳芳字國芬,廣東省香山縣黃茅斜村人,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華僑商人,夏威夷王國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