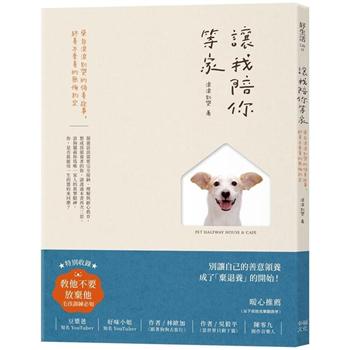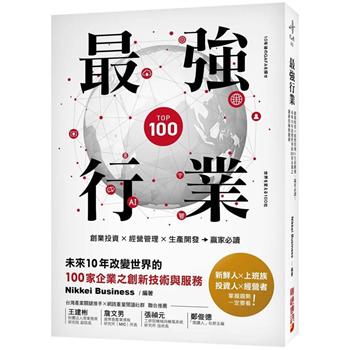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馬克.波里佐提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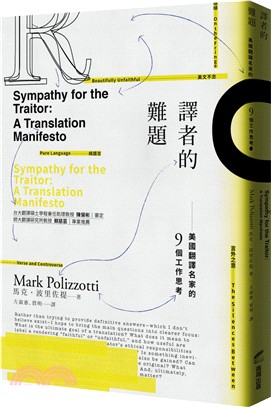 |
$ 199 ~ 360 | 譯者的難題:美國翻譯名家的9個工作思考
作者:馬克‧波里佐提 / 譯者:0px;">譯者的難題:美國翻譯名家的9個工作思考 出版社:商周文化 出版日期:2020-04-07 規格:21cm*15cm*1.5cm (高/寬/厚) / 初版 / 平裝 / 288頁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有人認為,翻譯是文學的窮親戚,是必要之惡,甚至是明目張膽的扭曲之舉——就像義大利古老的文字遊戲所言:「traduttore, traditore」,意思是「翻譯,背叛者也」。但也有人認為,翻譯是通往跨文化理解與豐富文學的康莊大道。在這本分析縝密、發人深省的研究中,作者馬克・波里佐提循著更有建設性的路線,重新界定這項爭論。他拒絕兩極化的簡單思考及越漸抽象的翻譯理論,而是清楚聚焦在重要問題上:翻譯的終極目標是什麼?為翻譯貼上「忠實」的標籤是什麼意思?(對什麼忠實?)翻譯是否勢必會失去什麼?能不能有失亦有得?翻譯重要嗎?若是重要,原因為何?作者敢於表達一己之見,寫下這本既是實用指南,也是宣言的著作,請讀者同情翻譯者,不把譯者視為「叛徒」,而是作者的創意夥伴。
波里佐提是譯者,曾譯過莫迪亞諾、福樓拜等名家之作,在本書中探討什麼是翻譯、什麼不是翻譯,以及翻譯如何能發揮功用,或是徒勞無功。他寫道,翻譯「遊走於藝術與工藝、創作與複製、利他與商業、天才與匠氣之作的邊緣」。在本書中,作者教我們解讀的不光是譯本,更是翻譯之舉本身;不把翻譯視為有待解決的問題,而是應該頌揚的成就——就像歌德的所言,翻譯是「不可能、必須,且是舉足輕重」的一件事。
各界好評
本書節奏明快,清晰易懂,宛如引人入勝的旅程,訴說翻譯是什麼,具有何種功能。波里佐提回顧兩千年來關於這個主題的思維,一掃深奧的學術理論,清楚展現容易引起共鳴的易讀性。之後,他提到翻譯時心靈融合的奇特之處,並進一步探索跨語言的遼闊範圍。這本小書值得成為權威之作。
——盧克・桑特(Luc Sante);著有《另一個巴黎》(The Other Paris);譯有費利克斯・費尼雍(Félix Fénéon)的《三行小說》
翻譯是最細膩的藝術,也是許多人都看不出來的模仿魔法。讀者把翻譯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少了翻譯,恐怕就會迷失。波里佐提在本書中,生動清晰地說明翻譯的風險與過程中的棘手選擇,不僅如此,還進一步探討長久以來在文化彼此碰撞、世界越趨均質時衍生的問題,並談論如何在促進了解時保留差異。這本優美的必讀之書,出現得正是時候。
——蓋瑞・印第安納(Gary Indiana),著有《我能給你一切,除了愛》(I Can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以及《黑暗中行事》(Do Everything in the Dark)
生動、好讀,趣味橫生⋯⋯以一系列迷人又奇特的系列文章,訴說在全球化的世界越發重要的主題⋯⋯波里佐提讓人覺得翻譯文學的創作與閱讀,可以是真正快樂的經驗。
——艾蜜莉・威爾森(Emily Wilson),《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本書深入淺出,旁徵博引,最重要的是引人入勝,兼具趣味與啟發性⋯⋯讀起來精彩有活力,宛如一股清涼純淨的空氣,吹入充滿教條與霉味的教室裡。
——法蘭克・懷因(Frank Wynne),《旁觀者》(THE SPECTATOR)
本書兼具深度與廣度,細節一絲不苟,提出關於翻譯是什麼、應該是什麼,以及為何重要的宣言⋯⋯波里佐提的著作展現他的專業與數十年的經驗,精確訴說內行人才知道的學門細膩之處,同時又熱情擁護這一行的廣大價值。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波里佐提說,沒有完美的翻譯,還說:「那樣會更好」。翻譯值得與其他藝術表達形式平起平坐,這過程應該「從家庭與學校開始」。這本書理當能啟發這樣的改變。
——安娜・阿絲蘭雅(Anna Aslanyan),《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本書深入淺出,旁徵博引,最重要的是引人入勝 、趣味橫生,能啟迪人心。波里佐提的主張令人精神抖擻,宛如一股清新的新鮮空氣,吹入滿是教條與霉味的教室。他拒絕說教地告訴我們翻譯「對我們好」,好像翻譯只是文學魚肝油,反而著重在能「帶來特殊的喜悅、引進無法取代的探索之喜,那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聲音」。他提出有說服力的主張:如果翻譯文學在當今世上有價值,是因為這些心靈與聲音極為珍稀,我們忽視不起任何一個。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本書中,作者提出犀利的宣言,鬥志十足,反對「譯者,背叛者也」的格言。他指出,譯者不是誹謗者或背叛者、鬼魅或鸚鵡,也不是工具人,而是如約翰・藍儂所言,是自己寫作的作者。長久以來,理想的譯者總是要在偉大原作的後方,不出鋒頭,但這樣的想法無法完全衡量出譯者的關鍵角色,讓他們與作者並駕齊驅。「必須尊重自己的作品,」波里佐提寫道,「相信自己的譯作本身就有自己的優點(或瑕疵),值得公評。因此如果譯文適當完成,就能與原文平起平坐。」
——《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
波里佐提認為,無論譯者的技藝如何隱而不見,都應該和藝術家一樣值得注意。隱藏自己的聲音,是一門藝術,讀者也該學著尋找這聲音。換言之,波里佐提要求讀者不要終止信念,而是在相信的行為中克制自己。
——美國書評網(Public Books)
作者簡介:
馬克.波里佐提Mark Polizzotti
傳記作家、評論家、譯者、編輯、詩人。二○一六年獲頒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文學獎,與法國文化部藝術與文學勳章。
法文譯作超過五十本,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福樓拜、詩人胡賽(Raymond Roussel)、作家兼導演瑪莒哈絲、作家及詩人布勒東(Andre Breton)、文化理論家及美學哲學家維希留(Paul Virilio)。
文章與評論散見《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圖書廣場》(Bookforum)、《國家》(The Nation)、《華爾街日報》、《帕納蘇斯》(Parnassus)、《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等報章雜誌。亦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出版品發行人兼總編輯。
著有《心靈革命:安德烈.布勒東的一生》(Revolution of the Mind: The Life of Andre Breton)等書。
譯者簡介:
方淑惠
(前言~第一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從事翻譯工作十餘年,譯有《孤雛淚》、《你出生那天,就是我的父親節》、《濟貧院的陰影》、《大藍海洋》、《星星男的天文大夢》、《去你的癌症》、《我的法國城堡夢》、《便便學問大》、《一生必遊的500經典路線》、《美麗的謊言》,以及《奇幻之屋》系列六部曲等書。
賈明
(第二章~第九章)
翻譯所畢業,曾任職金融業與出版公司。目前的任務是:把不該忽視的聲音,盡力傳達出來。
引 言:基本規則
第一章:翻譯可行嗎(究竟何為翻譯)?
第二章:聖人、殉道者與間諜
第三章:純粹的語言
第四章:美文不忠
第五章:言外之意
第六章:憐憫背叛者
第七章:作詩與辯論
第八章:懸崖邊緣
第九章:翻譯重要嗎?
附 注
參考書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