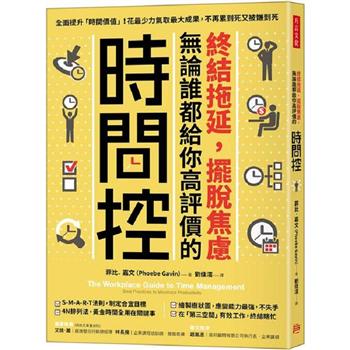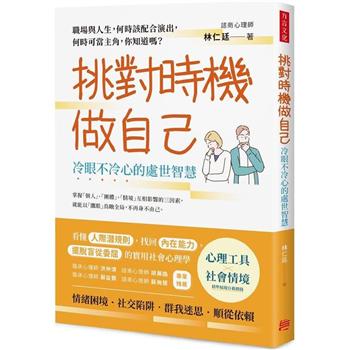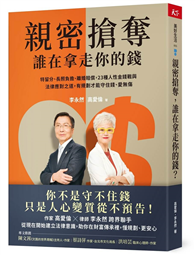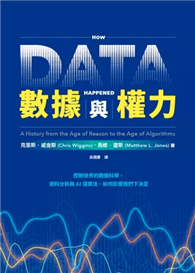1803年,普魯士王國的柯尼斯堡發生了一連串的殺人命案,動機不明,一時之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一位年輕檢察官在哲學大師康德的安排下前來調查,將康德批判哲學的原則運用在刑事辦案上,循著犯罪現場留下的蛛絲馬跡,追到人類理性的邊緣,腳下是人心深淵的無盡黑暗。真相,總是令人膽顫心寒……歐洲哲學發展到十八世紀,英國經驗主義與歐陸理性主義兩大傳統涇渭分明:前者以洛克、休謨為代表,認為人心有如一張白紙,全賴後天的經驗形塑;後者有高唱「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兒,認為經驗不足恃,確定的知識都來自理性。兩派相持不下,話不投機,幸好出了個康德,歐洲哲學才有轉機。這位日耳曼哲學家以一人之力完成「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1781)、《實踐理性批判》(1788)和《判斷力批判》(1790),不但融匯調和了兩大哲學派別,整個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沒有一個不受康德影響。甚至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維根斯坦、存在主義的沙特、現象學的胡塞爾,乃至當代哲學巨擘哈伯瑪斯、羅爾斯,都在回應康德哲學提出的課題。《謀殺理性批判》的作者高明之處,是在歷史的空隙中架構了一個飽滿又鮮活的虛構世界。一般人對康德的印象流於刻板沉悶:一個終身未娶的哲學教授,一輩子沒離開過柯尼斯堡,生活極為規律,一絲不苟到城裡的居民可以用他出門散步來對時。但是作者卻勾勒出一個有血有肉的康德:瘦小而精明的老者,睿智又充滿好奇心。同時也提醒了讀者,康德所處的乃是一個非常動盪的歐洲:啟蒙理性澆灌出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也孕育了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的崛起摧毀了貴族階級,也把歐洲帶入腥風血雨之中。理性主義走到非理性的暴力,是理性最大的嘲諷。康德沒有活著見到十九世紀的歐洲轉而走到理性的對反面,投入浪漫主義、乃至潛意識的懷抱。但讓人好奇的是,康德在1790年就已完成龐大哲學體系的建構,窮盡理性範疇的探討,難道到他去世的這十四年間,沒有想過再跨一步,探索非理性的黑暗深淵?《謀殺理性批判》正是玩味了這個可能性,頗有康德「第四批判」的意味,只是康德這部哲學巨著不純然是哲學的思辨,而是一連串以人命與鮮血為代價的人性實驗。整個柯尼斯堡都是康德的哲學實驗室,作者用非常詭異的方式謳歌了「敢於求知」的啟蒙精神!
章節試閱
一輛漂亮的黑色馬車,停在堡壘的大門外面等我。
我朝馬車走過去,臉上掩不住笑。康德教授就坐在緊閉的馬車窗戶裡面,一個勁兒看他的懷錶。他對準時的要求已達癡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我才要舉起拳頭輕敲玻璃車窗向他報告我到了,就有一隻手輕輕在我手肘上面點了一下,我的耳邊也有人在說:「可以借一步說話麼?大人?」
那一天早上,在河邊,一直悉心照料康德的男僕,就躲在馬車後面朝我偷偷示意。方正堅毅的大臉那一天早上毫無表情,這時候卻顯得緊張又沉重。
「約翰尼斯.奧登,沒說錯吧?」
他跟我使一下眼色,要我到馬車後面他那邊一趟。
「你家主人最見不得人浪費時間。」我警告他一句。
「幾句話就好,大人,不要太久的,」他沒放鬆,還用大拇指朝馬車和坐在裡面的貴客比一下手勢。「最近出的這些事,可苦了他,大人。今天早上在河邊看到的事,對誰都沒一點好處,大人,何況像他這般年紀,性子又敏感、容易緊張的老先生。」
「你也在場,應該看得很清楚,」我壓低聲音:「康德教授的身體或許是弱了一點,但看來還撐得住。」
說不定我該先跟這男僕說一下,危機已經過去,案子已經破了,只是,這樣的大事,我可不想沒跟康德說就先透露給他的男僕知道。
「他一直在忙這些案子的調查工作,沒日沒夜的,大人,」男僕回答:「有的時候甚至整晚不睡……」
「整晚?」我打斷他的話:「都在忙些什麼啊?」
「寫東西,我想是吧,大人。」
我想起雅赫曼先生提過的論文,只是,雅赫曼自己都懷疑真有這樣的論文嗎?「你知道他在寫些什麼嗎?」
約翰尼斯.奧登聳一下他的寬肩,無所謂的樣子。
「他有危險,大人,」他再把話題拉回去:「真的有危險。今天早上,大家在河邊都看到他和您一起。現在,您又坐他的馬車到處走。今天早上我們要出門前,我才看到一樣東西,您一定要看……」
「約翰尼斯!」一聲煩躁的怒斥,嚇了我們兩個一跳。「史蒂文尼檢察官到了沒有?」
我跟男僕比一下手勢,要他趕快繞過馬車,我自己則是一個箭步趕上前,去見康德教授。
「我到了,教授,」我口氣盡量輕快:「不小心把文件忘在辦公室裡沒拿,再跑回去拿。不知柯賀隊長可以跟我們一起去麼?」
我朝柯賀點一點頭,要他往前站上一步。
「沒問題,」康德的口氣很不耐煩。「我們要快一點,路很遠,冷得要命。」
「去西伯利亞,是吧?教授?」我拿他打趣,知道一定會一擊中的。康德就愛聽小道消息,這跟他分秒必較的性子一樣出名。有船就要開到皮勞港去的消息,他絕對不會漏掉。在那一陣子普魯士報上,這消息一直登得斗大。
「也沒遠到那裡去啦,」他笑了:「冷倒是有得比。」
我也開懷一笑。那時候我心情好得不得了。案子已經破了,只剩官樣文章要做。尤里希和葛妲.托茲夫婦就算逃得過絞刑手,也一定會被發配到冰天雪地的邊荒。我不知道康德教授要帶我們去哪兒,也不知道他要我們去看什麼。管它呢,我心想,逗逗老人家開心,雖然對辦案不會有定乾坤的影響,但也無傷大雅。
馬車往前轆轆急行,我只盼著他會開口問一下我那一天下午偵辦的進度如何。他應該不會不急著想要知道事情怎麼樣了吧?那一天早上,他是有過公開的質疑,但後來,還是催我快去偵訊尤里希和葛妲.托茲夫婦。所以,他一定很想知道他們兩個說了些什麼。
「你的新住處,你還滿意吧?」他忽然開口問我:「和『波羅的海捕鯨人』的舒適絕對沒得比,我敢打賭。托茲太太做的烤豬排,可是遠近馳名的喲。」
他這是在揶揄我嗎?我住過的客棧老闆娘的廚藝,他那麼有興趣啊?
「客棧那裡當然舒服。」我縱使滿腹狐疑,也不得不老實承認。
「我就知道那裡能讓你賓至如歸,」康德說時,臉上泛起溫煦的笑。「至於柯尼斯堡的堡壘,就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雅赫曼先生煩惱的,就是他這樣子嗎?康德的心思,好像都放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上面,盡是關心一些他不需要去管的閒事。此前二十年,他向來只在家裡用餐,哪兒也不去;普魯士各家報社爭相報導他的生活習慣,眾口一聲都是這樣的說法。名人還真是沒有祕密逃得過新聞界的法眼。
「堡壘那地方還真只是會壞了人的興致,」他話鋒一轉,心情跟著一變:「我很小的時候一看到它就寒毛直豎。我母親和我每天早上到虔信會教堂去時,都要經過堡壘那邊。但她說,我那害怕,比起終有一天要站在造物主面前直視祂眼睛的那恐懼啊,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
康德教授的眼睛落在馬車窗外,像迷路的小孩。堡壘已經遠遠落在我們身後,但對他彷彿仍歷歷在目。「你今天晚上會在那裡過夜嗎?漢諾?他們都說那裡有很多鬼,以前被條頓騎士團關在地牢裡死掉的人的鬼魂。」
這要教我怎麼回答?柯賀和我互看一眼,兩人都不敢回話。馬車嘩啦啦駛過古老的木橋,一大團濃霧從護城河墨黑、沉靜的水面捲來,像湧起層層渦旋的密雲。傍晚的天光愈來愈暗,只剩堡壘高聳的主樓還看得到,就在上方,佇立在山丘上面。城垛在低低的雲氣上方,像隔著厚厚的一堵霧靄,偷窺人世。
康德朝我這邊看過來:「就快到了!」他說得很開心,馬車也忽然急轉彎,轉向右邊,駛過另一道木橋。顯然,他要我們看什麼,終於要揭曉,他很興奮。「我看你一直都在數橋吧?」他說。
「橋?教授?」我不懂他在說什麼。
「那一道數學題啊?」他回答:「他死前,我是說那一位大數學家萊昂哈德.歐拉27,他問過一個問題:有沒有辦法找到一條路線,穿過柯尼斯堡,把布勒格爾河上的九道木橋全都走過一遍,但不會有一道橋重覆?等到了那裡,你可以想一想。」
我只好開口提醒他,我到柯尼斯堡來要幹的事,但他沒空理我。「我剛在大學教書時,」他接下去說:「和一個同事打過賭;他和這一位大數學家是好朋友。他跟我說,其實連歐拉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唔,這問題我倒是想出了兩種解答……」
還沒完呢;他轉向我,一隻手搭在我的手臂上,急急催我:「托茲夫婦他們的事,你有什麼要跟我說的沒有?」
有好一下子,我不知該如何作答。我該跟他說案子已經破了,罪犯已經關入大牢等著受審嗎?我要跟他說那一根什麼魔鬼爪子,管它是什麼鬼,在這時候根本都不重要了?
「作丈夫的已經招了,教授,而且,招得很乾脆。」我回答他。我特別小心把一樣樣事情按照先後順序,一一講給康德聽,還特別留心,把不時溜到嘴邊的勝利歡呼壓下去,盡量不動聲色。
「嗯,這樣子啊,」他說:「荼毒柯尼斯堡好一陣子的禍害,起源就是政治陰謀。是恐怖暴行,目的在……」
他忽然停下來,看向我。
「目的在什麼呢?這幾名罪犯說了他們最終的目的是什麼沒有?」
「沒說多少,教授,」我老實承認:「尤里希.托茲好像相信,這幾件命案引發的恐慌,會削弱人民對君主的信心,激起某種革命。我覺得他挑中這些人,都是因為他們是眾所周知的仇法派。」
康德教授靠回椅背,眉開眼笑。
「喔,我知道了。他真是聰明!那我想,他也跟你說了他用來殺死莫里克的凶器囉?」
我在皮面的長條椅上動了動,略有不安。
「他說是用榔頭,教授。」
康德聽了我的回答,好像更開心了。「大榔頭嗎?史蒂文尼?還是小榔頭?」他問我道。
「是……這還只是初步的偵訊而已。」我支支吾吾。我原以為他會大大誇我一下,結果,反而是以犀利的心智三兩下就把我辦案手法的缺點整個拆穿。「托茲是招認過,他用來殺害其他幾名死者的凶器各不相同。」
「不止一種啊?」康德皺起眉頭。
「他說是順手抓到什麼就用什麼,」我趕快補上一句:「當然了,教授,我會問到他把所有細節都交代清楚為止。」
「最最重要的就是細節,」康德像在跟我透露祕密:「國王陛下會想知道他的敵人勢力到底有多大,人數又有多少。」
他這有諷刺我的意思嗎?我覺得自己好像學生交作業給老師,老師說作業做得很好,很好,只是可以再好很多。這時候,康德忽然大笑出聲。他沒說是什麼事情好笑。我倒不知道他有這般飄忽不定的性子,心頭的忐忑當然更壓不下。柯賀應該也是吧;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得很清楚。
「我很高興你找到了通往真相的康莊大道,」康德說道:「你會不會也恰好把大家說的魔鬼爪子拿去問過尤里希.托茲吧?」
「檢察官大人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完成所有的偵訊工作。」柯賀隊長插嘴進來。他對我的職權十分尊敬,絲毫不輸他對隆肯檢察官時的態度。普魯士這裡的官僚制度,就是以出產這樣的人出名。恭順、服從到極點.有的時候甚至還很魯鈍。
「不管這個魔鬼爪子是什麼東西,」柯賀再說下去:「不管大家怎麼說這東西,看來都無關緊要,康德教授。史蒂文尼檢察官已經揭發了他們的陰謀。」
「我親愛的柯賀隊長啊,」康德輕聲回答:「假設不要推得太遠。依我的經驗,人世裡,眾人的聲音比起其他一切,都要更貼近真相。」
「尤里希.托茲已經承認是他殺了那孩子,」柯賀隊長的口氣十分堅定:「他承認其他人也都是他殺的,史蒂文尼先生已經抓到了真凶,教授。」
我沒想到,康德教授遭人直言反駁卻一點也不以為忤。他點了點頭,若有所思。「那我可以理解,等一下我要拿給你們看的東西有什麼用處,你應該會有一點意見,柯賀先生,」他再說下去:「我也欣賞你直言不諱的性子;像我這一位年輕朋友,就只知道緘默、恭順。我敢說,你的看法史蒂文尼先生應該也同意。我也只能懇請兩位稍安勿躁,再一下就好。兩位即將親眼得見我畢生研究的最獨特成果。」
我的心跳變得更快。伊曼紐.康德連他最要好、最親近的那些朋友都藏著不給看,居然要給我看?
「我說一定又是曠世巨著,教授,」我熱切回應:「從您的筆下寫出來的書……」
「書?」他凹陷的臉上驚訝的表情很明顯:「你以為我要給你看的是書啊?史蒂文尼?」
「世人對您的新作,翹首以待委實太久,教授。」我回答他。
他沒馬上回答。等他終於開口,樣子卻比先前還要更激動。「書……書!有何不可?」他說時,把下巴搭在一隻攢起來的拳頭上面。「那要取什麼書名才好呢?嗯,就這情況看,就叫《謀殺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riminal Reason)吧;我想這樣應該可以。」
「我等不及要拜讀大作。」我說得興高采烈,馬車轆轆在山坡上往上爬。
康德笑得很開心,兩片嘴唇朝兩旁咧得大開,露出嘴裡所剩無幾的發黃尖牙。老實說,不怎麼好看。
「你已經接收了隆肯的辦公室,我想是吧?那你讀過他七拼八湊寫出來的命案報告嗎?」
「昨天讀的,」我迫不及待作出回答:「十分有用,教授。而他的看法也因為托茲-就是那個客棧老闆-今天下午招供而證實了……」
「你是說政治陰謀?你真的覺得這幾件命案的背後有政治陰謀?」康德打斷我的話,一隻手還揮了一下,一副不屑的神氣。「維吉蘭修抓到的還更貼近事實!」他這一句話的口氣相當激動,幾近乎暴怒。「昨天晚上,你怎麼就沒耐性看他把事情做完?你該留到最後的。隆肯先生是老派的治安官。只會蒐集線索,不會別的。至於真相,也只能巴望從別人的嘴裡嚇出來。有的時候,是被他嚇出來了沒錯,但這一次,行不通了。他的想像力太遲鈍,和凶手根本沒得比。維吉蘭修挖出來的事就多得多,你卻不肯把他的見解納入考慮。」
我斜睨柯賀一眼。他臉色凝重,肌肉緊繃、僵硬,顯然要費很大的力氣才不會出聲替他忠心侍奉的已故長官辯駁。不過,有一件事倒很明確:沒人跟康德教授說這一位治安官已經過世。
一輛漂亮的黑色馬車,停在堡壘的大門外面等我。我朝馬車走過去,臉上掩不住笑。康德教授就坐在緊閉的馬車窗戶裡面,一個勁兒看他的懷錶。他對準時的要求已達癡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我才要舉起拳頭輕敲玻璃車窗向他報告我到了,就有一隻手輕輕在我手肘上面點了一下,我的耳邊也有人在說:「可以借一步說話麼?大人?」那一天早上,在河邊,一直悉心照料康德的男僕,就躲在馬車後面朝我偷偷示意。方正堅毅的大臉那一天早上毫無表情,這時候卻顯得緊張又沉重。「約翰尼斯.奧登,沒說錯吧?」他跟我使一下眼色,要我到馬車後面他那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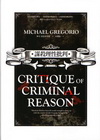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