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找回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母親?這些年來,我隱身在別人的生死故事裡,而她只活在我破碎的記憶中。」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從戰地回到廚房,藉著可以喚起對母親最甜美回憶的地方,展開一趟通往寬恕的旅程。
進廚房把不同風味的食材混在一起,也許能讓我回到小時候的時光;我想找回十歲以前認識的媽媽,那位優雅、聰慧、精神正常的母親。
在母親過世之前,他就已經失去了她,因精神上的疾病,命運之神從他的生命中奪走這位曾經優雅迷人的女性,也徹底毀掉他的童年。
長大後,他坦白傾訴自己通往寬恕的旅程,這趟旅程帶他回到母親留給他最多幸福回憶的地方——廚房。
透過追憶小時後的快樂時光、廚房點滴和對母親的記憶,他述說一個讓人印象深刻、感動人心的故事:關於家庭、食物和愛。
在這本文筆優美的回憶錄裡,普立茲新聞獎得主麥特.麥肯艾列斯特將鏡頭從戰地拉回廚房,一個可以喚起對母親最甜美回憶的地方,娓娓道來他與長年患精神病的往生母親重新連結的歷程。
麥特.麥肯艾列斯特的童年時光本來像田園詩般美好,那時他的母親會為全家人準備像天堂一樣美味的食物,再綴滿歡樂與笑聲。後來母親脫序,酗酒,從他十歲起少有清醒的時刻,在他成長的歲月中缺席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他只能孤單無助看著熱情機敏的母親,被那無從理解與診斷的疾病折磨摧殘。
最後他不顧一切地逃開,成為海外特派記者,走訪世上最危險的地方,從貝魯特到巴格達,隱身在恐怖行動與他人的悲劇裡。可是戰地的所見所聞仍沒讓他做好準備去面對曾經優雅、曾經生命力旺盛的母親終於過世的事實。
接下來那幾個禮拜和幾個月,麥特發現自己在家裡的舊照片和舊信件裡試圖找回母親。而就在他重新翻看母親珍藏已久的多本食譜時,這才明白唯有透過母子間共同熱愛的事物,才是找回母親的最好方法:她曾用滿滿的愛心為他烹調各種食物,那是他歡樂的源頭——從烤肋排到烙餅,再到手工草莓冰淇淋,這些在回憶裡似乎都是快樂時光的精華所在。在透過廚房回溯自己生命歷程的同時,他也如母親用美食餵養他般滋養另一個新生命。
麥肯艾列斯特以新聞記者特有的精練文筆與說書人般的優雅姿態,帶領我們走過漫漫傷悲的季節——烹飪、飲食與回憶——同時描繪他與妻子求子的坎坷歷程。
《廚房裡的家教課》是一本交織著家庭、食物與親情等故事的回憶錄,在食譜的點綴下,喚起所有過往美好的回憶與未來的希望。
作者簡介
麥特.麥肯艾列斯特(Matt McAllester)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在他與妻子潘妮拉(Pernilla)回到倫敦定居之前,曾擔任過《新聞日報》(Newsday)的海外特派記者,他表現非凡,榮獲多個獎項,包括以2006年的尼泊爾專題報導得到奧司邦艾略特卓越獎(Osborn Elliott Award for Excellence),他的國際新聞報導也屢獲多家海外新聞俱樂部的表揚。目前是《細節》(Details)雜誌的特約編輯。
譯者簡介
高子梅
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華威葛瑞廣告公司AE及智威湯遜廣告公司業務經理和總監,現專事翻譯。譯有《模範領導》、《世界咖啡館》、《賈伯斯在想什麼》、《抉擇》、《瑞秋.卡森:自然的證人》、《貓戰士》等書。


 共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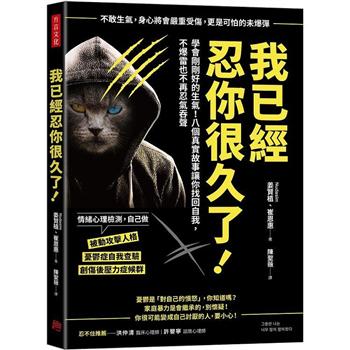










食譜不過是教人作菜,經歷母喪的心情的文章往往只是未亡人的苦水出口。如果食物味道的記憶是喪母之痛的救贖呢? 這本書是作者經歷喪母之痛的作品,作者媽媽發病二十五年,以致於在作者十歲以後,媽媽完全在自己的人生裡頭缺席,直到過世。 本書讓我聯想起偉大作品『家傳大煎鍋』,料理與人生一樣,得回到起點-食物的起點、餵養的起點與愛的起點。料理講究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頓飯,它在乎的是家人,用愛料理,用愛生活。料理別想要偷雞摸狗,是得花時間慢燉細熬。 作者陳述自己自從他媽媽過世後,一直到喪禮前,自己的腦袋似乎關閉了大半。他回顧三十多歲的日子中與母親的共同聯結非常少,僅有的只是童年時在廚房與餐\桌上的母愛回憶,於是作者決定從媽媽遺留下來的食譜中去找尋那失去多年的「媽媽的味道」。想要藉由作菜去複製那遺失多年的時光:家人一起聚在廚房裡,搬出成打的洋蔥剝皮,辛辣的味道嗆得大家眼淚\直流但卻笑聲不斷。 回想往事是治療傷痛的必經過程,只是它需要費點力氣,喚醒記憶亦然,作者在廚房內接觸亡靈,讀媽媽生前收藏的食譜,藉此探索媽媽的過去,讓兒時的記憶之門打開。 於是他走進廚房,翻著他媽媽留下來的遺物:食譜『法國鄉間料理』,找回媽媽的方法,走進廚房,照她的食譜一道一道做菜。讓這些菜餚一入口便能帶人回到記憶的過往-他曾經試圖遺忘的過往。食物是最佳的記憶指南,從零星片刻的回憶裡找回十歲以前認識的媽媽。 他藉由媽媽的食譜改變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作者是個戰地記者,只能靠想像躲進還未被探索的烹飪王國裡,躲進那個很舒服的世界藉此逃避殘酷的戰爭。 作者與他老婆也是在這段守喪期間開始著手懷孕之事,孕育生命的過程對許\多人來說再簡單不過,但對於不易懷孕者而言卻是無窮盡的煎熬,為了迎接那新生命,作者想要烹飪出媽媽的食譜上的美食去餵養他的老婆和他們在肚中的下一代。媽媽去世留下的空虛感,與肚中胚胎形成一種循環一種延續和連結。 生命中最強固的連結正是食物。 我喜歡作者提到想要再次嘗嘗當年(25年前)他媽媽為所做的草莓冰淇淋,那是當時經過百般撒嬌後才求得媽媽同意調配的冰淇淋,於是作者拿起媽媽食譜照著作,做法簡單有趣,過程好像訴說一段歷史,完成之後齒間冰涼留香,記憶與母愛交融成甜美的味道。 一篇篇食譜打開了一連串過往回憶,看到了不同旅途所留下的痕跡,還有一些人和一些風景,這一切緣自於母親那本破舊不堪的一本本食譜內。當讀者看到作者從媽媽的食譜學到的第一道菜「扁豆什錦砂鍋」的那段,不動容幾稀吧,或許\也該衝到廚房跟著作者媽媽的食譜做這道「扁豆什錦砂鍋」。 本書也是典型的失落-尋找-救贖的西方小說原型,失落的作者的母親與缺乏母愛的少年,尋找的中介是媽媽的食譜和味道,救贖的是又是什麼呢?是瞭解是體諒是超越。 作者除了一邊讀光明面的食譜以外,也試圖去挖掘過世媽媽的黑暗過去,一點都不擔心這會讓自己掉進危險深淵裡,媽媽生前的黑暗面-一連串的病歷紀錄,酗酒、憂鬱症。從病歷中去諒解並重新瞭解自己的母親,最後還是靠食物讓自己做最後的超脫。 吃飯是生命的起源,不是死亡亡靈的祭典,當作者做出一頓超越媽媽食譜以外的飯,有檸檬冰沙、白蘭地奶油蒸水果布丁、姐姐帶來的肉餡餅、岳母的烤薑餅人、….一頓媽媽生前從來沒作過的飯,他相信他媽媽會同意自己如此作菜,於是他得到救贖了,從親人亡故的心靈泥沼中脫離出來了。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半個人回憶錄,由媽媽的食譜和作菜的過程去講出一些不太愉快的故事,藉由食物去串連「失落-尋找-救贖」過程,字裡行間透過食材、親人對話與過往回顧而呈現一齣一點都不傷感的小悲劇,這種小品真的很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