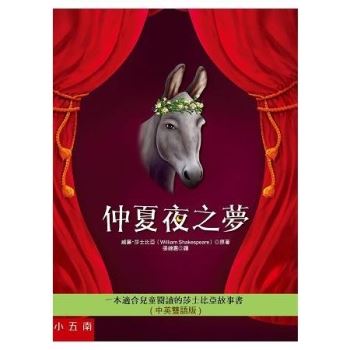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故事書:福地福人居》
地號:大溝
故事可以從父親精心布置在田中央的打擊練習區講起,故事也可以文旦白柚的摘收講起,故事破口開題的方式太多種,出路大溝的腳路卻僅只唯一──大溝至今仍是最常到訪的田地,它就坐落產業道路一邊,太便利了,路邊有電桿亦有水表,有路有電又有水,簡直就是最佳疏散地帶避難之地,未來想要住下來其實也可以。
大溝亦是面目變化最為劇烈的田地之一,如今它是植滿歸年透冬皆能結果的拔樂田地,連帶前後左右地主紛紛吹起芭樂風,站在鳥舍頂處眼前盡是一面白茫茫芭樂海,白茫茫是指它的果袋,母親下班無事騎車前來看田,隨意給它包個兩三粒,自食買賣送人都可以。
大溝亦有一座鳥舍,鳥舍下方空間當作倉庫,從老家撤出的家具電器都原封不動移到這裡,連擺設方式都完全相同,像是複製貼上的小客廳,不知是否太多悶濕的緣故,或者眼前畫面太像我的小時候:一樣的皮革沙發,一樣的茶几組和,一樣的日曆掛鐘。我好像沒進來幾次,待一下就想走了。
大溝雖在路邊,其實田身甚為隱密,不如現在完全露出,主要是兩分大小的園區都是文旦白柚,比芭樂高也比芭樂密集。暑假結束之前,我們時常被動員來幫忙摘採,那時家裡沒有貨車,都是二爺的鐵牛幫忙;同樣沒有貨庫,一車車黃綠色文旦白柚,皆被送至當時尚未獻給媽祖廟地的三合院囤放。這裡想來也像臨時店面,不少販仔都被祖母親自領路徒步至此精挑細選。其實文旦白柚時常囤到逼近梁柱高度,直至白露仍有半間貨量沒賣出去,古厝因而鎮日空間充斥迎面撲鼻天然果香,像在暗示這棟百年建築仍能呼吸,它還可以。
我們的大溝鄰田就是伯公的田地,從前來到大溝總會忍不住比較一番,因著種得作物大同小異,伯公那邊的文旦白柚園區卻是特別整齊,實則不只大溝,西仔尾、港仔、烏來田仔都是一分為二,平常談論都會問後起了彼此的作物,推薦肥料使用,談話間不經意提到了柚子花開,無形之中都再在互照應,不是真正分得那麼清。
比如一起共用一座水池。水池就在大溝田地入口處,現在仍有一些遺跡,圓狀的水池上面覆蓋一張圓狀的遮光黑網,我不知道它的真正用處,只知道從小我就被警告水深勿近,水池一邊有座簡易寮仔,那種四根梁柱一面歪斜屋簷的建物,西北雨來時可以躲避三個人。曾經我和年紀大我十歲的堂哥們,一起蹲在地上挖小溝引池水當遊戲,那是唯一一次,協力製作一座方才出土的微型市鎮,像在一分為二的地表另闢蹊徑,滿手泥濘的打造共享的家園。
大我十歲的堂哥們後來都在城市成人,之後每次獨自回到大溝,走到簷面傾斜的寮舍,等候田裡忙著不知天地的祖母,我就會蹲在地上努力辨認當年軟土深掘的痕跡,當時我不知道水深勿近的故事還有續曲。
我們也共同豢養兩隻公的毛孩。一隻叫做黃仔。一隻叫做黑仔。我家站的樓厝也與伯公比鄰,平常固定餵養祂們的是姆婆,兩戶人家卻在祂們看護範圍,為何在祂們眼中我們是一起的呢?記得兩隻毛孩也會跟著伯公上田,多遠都會跟出去。有時回程路途太長,伯公怕毛孩跑到腿軟,下車乾脆抱上鐵牛坐車回家,毛孩也乖乖坐了。有幅畫面至今仍在鄉里流傳──一臺載著老翁公婆噗噗行走的產業道路,車前車後跟著沿路狂吠的毛孩,像在喝斥路邊各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
我想起小學時期時常一人放學顧家,只要知道下午伯公與祖母分別要去的都是同座田地,機率最高的就是大溝,稍後我也會自行單車騎著前去會合,那時我擁有一臺黑色越野腳踏車,車至大溝路邊,從密密麻麻文旦白柚園衝出迎接我的就是滿身土漬的黃仔黑仔。
我為什麼堅持要來呢?車子停在水池一處,嘗試喊聲向祖母報備,同時聽到祖母來自田園深處的應答,於是縱身躍入林中尋找不知身在何處的她。兩隻毛孩並不與我同行,三方帶開在偏鄉午後並無人聲的祕境找事,常常繞了半天毛孩與我最後又在某棵樹前碰頭,彷彿還對視笑了一下,隨後又疏散進行自己發明的大地遊戲──這才是我真正認識大溝的契機。
不知為何記憶中果園內的我始終都在拔腿狂奔,兩分大小的田地格局十分方正,清晰可辨的田中小徑就只一條,田頭田尾來回跑一分鐘不到。站在自己的土地我是如此驚心膽跳,你是在怕什麼呢?怕蛇、怕跑步出這片文旦白柚森林.怕失去方向感於是走到了別人家的地──向來你總是要求公私分明。因著我的身形矮小,身手矯健,跑得特快於是沿途柚花被我打落,我也怕那位置就處在田邊的一門大墳。墳為果樹環環圍起,在並不十分偷光的園內,我的眼角不管走到哪裡都能瞥見局部的墳身,離得越遠墳的形貌越清晰越立體。
林中野放中的我,總在某棵樹腳遇到正歇息的祖母,記憶中的她總是處於休息狀態,如今回想才知根本是做不動了。她從帆布袋內取出礦泉水瓶,成箱的礦泉水瓶向來都是二爺友情贊助。為什麼我也堅持要找到祖母呢?我不僅無法幫上任何的忙,我也不曾明白到底鎮日她在做什麼。祖孫兩人相對無言,於是我以祖母得以聽見的範圍為半徑,在大溝田裡鬼祟摸走。我的膽子遠不如兩隻毛孩,祂們四處挖坑翻土野到不見人影,我只敢在一定的安全範圍內看看──
於是看見舉行在週末假日的控窯活動,人數奇少,就是母親與我,以及母親一位同樣嫁在附近的小學同窗,再加上她念外地學校的孩子。孩子剛剛轉學回大大內,以致在鄉里沒有朋友,知曉此事的我恍惚以為這是聯誼活動,因此過程並不十分自在。我幾乎沒有和他說話,中途帶他至父親搭設的打擊區。我們手邊沒有鋁棒亦無壘球,地上的枯柴與NG的文旦就是鋁棒壘球。民國八十五六年的曾文溪邊,兩對母子在遮遮掩掩文旦園內生著火,地上鋪滿許多從家中回收的《民眾日報》,擺著外地早市買的生鮮食品。話題都是這位老同窗帶出來的,她年輕在國外住過好一陣子,後來在高雄開過小店,現在嫁到鄉村當起家管,言談中得以察覺她的適與不適。除了烤肉,同時我們想控一隻雞,心中卻有許多擔心,窯已經挖好,擔心洞不深雞不熟;好不容易為鋁箔包裹的土雞安全降落,又擔心雞吃不完帶回家會冷掉。最後四人像是擔心被發現什麼,努力埋得地表離奇光整,看不出地下有雞在悶,邊笑邊說最後忘記埋在哪裡,撿了幾片枯葉意思一下做個記號。這洞前身分明黑仔黃仔傑作,而我彷彿就看見黑仔黃仔正在向我搖尾,祂們是否不懷好意就想就把深埋的土雞挖出來呢。
我也看見一場水。水從四方流向田中也從田中流向四周。僅有一次園區舉行大放水,我們都被通知前來看顧。粗如小孩大退的黑色水帶,平時曲曲折折散落田的各處,乍看像是廢棄物,其實作用可大了。當時我常以水帶為線索在林內走臺步,試著尋找水帶的所來與所去,其中一節水帶是否就會帶我通向那座大墳呢?這些水帶或者日曬龜裂,或者堵塞不通。為了這次放水祖母提前幾日前來場布。為什麼水管不用沒有妥善收拾?答案相當簡單,祖母一人做不過來,除了水帶,田裡也能看見隨地擱置的農具:隱沒在柴堆中的鋤頭、誘引蜂叮設置的各種陷阱,不能用的可以用的通通堆疊在一起。記得放水那天我的工作是負責巡視水帶接頭是否脫落,有時順手移動水帶位置,讓水流皆能適切通往各株文旦白柚。一時之間我們的果園換上濾鏡一般成了水田,水深大約來到我的腳踝,所有的落葉都漂浮了起來,所有的落葉都黏在我的腿肚。那天想必伯公也在隔壁工作,所以黃仔黑仔都來了,但凡水帶爆開之處往往形成微型水柱,於是我就能聽到黑仔黃仔叫得格外興奮,祂們像是田中送水系統的某種警報裝置,通知在不同樹下的誰趕緊前來處理,這人通常也是我,只因這是我們之間的獨有語言。放水故事唯此一回。不敢問以前有沒有,以後確定是沒有。我們全家大小在水中潦來潦去,真正才像是走進了大溝,記憶中可不曾如此親密。
大溝的名稱也是我們自己私擬的,只因附近真正有條水溝,怪的是它是長在地面的排水設施,也就是人車得以行走其中,排水溝都是灰白色的,因為罕為人至所以看不出年代遠近。我曾偶然騎過一次,坑坑巴巴的地面水路,始終給我一種錯覺,像是走在乾掉且劣質的修正液表層。後來我才知道許多平日在走的鄉間產業道路,其實前身都是大條水溝,溝渠只是覆蓋在柏油路下,也就聽不見什麼淙淙流水音效。八八水災那年,曾文水庫洩洪,加上連日超大豪雨,曾文溪潰堤導致溪邊聚落遭逢水難,距離河床地有段距離的大溝,竟也整片園區泡在水裡──所有植栽全死半死,那時大溝早已進入拋荒階段,祖母不再插手農事,但她每年某日依然備妥祭品大溝田頭祭祀,進行著從小到大最讓我不解的儀式:地上鋪著同樣從家裡帶來的《民眾日報》,擺上印象中就是孔雀餅乾四果香燭,謝天謝地地拜了起來──
實則仍在耕作收成中的田地都有一款屬於祖母的大地祭祀遊戲。通常就是選擇田地附近的萬善堂、有應公廟為對象,每年應公貝仔誕辰,我們就得不停趕攤:西仔尾的小廟仔、下州尾的小廟仔,我都有跟過,想來真是不可思議。八八水災間接導致父親重新接手大溝田地,將文旦白柚換成了每季都能收成的珍珠芭樂。大溝進入了它的芭樂時期。這才讓我想到來到大溝祭祀的工作已經自動暫停,而田頭舊址消失入口易位,寮仔與水池皆不復見,黑仔黃仔同樣不見蹤影。
因此故事不妨便從田頭這方水池講起。聽說那日伯公又來到大溝,黑仔黃仔也跟來了,我想像祂們四處挖土,玩得全身土漬;同樣又與鄰近毛孩咬成一團。如果我在田地,定能聽到祂們嬉鬧,以此判斷祂們遠近。伯公一做就是整個下午,加上他的耳朵不太靈光,身在田中的他看起來最專注最投入。他正努力檢查文旦樹的蛀蟲,留意柚花的生姿,也就不會知道毛孩到底去了哪裡。那日傍晚收工回家,伯公對著四方天地發出訊號,通知東南西北方的兩位毛孩收心歸隊,卻遲遲不見祂們應答。這時隱隱約約聽到田頭傳來急切吠聲,於是來到池邊看到黃仔在簡易寮仔原地打轉不止。我想像黃仔已經轉了一個下午,四肢早已略顯無力。伯公凝神一愣,才注意少了一隻。這時一個眼角掃到,本有遮光網隔著的池面早已破了大洞,遮光網真正目是用來防止池水氧化,自自然然就形成了一面黑顏色。誰知竟會讓黑仔因此失足踩空呢。伯公說黑仔半邊身軀泡在其實不深的水裡,半邊身軀捲在遮光黑網,讓人不敢看也看不清。我不知道伯公後來如何將黑仔打撈上來,也不知道後來黑仔是否就地埋葬大溝,他甚至沒有告訴大家一隻毛孩沒了,獨自守著這個祕密直至我們問起。黑仔勢必有過掙扎,祂是渴了想要喝水嗎?黃仔定也努力咆哮,伯公重聽因而沒有聽見,黃仔又是如何睜眼看著黑仔逐漸流失最後一股力氣呢。
黃仔是在民國八十二三年來偎在我家的,當時父親在鄉里組織一支慢速壘球隊伍,因而自購了許多壘包,賽事結束攜帶回家,於是層層堆在騎樓於是成了冬日浪浪最好的睡臥……
黑仔也是在黃仔之後抵達我家。其實本來有人飼養,偶然經過就停下來了,她的主人曾經趨車將她接回,記得我還躲在門邊偷偷看著,未料祂又執意脫身而出,也就這樣住下來了……
多少年後大溝視野終於大開,我也漸漸醒了過來。不見邊際珍珠芭樂樹海來到你的眼前,眼前的畫面早已不是容易迷失其中的文旦園白柚園。歡迎來到二十一世紀。無名大墳被撿骨,原地種起經年結果開花的樹。黃仔黑仔已經不在。
大溝是我家少數仍在耕作的老田地。近來冬季不知緣故,總會定時生出名之為黑甜仔的野菜,我們都稱呼它黑點點菜,因為聽起來比較可愛。這些野菜是祖母生前最愛,也是許多家庭熱門的家常菜色,如今地衣一般從田頭爬到田尾,春節初二於是全家帶隊前來摘菜,由於面積實在驚人,還相約邀請鄰居前來團摘。
暖冬午後得以在田享受摘採野菜的農家樂,不知為何我有一股想哭的衝動,上田不曾如此有趣,真正比放水的記憶親暱。我們家的生活確實改善許多。上一輩、上上一輩是完全苦過。我漸漸得以靜定看待這些田那些田的故事,而眼前正是大溝的現在式。我們同時想到祖母。祖母一輩在過去十年內相繼離開人世。人不在了結果田還在,我知道未來我會不在田地卻會在;鳥舍絕對不可以在,遠方丘陵則將一定在。
大溝的黃昏,近來天上出現私人滑翔翼飛行物。我喜歡站在芭樂樹邊與黑點點菜為伍,彷彿就讓自己成為空拍航行畫面中的一枚小點。飛行物嗡嗡作響,廟口廣播同時不停信號來回撞擊山壁。這時我聽見田頭出現車聲人聲孩笑聲。我要趕緊找棵矮樹躲起來,看看這麼晚是誰來了。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
文體:三合院創作課
不知道是第幾次重讀庄司總一的《陳夫人》,這部流行於臺灣四十年代的長篇,文本細節十分豐富,我覺得它在當代臺灣小說書寫隊伍,仍有許多部份值得梳理。過去我的讀法比較側重在故事主角的身份歸屬,譬若從東京歸返的認同問題,日臺兩造的通婚關係。再進一點的讀法,則是開始留意文本敘事的地景描述,空間理論讓我們看到戰爭時期殖民地臺南的日常與異常,小說人物的情貌更加被凸顯,在歷經諸多文化論的論辯之後,能關注小說技術與角色性格的折衝關係,就像是從空拍畫面來到了聚焦特寫,我們從而看到關於陳夫人一家族的身形神色、肌理紋路。
不同的讀法帶來不同的視野,幸運的是,重新回到文本描述終將是一必然的走向,而這也帶領我們不僅走進陳夫人的故事結構與心境內層,也走進支撐這個故事結構的關鍵場景──陳家三合院。我們太需要重視小說的建築、場景、布幕,乃至襯底的天色、雲朵與陽光了。
不知道你生命中的第一間三合院在哪呢?前陣子在高中進行講座,突發奇想在黑板畫了一個大字,也就是注音符號的ㄇ,我拋出問題也同時反問自己:三合院這個空間可以進行哪些活動?接著不斷傳來各年齡的神回覆,最常聽到的答案是曬稻與遊戲,大抵這也是我們想像此一空間的幾個動作。三合院本身就是一個框架,歡迎各路敘事來此陳列上架。我的舉例比如停車、曬衣、宴客與夯罵──烤肉啦。說出這些選項大家都笑了出來,好像我們都曾住過同座三合屋院。只是寫作它跟三合院什麼關係呢?
我生命中的第一間三合院是位在朝天宮後方的古厝,現址已經不存了,這也是我的第一個ㄇ,祖父因是最小的兒子,我們的三間厝身便在象徵輩分最低的位置,右邊護龍的最外頭。奇怪的是我們從來不稱呼它作三合院,就是直直喊他古厝,顯然古厝也是曾經年輕過的。我們在民國六十幾年左右,搬到現址的樓仔厝,古厝為此是一個被對照而出的說法。
當我來到古厝,各家護龍的閒置空間已經拿來當成倉庫,我家的那三間房,第一間會在秋天拿來囤積文旦和白柚,整個屋身因而吸納著一股飽滿的果香,在那本身光線不佳而潮濕悶熱的環境,賣不完的白柚漸漸變黃變軟,直至靠傷最後只好自己回收。古厝還有接電嗎?寫到這邊才猛然想起是有的。半空懸掛的日光燈,從上而下垂垂落下一條線路,橄欖形狀的開關,要輕推一下才放亮。所以也就沒有斷過電,像是可以回來居住或者出租他人。第二間是個飯廳,爐灶卻在外頭,這裡擺放許多從樓仔厝撤出的回收,許多看起來根本沒有用過的家電,我的小學課本也在這裡。印象最深刻是牆上有張寫滿祖先忌日的紙張,大老祖公、大老祖媽、老祖公、老祖媽……字跡是祖母的,我小時候也曾幫我祖母謄抄過新的一張,且是寫在粉紅色的紙上,然後貼在大家都會看到的客廳牆上,像是這個家族的獨有曆法,每次經過都看它一眼。第三間則是祖母臥房,有一扇門得以通開向隔壁緊鄰的伯公家,據說這在風水角度而言並非良好設計,祖母於是找來厚重衣櫥將門封死,像是得以將煞氣隔絕在外。說是臥房根本沒有實體床組,記憶中就是一個通鋪。古厝因廟拓建要拆那年,我陪著祖母回來清理打掃。數十年前未及搬到樓仔厝的老家具,一留就是二十多年,還有那從未整理的信件,寫在其中的情感課題,也都二十年過去了。我忍不住看了幾封,然後又默默將它放了回去。我就與祖母身在空氣並不流通的古厝,在蜘蛛拉網而膚癢難耐的環境,逐一聽取這是什麼那是什麼,然後長出更多的為什麼。
古厝大概適合拿來當成鬼故事的場景吧!而我確實也非常害怕單獨前來,最常被指派的任務,是來搬運一整組的扁擔與謝籃,通常這是廟口拜拜的時機。古厝使用的是傳統門鎖,兩片門板上有神荼鬱壘對看,兩個環扣就是我要試著上鎖的對象,最後再將鑰匙藏在門邊的暗溝。這些步驟看似簡單,每次我都弄得心神不寧,在外人眼中看來是不是很像小偷呢,畢竟我與古厝並沒有太多切身的連結。我沒有住過這裡。
大概從小我就問過這個問題,在穿越厝身的三個房間之後,每次我都會說:你們洗身軀的地方呢?也就是浴室在哪裡,以及與浴室關聯的拉撒之地,怎麼沒有看到廁所。這個提問顯然大家也都有想過,包括在庄司總一的故事,來自日本的安子初入陳家三合院,迎面而來的疑惑與挑戰,除了是自己的日本出身,最切身的就是平常起居了,而這又落實在小說關於三合院的空間描寫,你看切身兩字多麼精準,大概就是沐浴與泡澡一類的事。安子入住的陳家三合院並無浴室設備,跟許多臺灣的三合院相像,廁所獨立蓋在荒郊野外,丈夫清文只好倉促為她架好了屏風,在臥室以擦澡取代泡澡,以木桶當成馬桶。
而這個漸漸適應的過程,恰恰就是小說中安子的這句:「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不過我已有心理準備盡量和家裡的每一個人親密地和睦相處。」──「親密地和睦相處」我想大概就這部小說的金句,而其成立的基礎就是夫婿陳清文家的三合院。然而縱使安子有其覺悟,接受新式教育的清文,仍然堅持要在三合院外接一間二層樓西式洋房,小說場景當下成了傳統與現代並存的模板:
在陳家本來凹字型的建築物中,由其一方接翼處增建了二層樓的洋房。特別為安子設計了一間八席榻榻米大的和室。油漆的檳榔木地板和樟木兩種不同的架板,使和室別具一種異國風味。當然也有廁所,有附帶蓮蓬頭貼磁磚的浴室。還有西洋式的客廳和書房,有藤木植物棚架的陽臺,有可以仰望南國星星的屋頂上庭園等等。
這洋樓十分奢華,然而二樓的高度,已經凌駕作為精神核心的神明廳,清文甚至可以從他的住家二樓俯瞰廳堂的屋頂,這真是太超過了。長幼之間完全失了秩序,洋樓拔高而起,這個清文個性硬。如此以來「親密的和睦相處」從平行相看的視線,變成高低不夠對等,小說敘事軸自然跟著東西南北移動了,故事人物就在建物之中上下穿越奔走,試想這樣的大動作演出,在現實生活中,怎麼可能不生家族枝節?近年來閱讀臺灣小說,特別注意場景人物,好的場景給出好的境界,它不只是一個布景,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生活的環境切面,具備了神話的品質;好的人物有他的語言風格與不凡視野,人物與場景都到位了,這小說怎麼可能不讓人印象深刻?有趣的是,三合院在庄司總一的筆下被形容成是個凹,我卻把它說成了ㄇ。ㄇ與凹的差別應該就在觀看的位置吧:ㄇ的視線是從外而內,凹則是從神明廳向外探,或者兩種相反。我自己的視線是習慣與神明廳對看的,這是一個回返的視角;而庄司總一以凹型做為比喻,它的角度反而位像在家後,這跟過往論及日語作家因其殖民身份屬性,而帶來的觀看與被觀看的說法又多了些層次。而當我們要述說一個背景發生於三合院的大家族故事,庄司的視線不只從帝都到島都,從日本到臺灣,從內地到外地,也有了更多周旋的空間。而這些問題之於當時臺人日人,之於我那古厝的大小祖先們,自然也是相當切身的。
所以你生命中的第一間三合院是在哪呢?在你而言是ㄇ還是凹?你又在三合院進行什麼有趣的活動?三合院除了起居,埕斗的存在也是值得細細品頭,這是一個私人空間卻又十分開放,我們在此曬稻遊戲,我們也在此曬內衣褲、停名貴車與中秋烤肉。每種行為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我以為三合院的空間敘事練習,實在適合拿來當成創作課,人物、場景都到齊了,接下來就看你怎樣編織故事了。而如果真要讓你挑選一個位置,你是會站在神明廳之中,或者如同清文從二樓俯瞰從小長大的古厝?或是選在棗紅色的厝尾頂呢?你擁有的場景將是無限延伸的,一進又一進的院落?還是只有腳下站立的一點方寸,光線想是帶著斜日映照,人物身影則是細細長長。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故事書/楊富閔(果盒限定)套書(福地福人居+三合院靈光乍現)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05 |
散文 |
$ 506 |
文學作品 |
$ 563 |
現代散文 |
$ 576 |
現代散文 |
$ 576 |
超值套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故事書/楊富閔(果盒限定)套書(福地福人居+三合院靈光乍現)
強檔賀歲國片《花甲大人轉男孩》原著作者楊富閔2018最新概念創作。
《故事書》以地號書寫和人物群像連鎖鄉村少年的日常生活,
體例特殊,層次井然,呈現活跳跳的庶民文化。
全書故事接地氣而富有生命力,一篇一篇引領你我光臨臺灣文學的二十一世紀。
★國民作家楊富閔在《故事書》中提問,置身當代新媒體的虛擬語境中,一個「寫作者」如何定錨文字的功用、文學的角色?一個「有土地的人」怎樣才能重新腳踏「實」地?
二十一世紀的文學還可以是什麼──「故事書」熱切邀請讀者進入楊富閔的文學鄉村,一起行動,一起再狂想。
★《故事書》果盒套書有酪梨、芒果兩款,隨機出貨。
名家推薦
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白先勇(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榮退教授,小說家)
陳 列(散文家)
蔡妃喬(結果娛樂營運長)
瞿友寧(《花甲男孩》電視與電影導演)
王德威:「楊富閔是當代臺灣新鄉土寫作的代表人。《故事書》寫故鄉的人,故鄉的事,點點滴滴,實實在在,無不有情。《故事書》也是一個臺灣囝仔追尋文學的真誠告白。從臺南大内到臺中臺北、美西美東,遙遠的路,熾熱的心——《故事書》就是南臺灣版《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
千禧年的第一場葬禮多麼福氣,於我性命而言亦是全新的世紀。〈地號:花窯頂〉
深冬午後我們披麻戴孝站在花窯頂,幾乎以為視野如果可以夠好,便得以看到曾文溪畔的菅芒草原。千禧年後我就開始走在送葬行伍同時也走在離鄉道途。新墳剛到據說花窯頂立刻枯死兩株酪梨樹。許多事物都從根本開始產生體質變化,我也漸漸發育成人。〈地號:花窯頂〉
我看到月臺對岸有一對老夫妻大包小包,後來還跟著兩個小的,小的衝得很快,老夫妻卻走三步停兩步,絕對是累了,我突然有跳下火車的衝動,此時鈴聲大作,列車要準備落南了。〈農暇:落南〉
《故事書》是國民作家楊富閔繼《花甲男孩》、《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以來,再度探討鄉村與家庭,媒體和書寫,自我及世界的全新作品集。兩書得以合而觀之,亦可視作獨立作品,體例特殊,層次井然。
《故事書》亦是楊富閔對於創作的自我定錨,篇篇都是生命的註解。全書系一方面嘗試以「地號系列」貫穿兩書;另一方面,號召「大內楊先生十二位」等人物圖像為索引。整合、延伸而出對於山川草木、市鎮興衰、當代人文,乃至於新世紀的複雜思考。
《故事書》打破習慣的分輯或者編年手法,讓人事物走出一時一地的制式藩籬,讓文字符號於其自身脈絡舒展流變,讓敘述自行串聯與修復,讓是非因果隨聚隨散,渡入世情的曖昧地帶,讓聽故事和說故事的人彼此接駁、相互應答──全書無不流露楊富閔致力於發出語言新枝、形式新葉的實驗精神。
全書系其一:《故事書:福地福人居》從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葬禮說起,曾祖母在世紀交替之際歸葬福地花窯頂,這場葬禮多麼福氣,也開啟了楊富閔的新世紀、新生命。全書行文風格極具辨識,無不瀰漫楊式講古的特殊「饋口」。
〈收成:青菓市的故事〉栩栩重現青菓市的氣味、聲音、影像,紙箱上的「大內柳丁」、「關廟鳳梨」、「玉井芒果」,是一鄉鎮一物產的水果地理課;〈邊界:一個人的試膽大會〉寫曾祖母入殮那日,執事的土公仔從腳尾飯中拈出熟鴨蛋,阿嬤要給作者食來做膽,讓他面對神明廳的幢幢暗影攏免驚。〈上下文:二十一世紀的動態時報〉以短篇連綴形式,布置嶄新時空架構,緩緩道來南國少年的地上歲月。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狀寫南臺灣鄉村的地勢水文,莊稼農暇,個人與果物的世代交替,紀實中有抒情,風景裡見百態。全書布滿出入故事的閘口,處處暗藏隱喻:百葉箱的天啟、榕樹下的俗諺課、窯口的餘燼,無主有主的墳塋,敘事一路爬高落低,終於到達生命紀念園區。讀來盡是作者獨特的敘事風采與語言魅力。
編輯熱情推薦:〈花窯頂〉、〈落南〉、〈河床本事〉、〈歲次庚午的鬧熱〉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
我們世居的百年古厝如今正是媽祖廟的大殿,我們的三合院後來成了媽祖地。我們曾經住在媽祖隔壁。〈文體:古厝埕斗的同框敘事〉
實則古厝空間充滿各種活用可能,這是一個適合練習講故事與聽故事的好地方,理想的故事會找到理想的文字,說者聽者在其中取捨、狂想與捏拿,說與聽合而為一,我會繼續摸索、慢慢建立、朝向一些關於文體或者什麼的作品。〈文體:古厝埕斗的同框敘事〉
生命中一場一場的雷陣大雨,總是困我於曾文溪中游山區聚落,我的生命內建了一個關於地形的隱喻,苦雨追趕已是生活的常態:在麻善大橋、在縱貫公路、在四周盡是甘蔗平原的故鄉臺南,在看得見善化糖廠巨大煙囪的溪尾路段,我的身後身前,總有山勢一般湧動的烏雲跟蹤……〈說明:暴雨將至〉
《故事書》是國民作家楊富閔繼《花甲男孩》、《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以來,再度探討鄉村與家庭,媒體和書寫,自我及世界的全新作品集。兩書得以合而觀之,亦可視作獨立作品,體例特殊,層次井然。
《故事書》亦是楊富閔對於創作的自我定錨,篇篇都是生命的註解。全書系一方面嘗試以「地號系列」貫穿兩書;另一方面,號召「大內楊先生十二位」等人物圖像為索引。整合、延伸而出對於山川草木、市鎮興衰、當代人文,乃至於新世紀的複雜思考。
《故事書》打破習慣的分輯或者編年手法,讓人事物走出一時一地的制式藩籬,讓文字符號於其自身脈絡舒展流變,讓敘述自行串聯與修復,讓是非因果隨聚隨散,渡入世情的曖昧地帶,讓聽故事和說故事的人彼此接駁、相互應答──全書無處不流露楊富閔致力於發出語言新枝、形式新葉的實驗精神。
全書系其一:《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以〈九層塔得勝頭回〉破題,經由人與樹的日暮對話,布置了一個欲晚山村的故事背景,在柚皮蚊香氤氳之中,引領人物、讀者同步進入楊富閔的講古現場:「到處都在放光,照出一處處的舞臺,連月光也在替我打上斯巴賴。」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一方面狀寫個人與家族的切身記憶:〈儀式:惦惦仔吃〉;出出入入臺灣文史敘述:〈愛文:從小寫起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寫臺南山海的氣候、信仰及其變與不變:〈地號:大西仔尾〉;以及媒介、記憶與人情之間的萬千葛藤:〈有圖:我們之間〉。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呈現重新理解、詮釋傳統家屋的時空感知,乃至生活與倫理的獨特美學。既是一本過現未「同框」之書:混搭拼裝中長出井然的紋理,斷牆頹垣中隱約可見恍若有光的神思;《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更是一帖邀請函,邀請你我身歷其境古厝埕斗的百年故事。同時也是作者對於當前此刻的一次凝神,自我許諾一場朝向未來的文學行動。
編輯熱情推薦:〈上下文:鄉村符號生產器〉、〈鬧廳:超高清失散隊伍〉、〈行動中:破布子念珠大賽(搞剛的書寫)〉、〈開地球:自我的索引〉
作者簡介:
楊富閔
一九八七年生,臺南人,臺大臺文所碩士班畢業,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目前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臺灣文學、文學寫作與教育。
曾獲「二○一○博客來年度新秀作家」、「二○一三臺灣文學年鑑焦點人物」;入圍二○一一、二○一四年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部分作品譯有英、日、法文版本。
專欄經歷:《中國時報》「三少四壯」、《自由時報》「鬥鬧熱」、《聯合報》「節拍器」、《印刻文學生活誌》「好野人誌」、《幼獅少年》「播音中」、《皇冠》「貴寶地」。
創作出版:《花甲男孩》、《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共二冊)、《休書:我的臺南戶外寫作生活》、《書店本事:在你心中的那些書店》。編有《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與梅家玲、鍾秩維合編)。
文字作品曾獲改編電視、電影、漫畫、歌劇。
喜歡臺語歌、舊報紙、鐵支路、國道三號、酪梨牛奶、以及媽媽。持續努力寫成一個老作家!
TOP
章節試閱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
地號:大溝
故事可以從父親精心布置在田中央的打擊練習區講起,故事也可以文旦白柚的摘收講起,故事破口開題的方式太多種,出路大溝的腳路卻僅只唯一──大溝至今仍是最常到訪的田地,它就坐落產業道路一邊,太便利了,路邊有電桿亦有水表,有路有電又有水,簡直就是最佳疏散地帶避難之地,未來想要住下來其實也可以。
大溝亦是面目變化最為劇烈的田地之一,如今它是植滿歸年透冬皆能結果的拔樂田地,連帶前後左右地主紛紛吹起芭樂風,站在鳥舍頂處眼前盡是一面白茫茫芭樂海,白茫茫是指它的果袋,母親下班無事...
地號:大溝
故事可以從父親精心布置在田中央的打擊練習區講起,故事也可以文旦白柚的摘收講起,故事破口開題的方式太多種,出路大溝的腳路卻僅只唯一──大溝至今仍是最常到訪的田地,它就坐落產業道路一邊,太便利了,路邊有電桿亦有水表,有路有電又有水,簡直就是最佳疏散地帶避難之地,未來想要住下來其實也可以。
大溝亦是面目變化最為劇烈的田地之一,如今它是植滿歸年透冬皆能結果的拔樂田地,連帶前後左右地主紛紛吹起芭樂風,站在鳥舍頂處眼前盡是一面白茫茫芭樂海,白茫茫是指它的果袋,母親下班無事...
»看全部
TOP
目錄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
新人:大內楊先生十二位
聽故事的人
GrandMa
小家庭
曾祖母
小祖先單行本
姑婆群組
打赤膊的人
通報水情的小男孩
落落大方的人
遠親
拍噗仔:百葉箱得勝頭回
地號:天公地/逆天的人
地號:花窯頂
文體:等高線創作課
地號:大溝
收成:青菓市的故事
農暇:落南
節拍:心地的走讀
元宵
清明
星期六讀半天
禮拜天的打卡鐘
戶外教學日
班級返校日
黃金店面
電腦課
灶
排路隊
交錯:行軍部隊來了
送迎:歡退儀隊來了
交錯:賣醬菜的來了
有片:歲...
新人:大內楊先生十二位
聽故事的人
GrandMa
小家庭
曾祖母
小祖先單行本
姑婆群組
打赤膊的人
通報水情的小男孩
落落大方的人
遠親
拍噗仔:百葉箱得勝頭回
地號:天公地/逆天的人
地號:花窯頂
文體:等高線創作課
地號:大溝
收成:青菓市的故事
農暇:落南
節拍:心地的走讀
元宵
清明
星期六讀半天
禮拜天的打卡鐘
戶外教學日
班級返校日
黃金店面
電腦課
灶
排路隊
交錯:行軍部隊來了
送迎:歡退儀隊來了
交錯:賣醬菜的來了
有片:歲...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楊富閔
- 出版社: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10-0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12頁 開數:25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食物與廚藝 1-3 (第2版/3冊合售)
就在這裡! 超理科校園解謎! 科學實驗中學 1-3套書 (附元素週期表雙面墊板/3冊合售)
海道.海盜三部曲套書: 海道: 紫氣東來+海東清夷+披星桴海 (3冊合售)
屠格涅夫經典文學套書: 羅亭+父與子 (2冊合售)
最高深度學習法: 開發大腦潛力, 快速提升學習質與量, 像愛因斯坦一樣學習, 成為超級知識海綿
下班後只想輕鬆煮200: 一鍋到底X省時3步驟, 22位人氣料理家的日常好食 (經典上菜版)
尋味香港套書: 台灣胃看香港餐桌+四季裡的港式湯水圖鑑 (2冊合售)
別再內耗, 及時覺醒找回安定幸福的暖萌套書: 及時覺醒+平靜寧和就在每一刻 (2冊合售)
BANANA FISH復刻版 6-10 (5冊合售)
阿德勒集大成之作: 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阿德勒的理解人性 (2冊合售)
就在這裡! 超理科校園解謎! 科學實驗中學 1-3套書 (附元素週期表雙面墊板/3冊合售)
海道.海盜三部曲套書: 海道: 紫氣東來+海東清夷+披星桴海 (3冊合售)
屠格涅夫經典文學套書: 羅亭+父與子 (2冊合售)
最高深度學習法: 開發大腦潛力, 快速提升學習質與量, 像愛因斯坦一樣學習, 成為超級知識海綿
下班後只想輕鬆煮200: 一鍋到底X省時3步驟, 22位人氣料理家的日常好食 (經典上菜版)
尋味香港套書: 台灣胃看香港餐桌+四季裡的港式湯水圖鑑 (2冊合售)
別再內耗, 及時覺醒找回安定幸福的暖萌套書: 及時覺醒+平靜寧和就在每一刻 (2冊合售)
BANANA FISH復刻版 6-10 (5冊合售)
阿德勒集大成之作: 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阿德勒的理解人性 (2冊合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