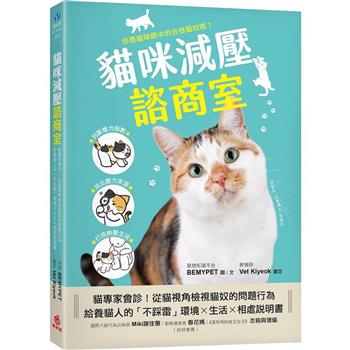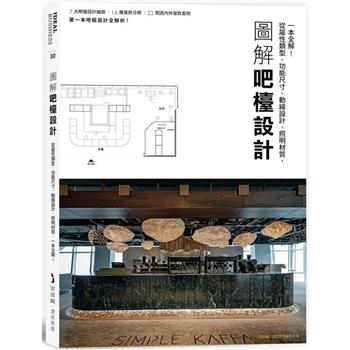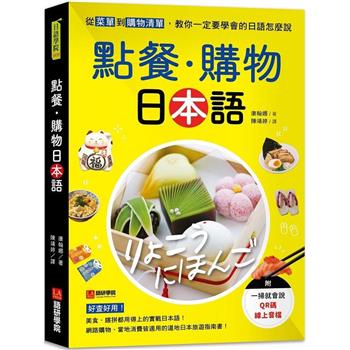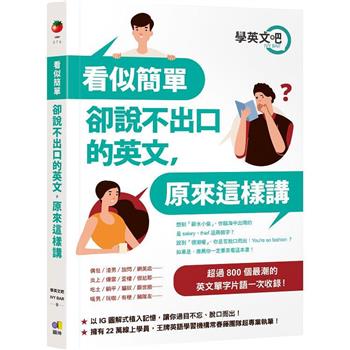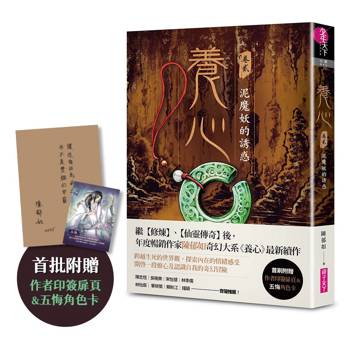再遠的地方,慢慢走都會到的(文字|陳盈臻)
那是我與山的開始
夏季的天光來得早,小時候每逢週日,阿公阿嬤會偕著全家人來到臺北圓山飯店後方的親山步道,隨階梯而上,兩側各有數座羽球場,孩子們會在這裡打羽球,大人們則用家常泡茶。坦白說,對於幼小的內心,要在假日趕赴陡傾的山林是帶有些許抗拒的,唯一吸引我的,是結束後大夥爭相向下衝至山腳的雜貨店,打開冰涼的透明櫃,選一瓶喜歡的飲料,好似作為今日慷慨赴約的獎勵。
我不能確定是不是從這時候開始懂得爬山是什麼,但它卻像個約定放在心底,其餘的記憶,都已模糊。
有伴侶後,「在各地生活」的想法像不斷滋長的原始渴望,推著我們移居紐西蘭,一處以原始自然環境為傲的國家。至此,如同受到啟蒙,開始追求、探索自然帶來的摒息與震撼,行至冰河的源頭、或穿越樹林抵達滿是氤氳的湖泊,也是從那時候意識到,想開啟不平常的風景,或許就從平常的走路開始。畢竟,再遠的地方,慢慢走都會到的。
在背負與卸載裡看見真正需要的東西
2018年,我們走上西班牙朝聖之路,從法國翻越庇里牛斯山來到西班牙的聖地牙哥,連續三十天、全長800公里,雙腳的疼痛感像是最直接的提醒,生存的延續與意義,那是頭曾經被豢養的幼獸,初次走出籠外看見的風景,自由且真實。
自徒步中甦醒。多年群居於社會的價值,讓我們在物質裡迷失,以為非得需要些什麼才能存活,於是,拼了命地將肩上的背包裝滿,深怕缺了、漏了,就會阻斷繼續前行的路途。但是,對於長時間異國旅行的我們,又怎麼會有額外的預算負擔這些嶄新的裝備呢?幸好,從朋友的倉庫拾來一只遺棄的背包;腳上的靴子不防水,就克難地用蠟燭塗鞋面;沒有登山杖,就在路上撿取一根合手的長枝。只是如此,我們仍然不安,盡可能地將背包裡塞進所有對路程恐懼的想像,直到真正走在路上,才一一地捨去。好像是從這時候認識到,什麼裝備才是真正能幫助我們更舒適的走在路上。「想要」與「需要」的界線,是來自於體驗後的理解,而非恐懼滋養的假想。
在這條路上,除了自己,還會與誰相遇呢?
2019年,喜馬拉雅山脈如巧合般地在生活中反覆召喚,我們飛行前往尼泊爾的聖母峰基地營健行,克服了高度適應中可能的不適,最終海拔來到5400公尺,是個人有限的生命經驗裡所能及最高之處。放眼群山,皚皚白雪深覆,冷冽的山風拂面中仰望了8000公尺巨峰的身形,長吁的呼吸裡藏著上揚的雙頰,「終於見面了!」當時心裡只是這麼想著。
喜馬拉雅山脈裡除了遇見登山者外,也住著雪巴人,從早期的游牧生活,到後期因登山文化興盛而生的高山嚮導、協作,成為了欲攀登聖母峰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力量,若是沒有這群生活在此的人們籌建基地營作為運補站,登山家遭遇的風險勢必倍增。也意識到山林裡不止登山者,還有憑藉山岳文化生活的人們,是如何協成一次次打破人類野外探險界限的攀登,讓我們有機會一窺極境的樣貌。
我們本是來自於山林,只是離家太久而遺忘
臺灣這一方小島,3000公尺以上的山脈竟多達268座,長年保護教育的政策下,島民始終缺少那麼一點點探索深山的勇氣,我們自然對於山林滿是陌生,直到幾次國外的朋友問起,才發覺,我不正是應該要好好認識自身土地的人嗎?於是,開始了臺灣這片土地的探索,郊山也好、百岳也罷,每每愈是深入其中,愈是驚嘆。
猶記得初次深入臺灣山林時,屬植物的多樣性最為之驚艷了,亞熱帶國家和立地拔起的高聳山脈,植物因氣溫下降而顯現不同的樣態,同時提供了不同生物棲息的最好空間。但也正因如此,臺灣的中級山系溼滑易雨,蚊蟲紛擾,若轉而向高山去,則因位處板塊地震好發帶,地形時而破碎、時而陡陗,多具有一定難度。但我們依舊被深深吸引。
甫回國那年,有一回,我們耐著對於氣候的不適,歷時半日,才抵達了藏在山中的松蘿湖畔營地,然而因水氣升起的白霧卻完整覆蓋了眼前的風景,匆匆搭帳煮食後只能靜靜入睡。翌日清晨,揭開帳前的幃幕,就望著眼前的風景怔怔出神,原本濃厚白霧開始如流動的雲朵迅速向山的一側蒸散,不出幾分鐘,如鏡的湖面映著天藍開闊,一陣麻脹感由背脊竄入腦門,「能夠看見這樣轉瞬即逝的風景,一定是備受山神呵護的吧?」心裡默念祝禱著。
臺灣山景幻化多變,晴時、雨時、風時、靜時,同樣的路線能有千百種姿態,即使全身泥濘,汗流浹背,都吸引著一群人義無反顧的前往。奇妙的是,山裡的時間感竟也與平地不同,學會將五感打開後,會開始慢了下來,同森林一起呼吸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植被色彩或鮮明或隱晦,地形或坡或緩,走進山裡的我們如織布機上的梭子來回於經緯的窄徑,一橫一豎地將自己的生命與山林共織,直至鼻息和脈搏的頻率相同。
人們是健忘的。忘了自己的氣味,忘了曾來自於大山,然而,山卻始終接納,也等待著被重新想起。例如,那個大汗淋漓的午後,坐在山間樹蔭下,陽光若有似無地穿透葉間在地面投射出像星子的光,那時的風和氣味,一直呼應著此時的呼吸與心跳。走進山林,再也不需要理由,就如同回家一樣。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把自己送回自然(1):成為走路的人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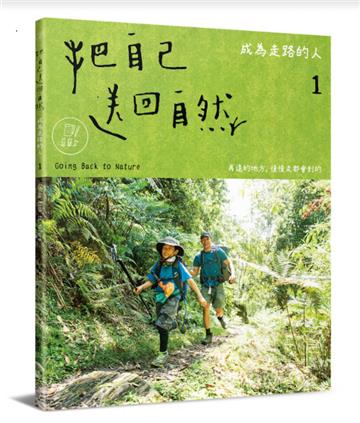 |
把自己送回自然(1):成為走路的人 作者:寫寫字採編學堂第七屆師生(2020年) 出版社:寫寫字工作室 出版日期:2021-12-22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6 |
台灣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把自己送回自然(1):成為走路的人
封面故事
再遠的地方,慢慢走總會到的
「開始時,很難有心情去欣賞,什麼聲景都感覺不到,只聽到心臟怦怦怦。」
我們用一年的時間往返自然,書寫描繪它的豐盛樣貌。
5種棲地表情、7條風景步道、3區自在串遊的步道群、1處看似無路可循的祕徑,
並邀請14位野地職人分享走入自然的準備,
如何培養心態體力、善用配備顧好安全。
有開始但沒有結束,我們也成為走路的人。
內容簡介
*以漫畫故事揭開序幕,貫穿三冊
漫畫中的主人翁代表作者群,內容是一整年走入自然的歷程,也循序漸進地引領讀者「把自己送回自然」。
*循序漸進打開視野,帶回豐盛
《把自己送回自然:成為走路的人》 運用大量插畫與解說方式,介紹人人均可親近的步道開始,生動凸顯各路線的棲地生態特色、職人經驗分享安全須知、食物準備等,閱讀間很容易就吸收了親近自然的基礎認識。
《把自己送回自然:遇見野地職人》 介紹守護自然與人們的12種類型工作者,從野地職人的故事,讀者更能感受到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並不遙遠、也不只有掠奪。
《把自己送回自然:與自然對話》 6篇自序故事、3個紙上攝影展,以大量視覺饗宴與感受書寫的呈現,鼓勵讀者也可以用五感去體驗,把豐盛帶給自己。
*把自己送回自然,從花蓮開始
花蓮的山海深具療癒能量,非常值得推薦給所有讀者,不趕路慢慢走,找回與大自然的連結。
寫字採編學堂 每年底10-12月開課,招收十位在地年輕人學習採訪編輯,以出版、展演活動等方式,關注一個在地議題。寫寫字工作室 出版「每個人都可以說故事」的作品,相信每個人都可以運用雙手與心,記錄我們在地球上活蹦亂跳的足跡。
章節試閱
再遠的地方,慢慢走都會到的(文字|陳盈臻)
那是我與山的開始
夏季的天光來得早,小時候每逢週日,阿公阿嬤會偕著全家人來到臺北圓山飯店後方的親山步道,隨階梯而上,兩側各有數座羽球場,孩子們會在這裡打羽球,大人們則用家常泡茶。坦白說,對於幼小的內心,要在假日趕赴陡傾的山林是帶有些許抗拒的,唯一吸引我的,是結束後大夥爭相向下衝至山腳的雜貨店,打開冰涼的透明櫃,選一瓶喜歡的飲料,好似作為今日慷慨赴約的獎勵。
我不能確定是不是從這時候開始懂得爬山是什麼,但它卻像個約定放在心底,其餘的記憶,都已模糊。
有伴...
那是我與山的開始
夏季的天光來得早,小時候每逢週日,阿公阿嬤會偕著全家人來到臺北圓山飯店後方的親山步道,隨階梯而上,兩側各有數座羽球場,孩子們會在這裡打羽球,大人們則用家常泡茶。坦白說,對於幼小的內心,要在假日趕赴陡傾的山林是帶有些許抗拒的,唯一吸引我的,是結束後大夥爭相向下衝至山腳的雜貨店,打開冰涼的透明櫃,選一瓶喜歡的飲料,好似作為今日慷慨赴約的獎勵。
我不能確定是不是從這時候開始懂得爬山是什麼,但它卻像個約定放在心底,其餘的記憶,都已模糊。
有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幕故事|蕭舜恩
*成為走路的人
再遠的地方,慢慢走都會到的|陳盈臻
七星潭海道_走在微笑海灣|夏尊湯
棲地表情:海岸保安林|俞凱倫
撒固兒步道_15分鐘擁抱森林|楊庭嘉
美崙山公園步道群_生機盎然城市之丘|陳乙先
鯉魚山步道群_小百岳的7種風貌|周明慧
棲地表情:農田溪畔|俞凱倫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單車步道_動物穿梭綠廊道|俞凱倫
棲地表情:人造林/次生林|俞凱倫
米棧古道_有百年樹爺爺祝福的眺望台|王心怡
森坂步道_朝聖之路安靜獨行|王心怡
瓦拉米步道_「跟我來」蕨森林|王...
*成為走路的人
再遠的地方,慢慢走都會到的|陳盈臻
七星潭海道_走在微笑海灣|夏尊湯
棲地表情:海岸保安林|俞凱倫
撒固兒步道_15分鐘擁抱森林|楊庭嘉
美崙山公園步道群_生機盎然城市之丘|陳乙先
鯉魚山步道群_小百岳的7種風貌|周明慧
棲地表情:農田溪畔|俞凱倫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單車步道_動物穿梭綠廊道|俞凱倫
棲地表情:人造林/次生林|俞凱倫
米棧古道_有百年樹爺爺祝福的眺望台|王心怡
森坂步道_朝聖之路安靜獨行|王心怡
瓦拉米步道_「跟我來」蕨森林|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