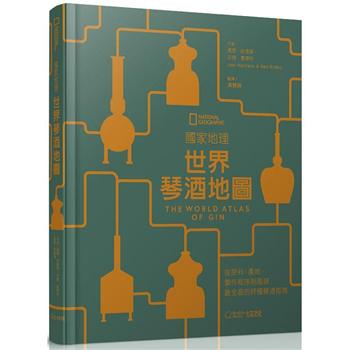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音樂札記《交響》《音樂札記》合集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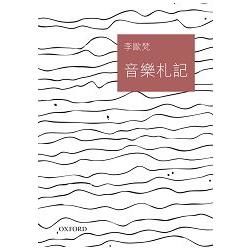 |
音樂札記《交響》《音樂札記》合集 作者:李歐梵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15-07-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14頁 / 14 x 19.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68 |
藝術設計 |
$ 474 |
藝術設計 |
$ 558 |
中文書 |
$ 558 |
音樂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音樂札記《交響》《音樂札記》合集
內容簡介
本書是李歐梵教授兩本音樂隨筆《交響》《音樂札記》的合集。對作者來說, 古典音樂就是日常生活, 至少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古典音樂從來沒有死, 還是活生生的。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歐梵
2015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河南太康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中央研究員院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曾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西湖的彼岸》、《上海摩登》、《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囈語》、《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臆語》、《我的哈佛歲月》、《蒼涼與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響》、《睇色戒》、《人文文本》等。
李歐梵
2015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河南太康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中央研究員院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曾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西湖的彼岸》、《上海摩登》、《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囈語》、《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臆語》、《我的哈佛歲月》、《蒼涼與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響》、《睇色戒》、《人文文本》等。
目錄
第一部分
3聽莫扎特的心路歷程
5莫扎特音樂司以養生
12《魔笛》狂想曲
17陳酒愈醇一聽莫扎特《費加羅婚禮》
22看賴聲川的《費加羅婚禮》
25波恩的莫扎特
29還我莫扎特
32後期莫扎特
35莫扎特和蕭斯達高維契一天堂對話錄
40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一(紀念節曰)
43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二(我讀《見證》)
46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49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四(形式主義的渾沌?)
53發現蕭奇斯達高維契之五(「反對形式主義的小天堂」)
57發現爾斯達高雄契之六(革命也斷腸)
62發現爾斯達高雄契之七(輕與重)
66發現肅斯達高維契之八(樂觀與悲觀)
71今天我也聽馬勒
73馬勒的《復活》交響曲
81馬勒的音樂盛宴
87聽馬勒,談「港樂」
94馬勒的第四交響樂
96生命的奉獻一談馬勒的第八交響樂
100聽《大地之歌》
103壯觀的演出一聽馬勒第八交響曲
109馬勒的《第九交響曲》
112拉陶成竹在胸
119柏林愛樂樂園 - 一流音樂家的互動
123聽柏林愛樂樂團
125漫談狄信湯瑪斯
137三藩市交響樂團
144美國樂壇新星的《電子吉他協奏曲》
147香港文化中心 - 不能聽馬友友演奏巴哈
153古風今詮
157華人音樂家印象
167香港聆樂手記
201文學、 電影 、音樂
209「敝帚」並不「自珍」 - 有覆於戴天者
216《夢幻曲》的童年回憶
218布拉姆斯晚年的鋼琴小品
第二部分
223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227紀念西貝流士
231霍夫曼斯塔爾與《玫瑰騎士》
235浪漫的餘燼
239向蕭斯達高維契致敬
242聽葛利格
246葛利約夫的神奇音樂
249郭文景歌劇美首演驚艷
258史克里亞賓的神秘音樂
261指揮家掠影
267芝加哥時代的蕭提
271紀念托斯卡尼尼
278紀念卡拉揚
282激情的魔力
289談根特萬德
294指揮家的魔術大師
298和迪華特-席談
306誰還記得杜拉第
310艾森巴哈的馬勒
314張弦執棒紐約愛樂技驚香港
319紀念羅斯托波維奇
323紀念里希特:一位「謎」樣的鋼琴大師
328天賦的抒情男高音
332閒談五位女高音
336誰是Diva
340聽音樂會札記
369我的天王歌星
373海菲茲站和雷賓
375我的唱碟入門經
383遨遊歐洲的音樂節和音樂景點
391我的音樂因緣與姻緣
李子玉
3聽莫扎特的心路歷程
5莫扎特音樂司以養生
12《魔笛》狂想曲
17陳酒愈醇一聽莫扎特《費加羅婚禮》
22看賴聲川的《費加羅婚禮》
25波恩的莫扎特
29還我莫扎特
32後期莫扎特
35莫扎特和蕭斯達高維契一天堂對話錄
40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一(紀念節曰)
43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二(我讀《見證》)
46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49發現蕭斯達高維契之四(形式主義的渾沌?)
53發現蕭奇斯達高維契之五(「反對形式主義的小天堂」)
57發現爾斯達高雄契之六(革命也斷腸)
62發現爾斯達高雄契之七(輕與重)
66發現肅斯達高維契之八(樂觀與悲觀)
71今天我也聽馬勒
73馬勒的《復活》交響曲
81馬勒的音樂盛宴
87聽馬勒,談「港樂」
94馬勒的第四交響樂
96生命的奉獻一談馬勒的第八交響樂
100聽《大地之歌》
103壯觀的演出一聽馬勒第八交響曲
109馬勒的《第九交響曲》
112拉陶成竹在胸
119柏林愛樂樂園 - 一流音樂家的互動
123聽柏林愛樂樂團
125漫談狄信湯瑪斯
137三藩市交響樂團
144美國樂壇新星的《電子吉他協奏曲》
147香港文化中心 - 不能聽馬友友演奏巴哈
153古風今詮
157華人音樂家印象
167香港聆樂手記
201文學、 電影 、音樂
209「敝帚」並不「自珍」 - 有覆於戴天者
216《夢幻曲》的童年回憶
218布拉姆斯晚年的鋼琴小品
第二部分
223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227紀念西貝流士
231霍夫曼斯塔爾與《玫瑰騎士》
235浪漫的餘燼
239向蕭斯達高維契致敬
242聽葛利格
246葛利約夫的神奇音樂
249郭文景歌劇美首演驚艷
258史克里亞賓的神秘音樂
261指揮家掠影
267芝加哥時代的蕭提
271紀念托斯卡尼尼
278紀念卡拉揚
282激情的魔力
289談根特萬德
294指揮家的魔術大師
298和迪華特-席談
306誰還記得杜拉第
310艾森巴哈的馬勒
314張弦執棒紐約愛樂技驚香港
319紀念羅斯托波維奇
323紀念里希特:一位「謎」樣的鋼琴大師
328天賦的抒情男高音
332閒談五位女高音
336誰是Diva
340聽音樂會札記
369我的天王歌星
373海菲茲站和雷賓
375我的唱碟入門經
383遨遊歐洲的音樂節和音樂景點
391我的音樂因緣與姻緣
李子玉
序
序
近年來我不知不覺間寫了不少有關古典音樂的文章,並曾先後結集在台灣、中國大陸和新加坡出版。在香港出版卻是第一次,也是最新結集的文章總彙,與以前的四個集子完全不同(除了兩三篇關於馬勒的文章)。
我明知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喜歡古典音樂的「樂迷」是小眾中的小眾,但正因為如此我才寫音樂文章。沒想到竟然有人看,而且反應熱烈,我非但和幾位(極少數)樂評家結為朋友,而且還交了不少知音,在電郵上談心,或在音樂會上打打招呼,真是不亦樂乎。名導演李安說:「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而我的「斷背山」就是音樂!我也萬萬沒有料到香港的「音樂斷背山」的人數還相當可觀!有了這一個讀者群,我也樂意地寫下去,而且約稿的報刊也越來越多?令我應接不暇。本書中的文章大多已在《信報》《信報月刊》、《明報》、《明報月刊》和《AM Post藝術地圖》等處發表。甚至連內地的權威音樂雜誌如《愛樂者》和《留聲機》也向我約稿。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怎麼不到兩三年我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樂評家?甚至因年歲關係,往往被奉為「資深」!
本書勉可算是個「樂迷」或「業餘樂評家」(因為我沒有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雖然家父母都是音樂家)對於香港樂壇的一個回應。如果我的文章能夠激起這些小眾讀者和聆樂者的興趣,甚至間或普及到一部份喜歡音樂但無暇去聽音樂的人,則予願已足 。
本書前半部的文章皆與二OO五至二OO六年樂季有關:柏林愛樂和三藩市交響樂團先後來港獻藝,我自願為文鼓吹,竟然見到兩位世界級的名指揮西蒙﹒拉陶(Simon Rattle)和湯瑪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並與之交談或進餐,真是三生有幸。香港的兩個樂團「港樂」和「小交」的音樂會,我作為半個香港人,自當捧場,不知不覺也寫下不少評論文章。但我個人較重視的是今年(2006年)的兩位作曲家的誕辰紀念:莫扎特的二百五十周年和蕭斯達高維契的一百周年。特別是後者,我為之寫了一系列文章,內中至少一半尚未發表過,這才發現我的觀點又和以前不同,是一種新發現,在沾沾自喜之餘,也不揣淺陋,獻給小眾中的「蕭迷」。
最後要在此聲明的是,這些文章絕非專業或學術作品,而是故意把音樂置於日常生活中的產物。如果有一件事我可以自豪,就是每天聽古典音樂,也不斷買唱碟和影碟,把自己浸淫在音樂天地之中,甚至把我妻每周給我的零用錢全數花在音樂上面──Why not? 人生到此,我也該隨心所欲了吧!
本書第二部分收集了近兩年來我在香港和台北發表的一部分音樂雜文,是繼《交響:音樂札記》(牛津2006)的另一本音樂隨筆。原書名就叫《音樂札記》。說來汗顏,我只不過是一個樂迷,並非音樂家或專業樂評家,卻不知不覺地「炮製」出大量此類文章,而且已經結集出版了四五本書,如此「不務正業」,原因何在?
第一當然是我太喜愛古典音樂了。雖說有「家學淵源」(父母親都是專業音樂家),但畢竟是個門外漠,從外行的角度看行內,自會養成一種習慣,有好的音樂會必到,忙得疲於奔命,但樂此不疲,結果文章越寫越多了。
第二個原因是香港樂壇對我的厚愛,即使我批評待很嚴厲,也不以為杵,依然把我視為樂評家。每年春季的的藝術節,主辦當局還願意邀請我以媒體身份參加各種發表會和音樂會,使我受寵若驚。香港的港樂和小交,更加如此。
第三,也許正因為我是個樂迷,所以也交上了不少樂迷間朋友,他們非但讀我的文章,偶爾還寫電郵來和我討論,甚至邀我喝咖啡、吃飯。我有一群「馬勒仔」的年輕朋友,更把我引為知己,毫無代構。我和他們在聽完音樂會後交換意見,有時。也把他們的意見寫在我的文章裏。更令我感動的是,偶然會在商場、音樂廳或街頭,碰到陌生人向我打招呼,有時還會拿著我的音樂書,指正我的錯誤,令我銘感於心。誰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連喜歡古典音樂的人都多有所在,雖然和流行歌迷的人數相比還是小眾。然而,我的所有文章和書,都是為了小眾讀者寫的,從來沒有想到要暢銷賺錢。
還有一個原因,是台北的《謬斯客》(Muzik)來雜誌,創辦人 胡先生初見面就向我約稿,盛情難卻,遂勉強每月供稿一篇。然而台灣懂古典音樂的人很多,欣賞的水準也高,並非我這種外行樂迷可以「唬」得住的,看來我不久要鳴金收兵了。中國大陸的重量級音樂就雜誌《留聲機》和《音樂愛好者》,經友人 介紹,偶爾也願意刊登我的文章,令我不勝榮幸。承蒙這幾位音樂大家和編者的青睞,我只能盡綿薄之力了。
此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發表於香港的《明報月刊》、《明報》世紀版、《信報》文化版和am post雜誌。我在此向以上的各刊物主編致以衷誠的謝意。牛津為我出書,當然更令我感激。除了以上的外在原因之外,我還應該作一點內在的自我辯解。作為研究文學和歷史學者和教書匠,多年來我養成一種習慣:必須事事講出一番道理,否則似乎對不起我的學生。這本書當然不是學術著作,但我還是有一股講道理的衝動。我預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為甚麼在此時此地,我還要大力鼓吹古典音樂?且容我略抒己見。
最近我買了一本英文書《其餘是噪音:聆聽二十世紀》,讀後心有戚戚焉。此書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音樂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上個世紀已成了歷史,但我們怎麼回顧這個舉世動盪不安的一百年?作者的回答就是「聆聽」,因為音樂也是一種文化史的記錄,它和文學、藝術一樣,充滿了人的創意,是人類集體回憶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我每吹在課堂上教文學和歷史,眼睛看的是文字和文本,腦海中湧現的卻是音樂和影靠(我認為電影藝術也是二十世紀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現在香港大談創意工業,往往把內容先後倒置,把工業生產和消費放在創意之前,我卻和這本書的作者Alex Ross(他時常在New Yorker發表音樂文章)一樣,把文化視為一波又一波的各種創意積累,先有了創意,才有工業和商機。
然而創意文化需要人,音樂家和聽原二者缺一不司,而且還要互動。我不相信與人的創意或時空環境無關的「文本」,即使「現代主義」的某些作曲家或文學家只為自己而寫,心目中完全沒有讀者或聽者,他們依然有一種「歷史感」。就音樂而言,或為整個音樂傳統形式的創新而作,或為達到自己的某種藝術理想(如茍伯格的十二音律)。然而,二者仍然和人(創意者)分不間,否則乾脆用電腦或機器自動創作就司以了。除作者和聽者之外,當然還有演奏家或演繹家,音樂是經過這些演奏藝術家傳給聽眾的。目前的流行音樂把這類人捧為明星偶像,聽眾成了盲目的「粉絲」,作曲家和作詞家幾乎成了明星的附庸,快被遺忘了,我不能荷同。如此繼續發展下去,音樂真的會變成包裝後的商品,甚至感官上的「噪音」。
我絕對無意貶低流行曲,因為不少古典音樂都是當時的流行曲(如李察史特勞斯的華爾茲),有的卻傳了下來,或被忽視多年後才被發掘出來(如馬勒),而成為流行的經典。這是一個極淺顯的道理。因此我也把這個「鐵三角」作為全書組織分類的標準──作曲家、演奏家(特別是指揮家)和聽者。這聆聽的人當然是我,但也希望藉此把個人聆聽的感想和經驗和所有聆聽者共享。
我欣賞古典音樂的方法,真的是先享受現場聆聽,聽後找唱片聽、再找書來看,由此而作心靈上的「自我增值」。從這種先聽後看的過程中,我不知不覺也會感受到一個時代和地方的文化風貌:世紀末的維也納、三十年代的德國、二戰後的美國。因此,聽西洋古典音樂也是一種心靈上的「神遊」,和西方古人交流,你不必懂外文(雖然我往往從唱諜和音樂會說明書上學到不少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就可以登堂入室,何樂而不為?音樂無國界,其實更沒有古今之別,因為現場聽到的演奏家都是今人,即使作了古,在唱片中依然有所謂的Living Presence,聽其音恍若見其人,比照片更真切,何況現在還有DVD。
不少香港朋友說不懂古典音樂,要我指點迷津,我的回答是:只要多聽、亂聽,先養成一種聽的習慣,時日一久就入門了。不必把音樂當成一種專業知識,業餘的愛好就夠了,自然而然會感到精神生活的豐富。又有人說太忙,沒有時間聽音樂,怎麼辦?我的回答是「肚子餓了,總有時間吃飯吧,心靈也會飢餓的,每天也需要音樂三餐」。拜科技之賜,有了耳機和音響,連返工放工坐車開車,甚至在家睡覺前都可以聽。聽甚麼呢?聽你喜歡聽的旋律,然後再多聽幾遍,哼不出來不要緊,聽進耳裏,嵌在心襄就夠了。為此我還不揣淺陋,特別寫了一篇唱片入門經。
總而言之,音樂就是日常生活,至少應該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的信念。古典音樂是音樂的一種,它並沒有死,還是活生生的,因為每位樂師和演奏家的詮釋和表現都不同,所以耐聽,而現今大部分的流行曲唱起來幾乎千篇一律,聽一遍就覺得夠了,除非演唱者本人如張國榮有涵養,又有個性。
說了一大堆道理,可能仍未能打動你。即使如此,我也自得其樂,這本書獻給所有聆聽古典音樂而自得其樂的小眾讀者。我很幸運,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還有一個和我朝夕共享這種樂趣的老婆李子玉,她縱容我浸淫音樂世界,說可以調節緊張的情緒,減少心理壓力,在此我也請她為我寫一篇特稿。這本小書,我願意獻給她。
近年來我不知不覺間寫了不少有關古典音樂的文章,並曾先後結集在台灣、中國大陸和新加坡出版。在香港出版卻是第一次,也是最新結集的文章總彙,與以前的四個集子完全不同(除了兩三篇關於馬勒的文章)。
我明知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喜歡古典音樂的「樂迷」是小眾中的小眾,但正因為如此我才寫音樂文章。沒想到竟然有人看,而且反應熱烈,我非但和幾位(極少數)樂評家結為朋友,而且還交了不少知音,在電郵上談心,或在音樂會上打打招呼,真是不亦樂乎。名導演李安說:「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而我的「斷背山」就是音樂!我也萬萬沒有料到香港的「音樂斷背山」的人數還相當可觀!有了這一個讀者群,我也樂意地寫下去,而且約稿的報刊也越來越多?令我應接不暇。本書中的文章大多已在《信報》《信報月刊》、《明報》、《明報月刊》和《AM Post藝術地圖》等處發表。甚至連內地的權威音樂雜誌如《愛樂者》和《留聲機》也向我約稿。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怎麼不到兩三年我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樂評家?甚至因年歲關係,往往被奉為「資深」!
本書勉可算是個「樂迷」或「業餘樂評家」(因為我沒有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雖然家父母都是音樂家)對於香港樂壇的一個回應。如果我的文章能夠激起這些小眾讀者和聆樂者的興趣,甚至間或普及到一部份喜歡音樂但無暇去聽音樂的人,則予願已足 。
本書前半部的文章皆與二OO五至二OO六年樂季有關:柏林愛樂和三藩市交響樂團先後來港獻藝,我自願為文鼓吹,竟然見到兩位世界級的名指揮西蒙﹒拉陶(Simon Rattle)和湯瑪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並與之交談或進餐,真是三生有幸。香港的兩個樂團「港樂」和「小交」的音樂會,我作為半個香港人,自當捧場,不知不覺也寫下不少評論文章。但我個人較重視的是今年(2006年)的兩位作曲家的誕辰紀念:莫扎特的二百五十周年和蕭斯達高維契的一百周年。特別是後者,我為之寫了一系列文章,內中至少一半尚未發表過,這才發現我的觀點又和以前不同,是一種新發現,在沾沾自喜之餘,也不揣淺陋,獻給小眾中的「蕭迷」。
最後要在此聲明的是,這些文章絕非專業或學術作品,而是故意把音樂置於日常生活中的產物。如果有一件事我可以自豪,就是每天聽古典音樂,也不斷買唱碟和影碟,把自己浸淫在音樂天地之中,甚至把我妻每周給我的零用錢全數花在音樂上面──Why not? 人生到此,我也該隨心所欲了吧!
本書第二部分收集了近兩年來我在香港和台北發表的一部分音樂雜文,是繼《交響:音樂札記》(牛津2006)的另一本音樂隨筆。原書名就叫《音樂札記》。說來汗顏,我只不過是一個樂迷,並非音樂家或專業樂評家,卻不知不覺地「炮製」出大量此類文章,而且已經結集出版了四五本書,如此「不務正業」,原因何在?
第一當然是我太喜愛古典音樂了。雖說有「家學淵源」(父母親都是專業音樂家),但畢竟是個門外漠,從外行的角度看行內,自會養成一種習慣,有好的音樂會必到,忙得疲於奔命,但樂此不疲,結果文章越寫越多了。
第二個原因是香港樂壇對我的厚愛,即使我批評待很嚴厲,也不以為杵,依然把我視為樂評家。每年春季的的藝術節,主辦當局還願意邀請我以媒體身份參加各種發表會和音樂會,使我受寵若驚。香港的港樂和小交,更加如此。
第三,也許正因為我是個樂迷,所以也交上了不少樂迷間朋友,他們非但讀我的文章,偶爾還寫電郵來和我討論,甚至邀我喝咖啡、吃飯。我有一群「馬勒仔」的年輕朋友,更把我引為知己,毫無代構。我和他們在聽完音樂會後交換意見,有時。也把他們的意見寫在我的文章裏。更令我感動的是,偶然會在商場、音樂廳或街頭,碰到陌生人向我打招呼,有時還會拿著我的音樂書,指正我的錯誤,令我銘感於心。誰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連喜歡古典音樂的人都多有所在,雖然和流行歌迷的人數相比還是小眾。然而,我的所有文章和書,都是為了小眾讀者寫的,從來沒有想到要暢銷賺錢。
還有一個原因,是台北的《謬斯客》(Muzik)來雜誌,創辦人 胡先生初見面就向我約稿,盛情難卻,遂勉強每月供稿一篇。然而台灣懂古典音樂的人很多,欣賞的水準也高,並非我這種外行樂迷可以「唬」得住的,看來我不久要鳴金收兵了。中國大陸的重量級音樂就雜誌《留聲機》和《音樂愛好者》,經友人 介紹,偶爾也願意刊登我的文章,令我不勝榮幸。承蒙這幾位音樂大家和編者的青睞,我只能盡綿薄之力了。
此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發表於香港的《明報月刊》、《明報》世紀版、《信報》文化版和am post雜誌。我在此向以上的各刊物主編致以衷誠的謝意。牛津為我出書,當然更令我感激。除了以上的外在原因之外,我還應該作一點內在的自我辯解。作為研究文學和歷史學者和教書匠,多年來我養成一種習慣:必須事事講出一番道理,否則似乎對不起我的學生。這本書當然不是學術著作,但我還是有一股講道理的衝動。我預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為甚麼在此時此地,我還要大力鼓吹古典音樂?且容我略抒己見。
最近我買了一本英文書《其餘是噪音:聆聽二十世紀》,讀後心有戚戚焉。此書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音樂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上個世紀已成了歷史,但我們怎麼回顧這個舉世動盪不安的一百年?作者的回答就是「聆聽」,因為音樂也是一種文化史的記錄,它和文學、藝術一樣,充滿了人的創意,是人類集體回憶不可或缺的一環。所以我每吹在課堂上教文學和歷史,眼睛看的是文字和文本,腦海中湧現的卻是音樂和影靠(我認為電影藝術也是二十世紀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現在香港大談創意工業,往往把內容先後倒置,把工業生產和消費放在創意之前,我卻和這本書的作者Alex Ross(他時常在New Yorker發表音樂文章)一樣,把文化視為一波又一波的各種創意積累,先有了創意,才有工業和商機。
然而創意文化需要人,音樂家和聽原二者缺一不司,而且還要互動。我不相信與人的創意或時空環境無關的「文本」,即使「現代主義」的某些作曲家或文學家只為自己而寫,心目中完全沒有讀者或聽者,他們依然有一種「歷史感」。就音樂而言,或為整個音樂傳統形式的創新而作,或為達到自己的某種藝術理想(如茍伯格的十二音律)。然而,二者仍然和人(創意者)分不間,否則乾脆用電腦或機器自動創作就司以了。除作者和聽者之外,當然還有演奏家或演繹家,音樂是經過這些演奏藝術家傳給聽眾的。目前的流行音樂把這類人捧為明星偶像,聽眾成了盲目的「粉絲」,作曲家和作詞家幾乎成了明星的附庸,快被遺忘了,我不能荷同。如此繼續發展下去,音樂真的會變成包裝後的商品,甚至感官上的「噪音」。
我絕對無意貶低流行曲,因為不少古典音樂都是當時的流行曲(如李察史特勞斯的華爾茲),有的卻傳了下來,或被忽視多年後才被發掘出來(如馬勒),而成為流行的經典。這是一個極淺顯的道理。因此我也把這個「鐵三角」作為全書組織分類的標準──作曲家、演奏家(特別是指揮家)和聽者。這聆聽的人當然是我,但也希望藉此把個人聆聽的感想和經驗和所有聆聽者共享。
我欣賞古典音樂的方法,真的是先享受現場聆聽,聽後找唱片聽、再找書來看,由此而作心靈上的「自我增值」。從這種先聽後看的過程中,我不知不覺也會感受到一個時代和地方的文化風貌:世紀末的維也納、三十年代的德國、二戰後的美國。因此,聽西洋古典音樂也是一種心靈上的「神遊」,和西方古人交流,你不必懂外文(雖然我往往從唱諜和音樂會說明書上學到不少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就可以登堂入室,何樂而不為?音樂無國界,其實更沒有古今之別,因為現場聽到的演奏家都是今人,即使作了古,在唱片中依然有所謂的Living Presence,聽其音恍若見其人,比照片更真切,何況現在還有DVD。
不少香港朋友說不懂古典音樂,要我指點迷津,我的回答是:只要多聽、亂聽,先養成一種聽的習慣,時日一久就入門了。不必把音樂當成一種專業知識,業餘的愛好就夠了,自然而然會感到精神生活的豐富。又有人說太忙,沒有時間聽音樂,怎麼辦?我的回答是「肚子餓了,總有時間吃飯吧,心靈也會飢餓的,每天也需要音樂三餐」。拜科技之賜,有了耳機和音響,連返工放工坐車開車,甚至在家睡覺前都可以聽。聽甚麼呢?聽你喜歡聽的旋律,然後再多聽幾遍,哼不出來不要緊,聽進耳裏,嵌在心襄就夠了。為此我還不揣淺陋,特別寫了一篇唱片入門經。
總而言之,音樂就是日常生活,至少應該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的信念。古典音樂是音樂的一種,它並沒有死,還是活生生的,因為每位樂師和演奏家的詮釋和表現都不同,所以耐聽,而現今大部分的流行曲唱起來幾乎千篇一律,聽一遍就覺得夠了,除非演唱者本人如張國榮有涵養,又有個性。
說了一大堆道理,可能仍未能打動你。即使如此,我也自得其樂,這本書獻給所有聆聽古典音樂而自得其樂的小眾讀者。我很幸運,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還有一個和我朝夕共享這種樂趣的老婆李子玉,她縱容我浸淫音樂世界,說可以調節緊張的情緒,減少心理壓力,在此我也請她為我寫一篇特稿。這本小書,我願意獻給她。
2008年4月20日於九龍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