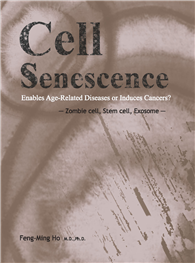冰島犯罪小說國際暢銷奇蹟!
《13.67》倒敘推理傑作X《霧中的男孩》冷冽北歐奇案
全系列三冊《暗潮》、《孤島》、《謎霧》同步出版
每年只發生兩件謀殺的極北小國、
沒有主角威能的孤傲女警探
從告別警界的最後一案,追回生命中殘酷陰影的起點
*名列《泰晤士報》1945年以降百大犯罪小說
*售出全球共33國版權,登上英國、澳洲、瑞典、法國暢銷排行榜冠軍
*即將由美國CBS Studios改編電視影集
*安東尼‧赫洛維茲、伊恩‧藍欽、李‧查德、A.J.芬恩等推理名家盛讚
推理評論人/冬陽、駐冰島文字部落客/冰島太太、推理評論家/路那、導演/盧建彰、國際版權經紀人/譚光磊──好評推薦
堅毅聰敏的冰島女警瑚達一生在男性主導的刑事偵察部奮鬥,卻長年無緣升遷,還被迫提早退休。主管勉為其難地允諾她在退休前的兩週內任選一件未解懸案重啟調查,瑚達於是挑中一年多年前首都近郊的俄國女子溺斃案,不但推翻原本判定為自殺的草率結論,更發現了另一名移民女性失蹤的案外案。
然而,瑚達沒有因此在警局內博得遲來的掌聲,反而換來更孤立無援的處境;當兩週的破案期限逐漸接近,她面對的會是真相大白的時刻、或是無力回天的終局……?
不同於常見的犯罪推理小說往往讓讀者跟著系列主角從昔到今一路走來,《冰島暗湧》系列首先以第一集《暗潮》將瑚達的探案人生從終點寫起,而後再透過《孤島》與《謎霧》中兩樁為她帶來重大衝擊的舊案、兩個在她內心劃下深刻痕跡的時間點,追溯她「為何成為一位這樣的警探」,兼具北歐犯罪小說代表性的冷冽陰暗和社會批判特色,以及經典推理作品的簡練風範。
❖故事簡介❖
┤I:暗潮├
「有時候他們會試著逃脫,卻忘記我們住的不過是個小島。他們都會回來。幾乎都會。」
鄰近冰島首都圈的移民臨時居所常年人滿為患,國籍、性別、出身背景各異的住客懷夢而來,但多數人只能夢碎離開。離鄉背井的俄羅斯女孩曾在這裡盼望得到庇護身分、準備展開新生活,最終卻無故消失、陳屍在陰寒的海灣。
女警探瑚達一生在男性主導的刑事偵察部奮鬥,卻得不到升遷與肯定,還被迫提早退休。主管為了打發她找點事情消磨時間,勉為其難地承諾她在退休前的兩週內,可以任選一件未解懸案重啟調查。瑚達於是挑中了一年多前這樁發生於首都近郊的俄國女子溺死案,原本警方以自殺草草結案,如今她卻發現死者當時才剛獲得期盼已久的居留權,根本沒有尋短的理由,而且同一個地區在不久前還有另一名俄國移民女性離奇失蹤。
瑚達努力想用這「最後一案」作為自己實力的證明與完美的退場,隨著她鍥而不捨的追查,受害女子生前令人心驚膽顫的線索逐漸浮現,難民求助無門的困境與跨國人口販運的疑雲亦隨之躍上台面……
┤II:孤島├
「埃德利扎島就像另一個世界吧?只有我們和大自然,我們和大海。即使想走,也無法馬上離開......今晚這一刻,我們屬於這座小島。」
一九八七年,活潑亮麗的少女凱特拉在冰島西峽灣的偏僻度假小屋裡頭破血流慘死,反覆酗酒的父親成為警方眼中的頭號嫌疑犯,尚未等到判決宣告,便消沉地在獄中自殺,留下心碎的母親和滿腹懷疑的弟弟──達格。
十年後,凱特拉生前的好友班尼迪克、亞莉珊卓與克拉拉找了達格重聚出遊,來到遠離塵囂的幽靜外島上共度週末。當年,他們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凱特拉的命案之後變了樣:班尼迪克放棄了攻讀藝術的夢想,早婚的亞莉珊卓背負著育兒持家的重擔,迷惘而退縮的克拉拉始終無法找到穩定工作並搬出父母家,達格更是被迫承受旁人的異樣眼光、獨力照顧深受打擊的母親。
當四名老友在風景絕美的小島上談笑遊玩,他們彷彿終於擺脫了過去十年的陰霾,回到輕鬆無憂的年少時光。然而,眾人一起緬懷凱特拉的溫馨夜晚才剛過去,克拉拉竟在石崖下摔死,脖子上還有可疑的掐痕。
雷克雅維克的警探瑚達臨時被召來調查,在這座與世隔絕、只靠定時船班和外界往來的孤島上,凶手必定就在克拉拉的三名友人之中。但瑚達不僅要突破三名嫌疑人的心防,更要查明十年前凱特拉遇害的真相,才能真正理清案件的全貌……
┤III:謎霧├
「雪又開始下了,安安靜靜、冷酷無情地消滅謊言的證據。不管白色雪花在窗外舞動飄落得多麼漂亮,都與凶兆無異。」
冰島東部一座偏僻的鄉間農舍,每年深冬都遭遇大雪,時常導致道路封閉、通訊中斷。農舍裡住著埃納和艾拉這對相依為命的老夫婦,當他們準備迎接又一個只有對方作伴的聖誕節,天寒地凍的屋外竟來了一位陌生訪客敲門求助。這位訪客友善有禮地感謝他們的收留,埃納和艾拉卻屢次發現他在家中偷偷刺探,晚上也聽見他鬼祟的腳步聲;當他們在他的行李中發現了危險的鋒利獵刀,終於無法忽視心中的懷疑與警覺,決定將他鎖進閣樓空房以求自保。
但是,暴雪停歇的聖誕節過後,當地警方發現埃納與艾拉分別陳屍在屋內的不同地點,神祕訪客則不知所蹤。
警探瑚達從首都前往支援偵察,卻得知這對老夫婦的謎樣死亡並不是這個冬天發生在此地的唯一疑案──一名獨自環島旅行的少女也曾經在離農舍不遠的同一個區域失蹤,她的父親冒著寒冬出發來到此地尋找她,同樣在聖誕節後便杳無音訊。浮現的線索逐漸拼湊出謎題的真相,卻也喚起了瑚達不久前才經歷的相似傷痛……
❖國際好評❖
「讓讀者的心從第一頁懸宕到最後一頁。」
──卡特琳‧雅各布斯朵蒂(Katrin Jakobsdottir),冰島總理
「冰島是個小國,謀殺案發生率又是全球數一數二之低,然而這個人口數僅有三十六萬餘的國家,卻產出了兩位世界級的推理作家,安諾德‧英卓達尚與伊莎‧西格朵蒂;現在拉格納‧約拿森也證明自己足以與這兩位大師齊名。」
──《泰晤士報》
「世界級的推理作家,當代犯罪小說中最驚人的劇情鋪排。」
──《週日泰晤士報》
「貨真價實的犯罪小說傑作,向讀者介紹了一位深具原創性的主角、一段充滿曲折起伏的情節,最後則是令人喘不過氣的結局。」
──伊莎‧西格朵蒂,冰島犯罪小說天后
「結局著實令我屏息,這是近年的作家很難達到的成就。主角描寫得巧妙、複雜又立體。」
──伊恩‧藍欽,蘇格蘭黑色小說之王
「一位出色的冰島作家,替北歐黑色小說文類又增添了幾許幽暗感。」
──安東尼‧赫洛維茲,《喜鵲謀殺案》作者
「這個敘事手法絕佳的故事,從一開頭就吸引住我,結局的震撼更是令我瞪大眼睛。」
──費歐娜‧巴頓,《只有她知道》作者
「妙不可言的黑暗與扭曲!結局讓我大呼一聲『天啊!』」
──C.J.杜朵,《粉筆人》作者
「劇情鋪排得十分高超,結局更是震撼人心。」
──《衛報》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冰島暗湧三部曲(全系列套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09 |
二手中文書 |
$ 792 |
歐美推理小說 |
$ 825 |
翻譯推理/犯罪小說 |
$ 825 |
推理小說 |
$ 869 |
Books |
$ 869 |
Books |
$ 968 |
中文書 |
$ 990 |
文學作品 |
$ 990 |
超值套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冰島暗湧三部曲(全系列套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拉格納・約拿森Ragnar Jónasson
生於一九七六年,從小就熱愛偵探推理小說,十七歲起開始將「謀殺天后」克莉絲蒂的十四部作品翻成冰島文。他當過記者、律師和法學教授,目前專職寫作,以一系列六本的「黑色冰島」(Dark Iceland)犯罪小說走紅國際,首部曲《大雪紛飛的小鎮》(Snowblind)登上英國電子書排行榜冠軍,被《獨立報》選為最佳年度犯罪小說,賣出美、德、法、日、韓等二十國版權,電視劇也在籌拍中。
二○一八年,《冰島暗湧》系列的英文譯本由英國企鵝集團的通俗小說旗艦品牌 Michael Joseph 推出,並在伊恩‧藍欽和李‧查德等名家盛讚之下,讓約拿森這位新生代犯罪書寫好手更上層樓,並且售出影視版權,將由美國CBS電視台攝製改編影集。截至目前為止,約拿森的作品在全球賣座超過一百萬冊,翻譯成二十二種語言,在三十餘國出版,《冰島暗湧》系列第一集《暗潮》更被英國《週日泰晤士報》選入一九四五年以降百大犯罪推理小說。
相關著作:《冰島暗湧III:謎霧》《冰島暗湧II:孤島》《冰島暗湧I:暗潮》
譯者簡介
蘇雅薇
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雙碩士。喜歡為了休閒而閱讀,為了翻譯而閱讀。畢生志向是躲在書頁後面,用自己的筆,寫別人的故事。譯有《最好別想起》、《雌性物種》、《柏青哥》等書。譯作賜教:pwk072347@gmail.com
林零
淡江大學英文系畢。
偽台北人,浮沉出版業,熱愛小說。
喜歡黑貓、慢跑,以及一人旅行。
拉格納・約拿森Ragnar Jónasson
生於一九七六年,從小就熱愛偵探推理小說,十七歲起開始將「謀殺天后」克莉絲蒂的十四部作品翻成冰島文。他當過記者、律師和法學教授,目前專職寫作,以一系列六本的「黑色冰島」(Dark Iceland)犯罪小說走紅國際,首部曲《大雪紛飛的小鎮》(Snowblind)登上英國電子書排行榜冠軍,被《獨立報》選為最佳年度犯罪小說,賣出美、德、法、日、韓等二十國版權,電視劇也在籌拍中。
二○一八年,《冰島暗湧》系列的英文譯本由英國企鵝集團的通俗小說旗艦品牌 Michael Joseph 推出,並在伊恩‧藍欽和李‧查德等名家盛讚之下,讓約拿森這位新生代犯罪書寫好手更上層樓,並且售出影視版權,將由美國CBS電視台攝製改編影集。截至目前為止,約拿森的作品在全球賣座超過一百萬冊,翻譯成二十二種語言,在三十餘國出版,《冰島暗湧》系列第一集《暗潮》更被英國《週日泰晤士報》選入一九四五年以降百大犯罪推理小說。
相關著作:《冰島暗湧III:謎霧》《冰島暗湧II:孤島》《冰島暗湧I:暗潮》
譯者簡介
蘇雅薇
倫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雙碩士。喜歡為了休閒而閱讀,為了翻譯而閱讀。畢生志向是躲在書頁後面,用自己的筆,寫別人的故事。譯有《最好別想起》、《雌性物種》、《柏青哥》等書。譯作賜教:pwk072347@gmail.com
林零
淡江大學英文系畢。
偽台北人,浮沉出版業,熱愛小說。
喜歡黑貓、慢跑,以及一人旅行。
冰島暗湧三部曲(全系列套書) 相關搜尋
食物與廚藝 1-3 (第2版/3冊合售)就在這裡! 超理科校園解謎! 科學實驗中學 1-3套書 (附元素週期表雙面墊板/3冊合售)
海道.海盜三部曲套書: 海道: 紫氣東來+海東清夷+披星桴海 (3冊合售)
屠格涅夫經典文學套書: 羅亭+父與子 (2冊合售)
最高深度學習法: 開發大腦潛力, 快速提升學習質與量, 像愛因斯坦一樣學習, 成為超級知識海綿
下班後只想輕鬆煮200: 一鍋到底X省時3步驟, 22位人氣料理家的日常好食 (經典上菜版)
尋味香港套書: 台灣胃看香港餐桌+四季裡的港式湯水圖鑑 (2冊合售)
別再內耗, 及時覺醒找回安定幸福的暖萌套書: 及時覺醒+平靜寧和就在每一刻 (2冊合售)
BANANA FISH復刻版 6-10 (5冊合售)
阿德勒集大成之作: 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阿德勒的理解人性 (2冊合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