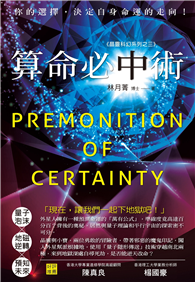1
週四上午,患者安娜走進心理諮商室。她很高興,值班的是個女諮商心理師。像其他諮商心理師那樣,她穿著白色的工作服(類似於外科醫生的那種醫師袍),戴著一副金框眼鏡,年約三十五歲。她正處在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成熟、理性、睿智卻又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安娜不再驚慌害怕了,諮商心理師將會理解安娜的尷尬處境,她會想出多種辦法解決安娜的人生難題。也許,安娜沉重的心理包袱就能卸下了。她會輕鬆的呼吸,甚至像許多正常人一樣,能在花園裡奔跑歌唱了。
也許這是個新的開始,安娜對自己說。諮商心理師微微的皺了下眉頭,馬上就裝作什麼也沒聽到。這個細微動作還是被安娜瞧見了。安娜是個過於敏感的人,從小就是這樣。安娜不清楚自己是否又在自言自語。但既然諮商心理師裝作什麼也沒發生,安娜自然也不好去問。這是個很好的策略。
安娜環顧四周,和很多心理諮商室一樣,這裡的牆壁也被刷成青色,房間中央也簡單的擺放著一桌二椅,桌子上堆滿了各種雜物:患者病歷表、墨水瓶、溫度計、各種顏色的水彩筆,甚至還有一包衛生棉。桌子旁擺著一張小床──白色的床單覆蓋在上面,床單就像五星級飯店裡的床單那樣乾淨──安娜明白,這是催眠用的,患者躺在小床上就能接受諮商心理師的催眠和暗示。和別處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心理諮商室還多了個小窗戶。黑色的鋼筋嚴密的裝飾著它,幾縷陽光透過空隙穿射進來,幾聲鳥叫聲也從窗戶外傳來。安娜能想像到屋外的陽光、草地、小鳥、和風、鮮花和美酒,當然,還有必不可少的帥哥猛男──這些可是安娜的摯愛啊。安娜心裡暖洋洋的。
諮商心理師說請坐。安娜轉過身,清了清嗓子,坐在患者專用的椅子上。安娜習慣性的轉了下椅子,椅子竟能自由轉動,就像安娜辦公室的電腦椅一樣。安娜不禁有點吃驚,她沒想到心理諮商室還有這麼高級的玩意。諮商心理師盯著安娜笑了一下,似乎很喜歡她臉上驚異的表情。諮商心理師翻開患者病歷表,優雅的坐在安娜對面。諮商心理師頭髮上停著一隻藍蝴蝶,牠凶狠而惡毒的望著安娜。有一刻,安娜真害怕牠會張開嘴巴噴射出毒液和火焰。如果她沒有辨認出那隻蝴蝶只是髮夾上的一個裝飾品的話,安娜肯定會尖叫起來。即使這樣,安娜仍舊嚇出一身冷汗。她剛才進屋時並沒看見諮商心理師頭上有蝴蝶髮夾啊。不過也許是安娜沒注意到,也許是諮商心理師在坐下的瞬間別上去的。安娜實在無法確定。
「太奇怪了。」
「什麼?」雖然已經見過比安娜更奇怪的患者,但諮商心理師還是沒有控制住自己的驚奇。
「哦,沒,沒什麼。」安娜知道自己又在自言自語。她狠狠的掐了下大腿根,算是給自己一個警告。
「妳怎麼了?不舒服嗎?」
「沒有。我挺好,好極了。」諮商心理師一直關切的看著安娜,安娜都感動得要哭了。很少有人對她這麼好過。
「我希望妳不要緊張。這裡很自由。妳完全可以把這裡當成妳的家。」諮商心理師微笑的望著安娜,然後放了一個悠長、洪亮而味道鮮美的臭屁。這太出乎意料了,安娜吃驚的望著諮商心理師,她已經笑得不行了,頭上的藍蝴蝶也隨著笑聲顫抖,就像在花叢中採到極品花蜜一般興奮。
「咯咯咯咯,對不起,真的對不起,請原諒我,我都笑得說不出話了。咯咯咯咯。我絕對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在患者面前放臭屁很沒面子,也很丟我諮商心理師的身分,但我也不想刻意壓抑自己,妳明白嗎?我不喜歡壓抑自己就像我不喜歡患者壓抑自己一樣,我想讓患者放鬆下來,如果他們能學會放鬆,他們的病也就好了一大半了。而且,我還想要妳親自見證這裡的自由。咯咯咯咯,不管妳是誰──是小偷也好,是殺人犯也好,是國家追捕的逃犯也好──只要來到這裡,妳都會受到保護,受到我們的絕密保護,沒有人會欺負妳,妳可以隨意的做任何事情,只要是出於真心,我都會支持妳,即使是比放臭屁嚴重一百倍的事情我也支持……我想滿足妳,妳一定覺得奇怪,但這確實是真的。妳可以隨意打開心靈,我絕不會有任何的恥笑或者看不起,就像妳不會恥笑或者看不起我放臭屁一樣……咯咯咯咯,放臭屁實在太好笑了,不是嗎?──妳太容易緊張了,妳該學會微笑,這樣妳就能好了。咯咯咯咯,說真的,這個屁太臭了,真太他媽的臭,我都三個月沒放出這樣臭的屁了。咯咯咯咯,妳不覺得很好笑嗎?妳一點都沒笑,真的,這樣可不行,妳要學會欣賞生活中的幽默。咯咯咯咯……」
像剛剛下過蛋的老母雞,諮商心理師又笑了好一陣才停下來。隨著她笑聲的高低快慢,那隻藍蝴蝶不斷變換著採蜜的各種造型,一會是芳草渡式,一會是探春令式,一會是滿江紅式,一會是破陣樂式,一會又是鳳簫吟式,一會又是洞仙歌式、迷神引式、少年遊式……安娜都快看暈了。
「是的,嗯,是的,這很可笑,妳可真幽默。」安娜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可笑得比哭都難看。
諮商心理師又「咯咯咯咯」的笑了好一會,安娜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安娜真想離開這個心理諮商室(牠和這個諮商心理師一樣奇怪),要不就拿什麼東西砸到諮商心理師的腦袋上──把她的藍蝴蝶砸得稀巴爛才好呢──最好是桌子上的墨水瓶,或者把滿袋的衛生棉扔在諮商心理師臉上,那也會很爽啊!如果真像她所說得那樣──安娜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只要出於真心──那諮商心理師一定不能怪罪安娜,安娜是按照她的吩咐才做了壞事……
但這怎麼可能?哪裡會有這種完全自由的世界?哪裡會有這種做任何事情都不會受到處罰的世界?……安娜學過社會學,知道這只是人們的烏托邦幻想。任何世界都沒有絕對自由,這絕對是個真理!……可是暴躁的安娜真想做點什麼,比如搧諮商心理師一個耳光,或者拔掉她頭上的藍蝴蝶髮夾然後扔到窗外。安娜想了好久,但還是克制住了要做壞事的衝動……
諮商心理師似乎意識到了安娜的不滿,她終於停止了讓人渾身不自在的「咯咯咯咯」聲。諮商心理師安靜下來,但很顯然她還沒調整好心情。一下子,心理諮商室安靜極了,她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只好本能的陷入了呆滯,就像墳墓裡兩具躺了幾千年的木乃伊。窗戶空隙中的那幾縷陽光消失了,小鳥的叫聲也聽不見了。黑鋼筋阻擋住了一切,心理諮商室陷入一片黑暗中。
沉默。她們沉默了好長時間……
2
「好吧,我們現在開始心理諮商。」
不知過了多久,諮商心理師終於開口說話了。安娜睜開雙眼,彷彿剛從睡夢中醒來,她很高興,終於可以不用忍受沉默以及沉默帶來的尷尬了。陽光重新照著小屋,小鳥的清脆的叫聲再度傳來,一切都那麼欣欣向榮……安娜盯著諮商心理師,她也正揉著眼睛呢,看來她也睏極了,安娜發現她頭上的藍蝴蝶髮夾不見了,這也太奇怪了吧,剛才安娜可是瞧得一清二楚啊……
有那麼一會,安娜又聽到諮商心理師「咯咯咯咯」的笑聲,可坐在她對面的諮商心理師嘴巴根本就沒動,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是自己又出現了幻視幻聽的症狀了嗎?這可真夠糟糕的,可剛才的那一切(諮商心理師的臭屁、大段獨白、笑聲和她們的沉默)太像是真的,簡直就是真的!它們真的是真的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是真實還是幻覺?安娜說不清楚,可誰又能說得清楚呢?那個白鬍子老頭能說清楚嗎?也許他可以,但又有誰見過那個白鬍子老頭?……安娜打了一個哈欠。
「妳叫什麼名字?」諮商心理師打開患者病歷表。她的聲音既冰冷又空洞,就像冷漠的機器人。諮商心理師張大嘴巴又打了一個哈欠,她的牙齒閃閃發光,安娜甚至看到了諮商心理師肉紅色的上顎和喉嚨,以及喉嚨連通著的黑暗世界。
「安娜。」安娜有點驚恐,甚至懷疑來這裡是不是個錯誤。
「噢,是安娜.克利斯蒂還是安娜.卡列尼娜?」諮商心理師臉上勉強擠出個笑容,雖然還有點僵硬,但比剛才好多了。
「就安娜。」安娜惱怒的把頭扭到一邊,這個玩笑可不有趣,安娜不喜歡。
「別生氣,我只想逗妳開心。安娜是個好名字,我母親也喜歡這個名字,她給她的一個女兒也取名叫安娜。」
「是嗎?」安娜滿腹煩悶。從小學到大學,她曾有八個同學叫安娜,這還不算三個沒上幾天就輟學的安娜。工作後,安娜對面的同事也叫安娜,結果辦公室的人不知道怎麼稱呼她們,只好在她們的名字前加上各種代號,如「湖南安娜」或「河南安娜」,「北大安娜」或「清華安娜」,要不就是「大安娜」和「小安娜」,而私下裡他們會叫「醜安娜」和「美安娜」,「暴躁安娜」和「和善安娜」。
安娜討厭死對面那個安娜了,她想,對面那個安娜也一定討厭死她了。(她們共用一個辦公桌,每天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她們同叫這個名字,這個名字卻不屬於她們,無論她們想什麼辦法,都不能掙脫它的控制。(安娜曾經嘗試去警察局修改自己的名字,但因為修改一個人的名字,需要上報十幾道手續。為了提高做事效率減少工作量,很自然,警察局拒絕了安娜的要求。)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安娜們一定會離開這個辦公室,但現在失業率這麼高,她們誰也不敢冒險離開。
「妳也叫安娜嗎?」安娜問。
「噢。不,那是我妹妹的名字,我叫李娜。」
「噢。」安娜看到諮商心理師胸前的卡片,上面果然寫著「李娜」兩個字。安娜有點失望。
「噢。安娜妹妹,別害怕,就當我是妳的姐姐吧──妳知道,我在這裡工作,十分思念老家的安娜妹妹!今天遇到妳,我高興極了,這一定是老天的安排!來,安娜好妹妹,告訴我妳遇到了什麼問題,姐姐一定會幫妳度過難關!」諮商心理師的聲音中透出別樣的溫柔。
幾塊陽光照在安娜的背上,安娜很高興,就像他鄉遇到故友。「我能告訴妳一切嗎?」安娜緊緊的握著諮商心理師的手。
「當然。只要妳願意。」諮商心理師眨了下眼睛,彷彿她們在共同面對一個祕密。她笑得那麼親切(可不是那種職業微笑),安娜感動得都要哭了。
「妳知道在北京一個人生活和打拚有多難,有多不容易!我一個人離鄉背井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努力用自己的雙手去奮鬥,老天爺知道我有多勤奮,我認真讀書,努力考試,辛苦學習,參加比賽,贏取學校的各種榮譽,畢業後又是費盡千心萬苦去找工作。妳知道嗎?我,我……」安娜激動得語無倫次。
「怎麼了?別急,別急,親愛的小妹妹,妳慢慢說,慢慢告訴姐姐。」
諮商心理師回握著安娜的小手,她握得那麼緊。安娜嚎啕大哭起來。諮商心理師給安娜遞來面紙,她也哭起來。諮商心理師取下金框眼鏡,擦掉眼淚。安娜很滿足,在這個荒漠都市,能陪著一塊哭泣的人可不多。
「安娜,妳受了什麼委屈?給我說說,我一定幫妳出主意!」過了好一會,諮商心理師接著問起來。安娜穩定了下情緒,向諮商心理師娓娓道來自己的遭遇。
她這麼信任她,她可不能辜負了她。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安娜的心理諮商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安娜的心理諮商
《安娜的心理諮商》小說╳戲劇劇本全本╳演出後記
安娜在諮商室裡講述自己的故事
李娜在她的故事中發現自己的身影
安娜,有時候我感覺妳就是我,我就是妳,
我們是切成兩半的蘋果,被撕開的連體嬰兒……
有一天,安娜闖進心理諮商室,接待她的是諮商師李娜。
一開始安娜心存戒備,但在李娜的層層誘導下,
安娜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大學生活、和孫娜的情感糾葛、新同事安娜、辦公室生涯……
她並不知道,她正掉進一個可怕的陷阱中──
【小說】
「來,說出妳的故事!」
妳可以把這裡當成……當成妳的家
安娜:患者
李娜:心理諮商師
安娜與李娜兩人之間有著很深的連結,
卻又包含著狂躁的渴望與不為人知的陰謀。
在詩意、瘋狂和壓抑的背後,
作者藉由本書試圖探討安娜的悲劇根源;
試圖在時代進程和個人命運中尋找某種關聯。
【劇本】
「我們來談談安娜這個名字吧。」
我們共叫一個名字,這名字卻不屬於我們。
無論我們做什麼,都不能掙脫它的控制⋯⋯
安娜:患者
李娜:諮商心理師
孫娜:安娜的大學同學,喜歡安娜
新安娜:安娜的新同事,和安娜是競爭關係。
只有說出妳的故事,妳才知道我是誰……
如果遺忘了妳的故事,我將什麼都不是,
如果遺忘了我的故事,妳每天的生活就是行屍走肉,
沒有了故事,也就沒有了我,沒有了妳。
90分鐘的戲劇,在生命中留下或深或淺的漣漪,
慢慢消失時間的長河中──
作者簡介:
劉紅卿,政治學碩士、戲劇美學博士。喜歡寫作和電影,著有多部話劇並於劇場上演。在劇本創作中崇尚意識流風格,在劇本內容和形式上喜歡做多種探索,主要關注的主題是:兒童戲劇、意識流、情色、暴政、現實生活中的悲劇、生存中的心理困境等,想要創造出更多美的作品,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章節試閱
1
週四上午,患者安娜走進心理諮商室。她很高興,值班的是個女諮商心理師。像其他諮商心理師那樣,她穿著白色的工作服(類似於外科醫生的那種醫師袍),戴著一副金框眼鏡,年約三十五歲。她正處在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成熟、理性、睿智卻又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安娜不再驚慌害怕了,諮商心理師將會理解安娜的尷尬處境,她會想出多種辦法解決安娜的人生難題。也許,安娜沉重的心理包袱就能卸下了。她會輕鬆的呼吸,甚至像許多正常人一樣,能在花園裡奔跑歌唱了。
也許這是個新的開始,安娜對自己說。諮商心理師微微的皺了下眉頭,馬上就裝...
週四上午,患者安娜走進心理諮商室。她很高興,值班的是個女諮商心理師。像其他諮商心理師那樣,她穿著白色的工作服(類似於外科醫生的那種醫師袍),戴著一副金框眼鏡,年約三十五歲。她正處在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成熟、理性、睿智卻又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安娜不再驚慌害怕了,諮商心理師將會理解安娜的尷尬處境,她會想出多種辦法解決安娜的人生難題。也許,安娜沉重的心理包袱就能卸下了。她會輕鬆的呼吸,甚至像許多正常人一樣,能在花園裡奔跑歌唱了。
也許這是個新的開始,安娜對自己說。諮商心理師微微的皺了下眉頭,馬上就裝...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安娜的心理諮商》小說
《安娜的心理諮商》戲劇劇本全本
《安娜的心理諮商》戲劇劇本簡版
《安娜的心理諮商》戲劇演出後記
《安娜的心理諮商》戲劇劇本全本
《安娜的心理諮商》戲劇劇本簡版
《安娜的心理諮商》戲劇演出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