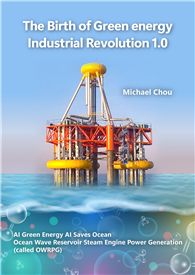第一章 書籤與花
1
那個人很愛惜書本。
像是對待易碎物一樣,輕輕地把書還回放學後的圖書室。
書本還回來時,我正在寫催討單。我們學校圖書室的使用者不多,借書逾期不還的人卻很多,寫催討單時必須一再地對照名單,所以我沒注意到那個人走過來。
依照這間圖書室的規矩,還書時只要放進還書箱就好了,還書箱是沒有蓋子的。我不知道察覺到了什麼,或許是人的存在感,又或許是書本碰觸箱子的聲音,搞不好是衣服摩擦的聲音,總之當我抬起頭時,原本空無一物的還書箱裡出現了一本書。
除此之外,有個人正從敞開通風的門走出去。我只是稍微瞥見穿著我們學校水手服的那個人的背影。
我放學後一直在寫催討單,寫得都有點煩了,所以我暫停工作,望向還書箱裡的書本。
那是一本很漂亮、看起來有點眼熟的普通尺寸精裝本,封面插畫是沒有用到透視技法的古典畫風繪製的建築物,有點像中東風格,或是歐洲風格,或是這世上沒有的風格。背景有很多橘色的三角形,看起來像是尖塔,又像是樹林。一位黑翅膀的天使飛在建築物上方,手往下伸出。書很厚,印在左上角的書名是《玫瑰的名字》,這本是下集。
作者是安伯托.艾可。我記得這套書不是上中下三集,而是上下兩集。我沒讀過這本書,但我看過電影,那是個可怕的故事,描述一個連擁有感情都得有理由和正當性的世界。不知為何,我沒有立刻拿起那本書,而是打算晚點再放回書架上。
圖書室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人,不過這種情況並不稀奇。我嘆了一口氣,繼續寫催討單。
書本外借記錄由電腦管理,誰在何時借了什麼書,是否逾期,全都存在檔案裡。但是,沒人能看到這些資料,因為一個人需要的書能反映出他的內心,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偷窺。話雖如此,若是有人借書不還就麻煩了,必須知道誰借了書才有辦法催討,這就是矛盾之處。
我目前正看著螢幕上列出的逾期清單,裡面只寫了「人名」、「逾期日數」、「借書數量」,沒有寫出「書名」,圖書委員會依照這份清單來寫催討單。
其實不是每天都要寫很多催討單,遺憾的是我們的圖書委員會很散漫,工作老是拖延,往往累積了一大堆逾期清單沒催討,所以發現工作累積很多的人只好一口氣寫完幾天份的催討單,就像我今天的情況。
這項工作很麻煩,雖說只是把螢幕上的資料抄到單子上,但電腦在櫃台後方,而且那邊沒有寫字的空間,必須轉頭看螢幕上的資料再轉回來寫單子,我今天已經不知道在螢幕和工作區之間轉來轉去多少次了。如果能把逾期清單列印出來就輕鬆多了,但司書老師不同意這種做法,說是「螢幕上就看得到,列印出來太浪費紙張了」。原來我們的辛勞連一張紙都不值。
後來我想出了兩人合作寫催討單的方法,就是一個人坐在螢幕前讀出清單,另一個人抄在單子上。發明這種方法後,我和另一個人不到一個小時就解決了累積的工作,結果圖書委員會達成了一致的共識:「催討單都交給堀川次郎去寫就好了」。發明效率高的方法反而增加了工作量,聽起來很沒道理,但我也沒有多排斥就是了,反正只要有兩個人就能輕鬆解決。
可是,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我看看牆上的時鐘。我一放學就來到圖書室,至今過了將近一個小時。我放下原子筆,大大伸了個懶腰,喃喃地說:
「好慢啊。」
放學後有兩位圖書委員一起值班,今天是我和高一的植田登值班。說得更準確點,經常和我搭檔的圖書委員將近兩個月沒來圖書室了,所以才由植田代替。不過,今天連植田都沒來,所以我寫催討單的效率才會如此低迷。
我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本來要打給植田,想想還是不打了。植田不是沒有責任感的人,他沒來一定是有要事處理。就算他沒事,只是突然厭倦了放學後來當沒有酬勞的圖書委員,那也很正常。
催討單不必在今天之內全部寫完,借書櫃台上還有堆積如山的工作,像是新書的上架程序,圖書室通訊的文稿,還有張貼獎學金海報,但那不單單是我和植田的責任,而是全體圖書委員的工作。我把手機放回口袋。
風吹了進來。現在是二月。
今年的冬天不太冷,但傍晚時分的風還是有點涼。圖書室裡很容易積灰塵,放學後一定要打開門窗通風,現在已經通得差不多了。我走出櫃台去關窗戶。
窗外的北八王子市瀰漫著黃昏的氣氛,足球社在操場上練習,不時傳來踢球的鈍響。旁邊有其他社團的人在跑步。所有人都沒出聲。因為我們學校位於住宅區,如果運動社團大聲吆喝,附近鄰居就會抗議。
我呆呆望著窗外時覺得越來越冷,於是關起窗戶,上了鎖,把原本打開通風的窗簾緊緊闔起,防止紫外線照進來。二月的陽光雖弱,但紫外線可是書本的大敵。
我轉過身,看見櫃台裡坐著一位男學生。
那人五官深邃,嘴角掛著揶揄的笑容,像是把櫃台當成自己的地盤,大剌剌地坐在那裡翻著新採購的書籍。他發現我在看他,就闔起書本,輕輕抬手。
「嗨,堀川次郎。」
我也抬起一隻手回答:
「嗨,松倉詩門。你未免遲到太久了。」
「遲到嗎……」
松倉喃喃說著,露出苦笑。
「是啊,我遲到了。抱歉。」
「本來是植田要來,不過他也沒來。」
「我跟他換班了。還是植田比較好?」
不好說。
「他工作還不太熟練。」
「的確,可是不多多練習就不會進步。真是個兩難的老問題。」
松倉看了看堆在櫃台上的書本和紙張。
「你們累積了不少工作呢。」
我非糾正他不可。
「不是我們累積的,是被累積的。」
「真慘。」
我本想說「都是因為你沒來才累積這麼多」,結果還是沒說。松倉自己應該心知肚明,而且圖書委員會也太過依賴我們兩人的工作能力了。
松倉詩門和我都是高二,但是我們沒有同班過。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四月的圖書委員會會議,當時的委員會沒有正常運作,圖書室形同圖書委員的遊樂場,委員們自己鬧翻天,其他學生根本沒辦法安靜看書。面對這個情況,我和松倉既沒有強硬制止,也沒有跟著玩鬧,只是安分守己地做自己的工作。
導致圖書室變成私人場所的高三生已經退出委員會,圖書室漸漸恢復了平靜,我們兩人的態度還是一如往常。就算我誇口本校圖書室能順利地運作至今,都得歸功於我和松倉一直勤勉不懈地處理雜務,也不算言過其實。
松倉指著我寫到一半的催討單。
「要先做完這個嗎?我需要重新熟悉狀況。誰負責念?」
我不知道松倉是明知故問,還是真的生疏了。以前我們合作寫催討單,都是我負責念,松倉負責寫。松倉寫字比我漂亮多了。
「老樣子。」
聽到我這麼說,松倉不加思索地拿起筆,我則是把椅子搬到松倉背後的電腦螢幕前。
「好,來吧。你寫到哪裡了?」
「二年一班,佐田桃,兩本。」
「OK。從下一個開始。」
「一年三班,Aoki Masamichi。青綠的青,樹木的木,正確道路的正道。一本。」
松倉照我說的寫在單子上。
「下一個。」
「二年四班,Takamoto Yuuri。高低的高,書本的本,悠然自得的悠,示部的ri。」
「示部?」
「啊……是衣部。」
「衣部的ri?我還是想不出來……」
松倉舉起筆在半空揮動,彷彿在畫魔法陣。
「其實我也想不起來悠然自得的悠要怎麼寫。太失敗了。」
「去查字典吧。」
我一邊說,一邊在手邊的紙寫上「悠裡」交給松倉,他露出不甘心的表情。(譯註:在日文中,「裡」不是常用漢字。)
「如果你說是『背地裡』的裡,那我就知道了。」
他不服氣地說道。
「真的嗎?」
「不,假的。繼續吧。」
幹嘛扯這種謊啊……
兩人合力工作非常輕鬆,我們不到五分鐘就寫完了催討單。松倉拿起整疊單子,啪沙啪沙地揮動。
「圖書室明明都沒人來,催討單卻這麼多。這是不是違反了什麼質量守恆定律啊?」
「來的人雖少,但毫無例外地全都逾期了。」
「這樣會導出性惡論喔。」
我真想說「你早就是性惡論的擁護者了」,結果還是沒說,這種話不太適合拿來抬槓。從去年十一月底開始,松倉都沒再來圖書室值班,所有圖書委員都很意外,因為松倉從來不曾翹班。他在排班表上造成的空缺由幾位圖書委員輪流補上,最近漸漸固定由植田代替。也就是說,植田現在負擔了兩人份的班次。
我知道松倉為什麼不來圖書室。
因為他有問題需要解決,有選項需要考慮。雖然沒有實際確認過,但我猜松倉不只沒來值班,甚至連學校都沒來。如果他把圖書委員的工作和上學擺在自己的問題之後,我也不覺得意外。
現在松倉詩門又出現在圖書室。他是不是已經找到答案了?他的答案是什麼?我很想問松倉「那件事後來怎麼樣了」。
可是,我也說不出這句話。早在去年十一月的那一夜,我就決定不再插手松倉私人的事,如今再去打聽結果,未免太厚臉皮了。
所以我只是從松倉手中拿回整疊催討單,說道:
「繼續做事吧。」
松倉聳聳肩,露出笑容。
「言之有理。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望向櫃台,有一些書本需要圖書委員來處理。新買的書,破損的書,還有弄髒的書。要先處理的應該是……
「先處理歸還書籍吧。」
歸還的書本要放回書架上,這是圖書室最基本的工作。
還書箱裡只有剛才放進來的《玫瑰的名字》下集,要放回書架的書不只這一本,圖書室裡有一個附輪子的活動櫃,裡面堆滿了歸還書籍。松倉看著活動櫃,露出厭煩的表情。
「這裡也積了這麼多。」
活動櫃不是用來放書的地方,而是用來把書本放回架上的移動工作台,活動櫃堆滿書本就代表這幾天值班的圖書委員都沒有把書歸位。松倉用視線默數書的數量。
「大概有二十本。」
根據我的經驗,歸還書籍累積到二十本,就表示圖書委員已經偷懶了兩三天。很遺憾,這種情況早就司空見慣了。
松倉聳了聳肩膀。
「那就做吧。我不討厭歸位的工作。」
「我懂。」
該怎麼說呢?把東西放回該放的地方確實挺愉快的。
要把借書者歸還的書本放回架上有兩個步驟,首先要掃描貼在書上的條碼,把電腦資料的書籍狀態從「借出」改成「在架」,接著才是把書放回書架。堆在活動櫃裡的書應該已經改好資料了,接下來只要依照貼在書脊上的分類號放回原本的位置。
松倉走出櫃台,從活動櫃裡拿出最近的一本書。我看見封面寫著「馬克士威的惡魔」。松倉停止動作,轉頭看我。
「檢查過了嗎?」
「……喔,對耶。不知道檢查了沒。」
檢查不是圖書委員的專業術語,但我知道松倉要表達的意思。
還回圖書室的書本經常夾著東西,最常見的是市面販售的文庫本附贈的書籤,便利商店之類的收據也不少,還有人把升學意向調查表夾在書裡,我有一次甚至在書裡發現了千圓大鈔,後來交給司書老師了。
就算書裡沒有夾東西,也可能會發現塗鴉或髒汙。只要把歸還的書本迅速地翻一遍,就能免去很多麻煩,可是圖書委員不知為何經常疏忽這個步驟。要是問我這些書被放進活動櫃之前有沒有檢查過,我還真不敢保證。
松倉單手從活動櫃裡抽出幾本書遞給我。
「檢查一下吧。」
「也好。」
活動櫃裡的書有一半是小說,另一半是升學相關書籍、科學讀物、知識類書刊等等五花八門的書,甚至還有保養機車的書。一般高中的圖書室為什麼會有這種書呢?
第一本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我在快速檢查時無意翻到某一頁,裡面寫著「單個肉體變成了一種可以被安置、移動及與其它肉體結合的因素」這種讓人似懂非懂的句子。我之所以會翻到這一頁,是因為裡面夾著集點卡。我拿出集點卡,舉向松倉。
「裡面有東西。『排排站』?該怎麼說呢,好像是會讓人很累的店。」
我喃喃說道,松倉朝我的手上瞥了一眼。
「你不知道嗎?沒想到我們學校裡竟然有人不知道『排排站』。」
「你一定也不知道。」
「你猜錯了。那是賣炸豬排的店。」
「好吃嗎?」
「我又沒吃過。」
那就等於不知道嘛。
集點卡註明集滿二十點就能折價五百圓,這張已經集了十七點。可想而知,丟了這張集點卡的人一定會非常懊惱。我把卡片丟進失物盒,一個不知從何時開始放在這裡的餅乾鐵盒。
沒過多久,松倉從《產婆蟾之謎》中拿出一張紙片。
「大豐收,我也找到了。」
那張紙像是從影印紙撕下來的,上面寫著一些數字,大概是電話號碼。這張紙也被丟進了失物盒。
我們三兩下就檢查完活動櫃裡的書本,接著要把書放回架上。我本來這樣想,卻突然想起還有一本,就是還書箱裡僅有的《玫瑰的名字》下集。
「我都忘了,還有這本。」
這本書還沒更改書籍狀態。我用讀碼器掃描書上的條碼,完成資料上的還書程序。松倉看到我手上的《玫瑰的名字》下集,探出身子說:
「《玫瑰的名字》?有人借這麼厲害的書啊?」
「你看過嗎?」
「看過電影。」
果然是我的好搭檔。
松倉從我手上拿走《玫瑰的名字》下集,快速地翻閱。看到他這麼隨性的動作,我忍不住出言提醒。
「這可是推理小說,別先看結局喔。」
松倉漫不經心地回答:
「知道啦。」
他繼續翻閱,但很快就停下來,用食指和中指夾起某樣東西。松倉笑著說:
「還好有檢查,光是今天就找到三件呢。」
夾在他手指間的是書籤,裡面有朵漂亮的花。我說:
「這是今天找到的失物中最適合夾在書裡的東西。」
松倉把書籤放在櫃台上。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書籤與謊言的季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日本推理/犯罪小說 |
$ 300 |
日本推理小說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推理小說 |
$ 342 |
文學作品 |
$ 342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書籤與謊言的季節
「堀川和松倉這兩位高中生,
有時看看書,有時解解謎,
就這樣漸漸了解彼此,
也了解到彼此都有看不到的部分。
希望大家會喜歡。」
──作者/米澤穗信
銷售量突破25萬本!(圖書委員系列)
《書與鑰匙的季節》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續集
★史上第一位推理年度排行榜四冠王暨直木獎得主,青春推理的巔峰之作。
【故事簡介】
圍繞著劇毒書籤的層層謊言。
圖書委員堀川次郎和松倉詩門在圖書室的歸還書籍中發現烏頭花的書籤,又發現校舍後面種了烏頭,最後終於出現了受害者……
兩人和自稱書籤所有者的女學生瀨野一起調查真相。
殺意背後隱藏著動人心弦的感情。青春推理長篇小說。
【登場人物簡介】
堀川次郎(Horikawa Jirou)
高二。圖書委員。
成績頗優秀。
經常被人求助。
松倉詩門(Matsukura Simon)
高二。圖書委員。
課業和運動都很厲害,手卻有點笨拙。
不喜歡自己的名字。
作者簡介:
米澤穗信
一九七八年出生於岐阜縣。二○○一年以《冰菓》獲得第五回角川學園小說大賞獎勵賞(青少年推理&恐怖小說部門)而出道。他兼具青春小說魅力與解謎趣味的作風受到矚目,在發表《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等作品之後奠定人氣作家的地位。
得獎紀錄:
2011年《折斷的龍骨》獲得第六十四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
2014年《滿願》獲得第二十七回山本周五郎賞。同時得到三項年度推理小說排行榜冠軍。
2015年《王與馬戲團》史上首位連續兩年獲得三項年度推理小說排行榜冠軍,入選本屋大賞。
2017年《真相的十公尺前》蟬聯「這本推理小說好想讀!」第一名。
2022年《黑牢城》獲得第十二回山田風太郎賞、第一六六回直木賞。同時得到當年度四大推理小說排行榜冠軍。
另有《再見,妖精》、《尋狗事務所》、《追想五斷章》、《書與鑰匙的季節》、《黑牢城》等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書籤與花
1
那個人很愛惜書本。
像是對待易碎物一樣,輕輕地把書還回放學後的圖書室。
書本還回來時,我正在寫催討單。我們學校圖書室的使用者不多,借書逾期不還的人卻很多,寫催討單時必須一再地對照名單,所以我沒注意到那個人走過來。
依照這間圖書室的規矩,還書時只要放進還書箱就好了,還書箱是沒有蓋子的。我不知道察覺到了什麼,或許是人的存在感,又或許是書本碰觸箱子的聲音,搞不好是衣服摩擦的聲音,總之當我抬起頭時,原本空無一物的還書箱裡出現了一本書。
除此之外,有個人正從敞開通風的門走出去。我...
1
那個人很愛惜書本。
像是對待易碎物一樣,輕輕地把書還回放學後的圖書室。
書本還回來時,我正在寫催討單。我們學校圖書室的使用者不多,借書逾期不還的人卻很多,寫催討單時必須一再地對照名單,所以我沒注意到那個人走過來。
依照這間圖書室的規矩,還書時只要放進還書箱就好了,還書箱是沒有蓋子的。我不知道察覺到了什麼,或許是人的存在感,又或許是書本碰觸箱子的聲音,搞不好是衣服摩擦的聲音,總之當我抬起頭時,原本空無一物的還書箱裡出現了一本書。
除此之外,有個人正從敞開通風的門走出去。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書籤與花
第二章 書籤與毒
第三章 書籤與流言
第四章 書籤與謊言
第二章 書籤與毒
第三章 書籤與流言
第四章 書籤與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