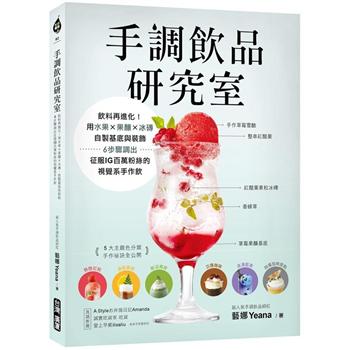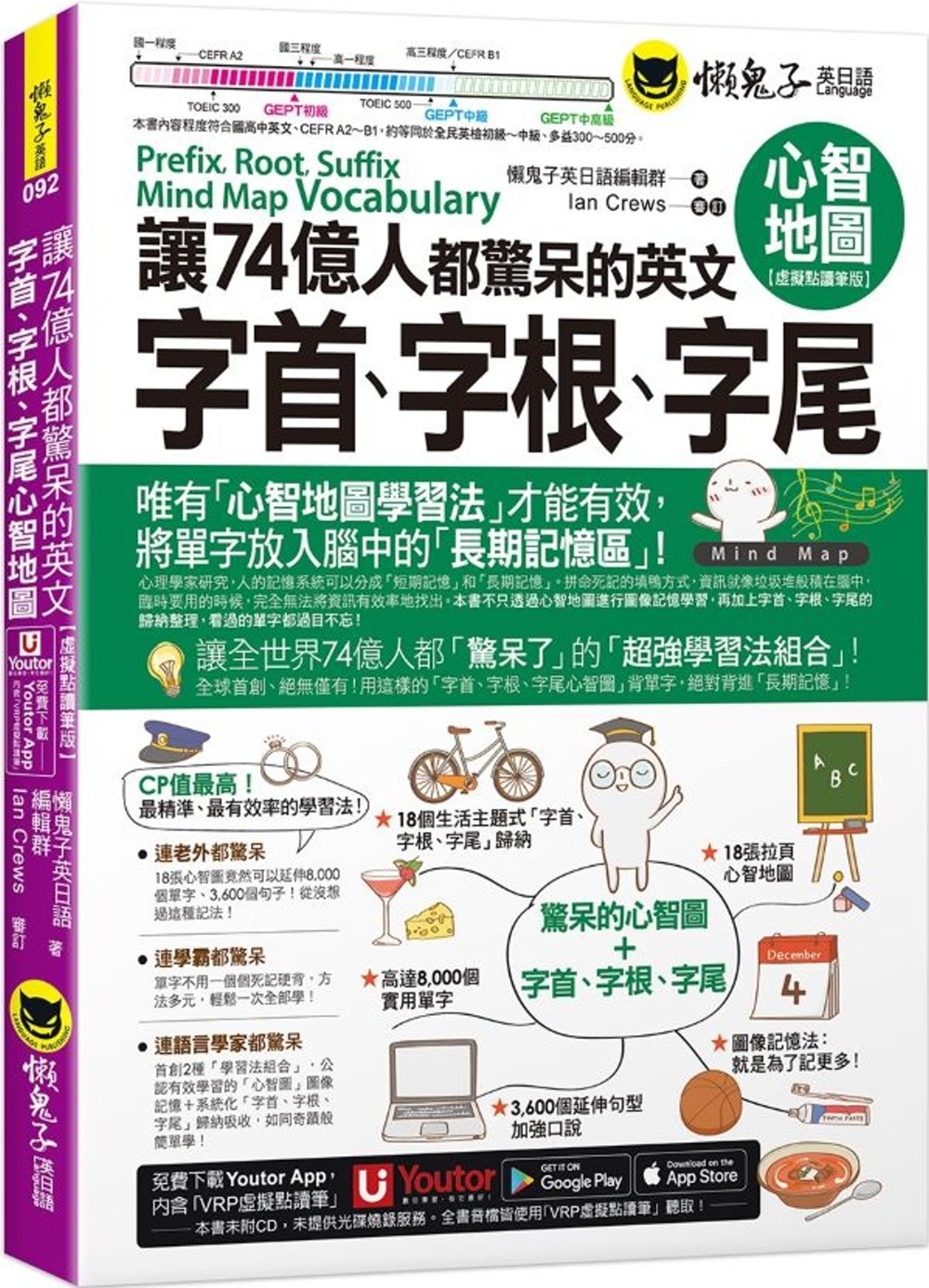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為解放而戰的青蛙們,唯有蹲坐在陰暗的半個椰殼底下不動才會失敗。
全世界的青蛙團結起來!」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學術人生自述
是什麼樣的社會、政治、文化與時代背景,孕育、教育並養成了《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的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班納迪克.安德森終其一生都在挑戰他那個時代的紀律、文化、學術和政治的界限。在《椰殼碗外的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這本書裡,他記述自己人生中智識形成的歷程,如何迎向寬廣的世界,從中感受探索學習語言的樂趣,以及田野調查的重要性、新左派對全球思維的影響力、教書帶來的滿足感和對世界文學的熱愛。安德森同時在書中敘述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流產政變後,他揭發軍方所扮演的角色,結果遭到蘇哈托政權驅逐出境。此外,他也重溫自己最知名,改變了民族主義研究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背後的構思與靈感。
二○一五年安德森修改完本書的校樣後不久,便在爪哇與世長辭,旋即從亞洲湧來大量向他致敬的悼文,顯示安德森的作品將會繼續啟發和鼓舞年輕與年長世代的心靈。
媒體評論
「本書以特有的魅力與文學美感,記述一位當代極受仰慕的學者的智識軌跡。」——古哈(Ramachandra Guha),《泰唔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迷人而低調的回憶錄。作者心酸的表示他對於自己的成就感到多麼幸運。我們都應該感同身受。」——《展望》雜誌(Prospect Magazine)
「安德森是舒適圈的敵人,不論國家、學校或語言皆是如此。他反覆再三的提到泰國和印尼文化的一個意象,也就是一輩子住在半個椰子殼下的青蛙。閱讀安德森的書讓人產生從椰子殼裡探出頭來的感覺。」——《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
「安德森的寫作充滿紳士味,仁善,還點綴著笑話——他這種非正式、易閱讀、跨學科的寫作風格一如既往贏得多方喝采。」——《衛報》(Guardian)
「世紀主義的入門書,提供跨越地理、歷史、語言、學科邊界的主張。」——《國家》雜誌(Nation)
「安德森大大改變了民族主義研究…他響亮的名聲不僅來自理論方面的貢獻,更來自鉅細靡遺的深研印尼、泰國、菲律賓的語言和權力。」——《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安德森所寫的每一件事物,都是藉由揭露受忽視者或受壓制者的聲音,提出大膽的原創性、挑戰性假設。他從不滿意迎合聽眾,不肯只說對方想聽的話。」——《衛報》(Guardian)
作者簡介: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
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為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著有《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比較的鬼魂: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美國殖民時期之暹羅政治與文學》(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的想像》(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譯者簡介:
李宛蓉:
主修新聞、大傳,從事翻譯工作30餘年,已出版譯作60餘本。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漂泊的年少時光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在雲南昆明出生,時值日本對中國北方發動大規模侵略的前夕,短短三年之後,歐洲便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一年夏天,就在我快滿五週歲的時候,生病的父親決定帶全家人取道美國返回維持中立的愛爾蘭。
然而我們搭乘的船在舊金山碼頭靠岸後,父親才明白當時大西洋上潛水艇交戰頻繁,根本沒辦法回老家。於是我們只好待在加州,後來又遷到科羅拉多州(Colorado),直到納粹德國戰敗為止。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搭船前往愛爾蘭,船上依然擠滿了遠赴歐洲戰場的美國士兵。那時候我已經快滿九歲,隔年父親不幸去世,但是英國籍的母親卻決定全家人要繼續待在愛爾蘭。
我就讀小學、中學、學院的那些年適逢冷戰時期,一度無比遼闊的大英帝國也在那段期間迅速崩解。就我的記憶所及,當時冷戰對我的影響並不大,但假如我不是幸運住在愛爾蘭,恐怕十八歲那年(一九五四年)就會被徵召入伍,前去馬來西亞、肯亞或塞浦路斯為垂死的帝國奮戰,結果搞不好就戰死或重傷了。
我的成長歲月也在電視機問世之前,不過我們倒是經常收聽廣播節目——廣播這個媒介可以讓人一邊做家事、做功課、玩牌、下棋,一邊收聽節目作為娛樂。夜裡我們往往轉到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頻道,聽非常傑出的演員高聲朗讀小說巨作,這些節目像連續劇那樣逐集播放,我們的腦中因此充滿對小說人物的想像,譬如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基督山伯爵(Count of Monte Cristo)、吉姆爺(Lord Jim)、烏利亞‧希普(Uriah Heep)、黛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等等。
巡演劇團對我們也非常重要。愛爾蘭到處都是優秀的劇場演員,我們不僅能欣賞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劇(這些劇本後來才被拿來當教科書),也有世界知名的愛爾蘭劇作家撰寫的戲劇,像是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王爾德(Oscar Wilde)、謝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奧凱西(Sean O’Casey)等人。那時候美國大眾文化剛開始抵達愛爾蘭,本地電影院會放映西部片和迪士尼卡通片。
這一切原本可能不會如此演變——假如父親當初因為太平洋戰爭而延後離開中國,最終我們可能都會被關進日軍收容營,也許就死在那裡了。假如父親不是愛爾蘭籍,我可能會在英國長大,然後為了大英帝國去海外參戰。假如我晚一點才出生,可能會沉迷於電視,以致懶得去本地劇院看戲。
我的父母親是了不起的家長,慈愛寬厚,為人風趣,我和弟弟羅瑞〔Rory,如今又以派瑞(Perry)之名著稱〕、小妹美蘭妮(Melanie)都深愛他們;可以說我們兄妹非常幸運擁有這樣的雙親。
父親的大名是謝莫斯.詹姆斯.奧格曼.安德森(Seamus James O’GormanAnderson),他的父母都系出名門。祖母的父系祖先是愛爾蘭人,這從她的娘家姓氏奧格曼(O’Gorman)就看得出來,這個家族有投身政治激進行動的悠久歷史,主要是對抗愛爾蘭境內的英格蘭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一七九八年發生了愛爾蘭起義(United Irishmen rebellion),這是受到法國大革命鼓舞所激發的行動,奧格曼家族的一對兄弟,也就是我的外高祖父和外高叔祖父都參與了,而行動的回報是兩兄弟都進了監獄,在牢裡待了一段時間。一八二○年代,兄弟倆都成為奧康諾(Daniel O’Connell)所創立的「天主教協會」(Catholic Association)的重要成員。「天主教協會」的奮鬥宗旨是,終結百年來社會上佔多數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所遭受的法律、政治、經濟歧視。他們的一個姪子參加一八四八年的叛亂,當時正處在「愛爾蘭馬鈴薯飢荒」水深火熱之際;叛亂失敗之後,這個姪子逃到巴黎,又轉往伊斯坦堡,後來移民美國,最終成為紐約州最高法院的一員。
我父親的外祖父波賽爾.奧格曼少校(Major Purcell O’Gorman)在一八七四年獲選為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的議員,選區位在小城瓦特福(Waterford),他還成為巴奈爾(Charles Parnell)所領導的愛爾蘭自治運動(Home Rule for Ireland bloc)旗下重要的角色(據說他的體重達三百多磅,是議會裡最胖的人),可是他卻娶了一個信奉新教的英格蘭女子。當時社會對異教婚姻還頗為寬容,只是不久之後教宗庇護九世(Pope Pius IX)即位,風氣為之一變。在社會風氣比較寬容的年代,本地法規對於異教徒結婚的問題有個通情達理的解決辦法,那就是兒子信奉父親的宗教,女兒則信奉母親的宗教。因此我的祖母是新教徒,而她的哥哥卻是天主教徒。
再講到我祖父這一支,幾乎是完全相反。祖父家裡是「盎格魯-愛爾蘭」一系,指的是十七世紀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入侵愛爾蘭,奪取本地人的土地,然後在此定居,躋身當地仕紳,他們的後代依然是新教徒,不過世世代代之後,這些子孫覺得自己更像愛爾蘭人。我祖父這一支出了很多軍官,有些在拿破崙戰爭中上了戰場,有些去了阿富汗和緬甸服役,還有些隨著大英帝國的擴張,被派駐香港和印度。
我的盎格魯-愛爾蘭祖父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過世了,他的職業也是大英帝國的陸軍軍官(當年的盎格魯-愛爾蘭家庭是由長子繼承父親的財產,餘下的兒子往往成為教士或軍官。)祖父就讀倫敦沃維奇(Woolwich)的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這所學校專門訓練工程師,他畢業之後先後前往印度、緬甸、馬來亞服役。在派駐檳城(Penang,我父親的誕生地)期間,祖父興建了一座淨水水庫,至今依然正常運作,此外他還建造了一座新式港口。如今站在檳城的高樓上眺望,仍然能看見祖父當年為妻子所設計的愛爾蘭風格屋舍的遺跡,那正是波賽爾.奧格曼少校的女兒,也就是我的祖母。祖父是最早對密碼學感興趣的那批人當中的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成功領導英國陸軍部(War Office)的密碼局。有時候我也感到好奇,自己之所以終身癡迷玩填字遊戲,是不是源自於祖父的基因?
關於先人的這些歷史,有許多是我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才發現的,當時我開始考慮自己該選擇當哪一國的公民,最後選的是愛爾蘭。我小時候旅行用的是母親的英國護照,後來用自己的英國護照,從來沒有多想。長大後知道了人有靈魂和性格,但也很少為自己的身分煩惱。身分的主要關聯是數學,不然就是針對屍體所進行的法醫調查。
我選擇當愛爾蘭公民,除了有政治理由,也有私人因素。當時越戰正打得如火如荼,鄰近的印尼反共黨軍隊奪得權力,屠殺了大約五十萬名共產黨員與同情共黨人士。這些事件使我的左傾情感更加堅定。另一個理由比較私人,由於弟弟妹妹已經決定要保持英國籍,我覺得自己欠父親一個公道,畢竟在我出生時,他給了我奧格曼這個「部族」姓氏,所以我應該申請愛爾蘭國籍才對。
愛爾蘭的公民權並不難取得,前提是我要能證明雙親或祖父母當中,至少有一人是在愛爾蘭出生的(我父親生在祖父駐紮的檳城,母親則生在倫敦。)可惜的是,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在一九一六年發動反抗英國的復活節起義(Easter Uprising),叛軍燒毀存放愛爾蘭出生記錄檔案的建築。所幸我母親有個朋友的嗜好是研究瓦特福郡(County of Waterford)各家族的家譜,他挖掘出前文所述的大部分資料,我將資料拿給本地選出的國會議員看,獲得對方協助,才得以在一九六七年拿到自己的第一本愛爾蘭護照。
第二章 區域研究
事實證明,命運的發展和我原先所預料的大不相同。我很快就深受康乃爾大學美麗的自然風景吸引,而卡欣所教授的印尼、東南亞、美國對亞洲政策的課程也令我傾倒。在康乃爾的第一年結束時,我明白自己終於下定決心追求此生的志願:當教授、做研究、寫書和教書,並且在學術和政治傾向上跟隨卡欣的步伐。後文還會多講一些卡欣的事,他不僅是優秀的學者,更是堅持信念、充滿活力的人。
所以我就這樣待下來了。母親很高興我終於安頓下來,但也抱怨我離開她和弟妹那麼遠,因此我幾乎每星期都寫信給母親,每年耶誕節和暑假也會回家。母親常常給我回信,西麗雅(Celia)姨媽會寄字謎剪報給我,她寄來的字謎通常比美國當地的字謎更難破解。
儘管一到康乃爾就受到卡欣教授的東南亞課程所吸引,但是我花了好幾個月才適應美國研究生的生活,又花了更久的時間,才了解康乃爾大學及其東南亞學程在當時地位多麼獨特。要解釋這種獨特性的本質,就需要暫且放下康乃爾,先說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人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如何乍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美國雖然在全世界積極推動經濟擴張的政策,但骨子裡其實是奉行孤立主義的。世人都記得,儘管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使出渾身解數,美國仍然拒絕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由於美國只擁有一個重要殖民地,也就是菲律賓,加上本身曾經也是殖民地,因此在涉足「歐洲」和日本殖民帝國的競賽時,經常會感到尷尬。到了一九三○年代中期,美國已經訂好一九四六年讓菲律賓獨立的計畫。美國雖然擁有規模龐大的現代化海軍,可是陸軍和空軍力量乏善可陳,直接的政治干預主要限於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主張的自家後院,也就是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部分,以及太平洋的一大塊。美國的學術界也反映這個較大的格局,因為有太多美國人祖上源於歐洲,也因為歐洲的學術界地位崇高,所以很多美國學者研究的國家主要位在西歐——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蘇聯也是學者研究的目標之一,因為該國被視為強大的意識形態敵人。至於亞洲,一般只關心中國和日本,研究日本的主要原因是它握有軍事力量,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獨大的地位。早期學界之所以對中國產生強烈的興趣,是受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大批傳教士前去中國傳道的刺激。到了一九四○年代末期,蔣介石政權瓦解,很多中國學者逃到美國——反動派和自由派不拘,水準頂尖的和平庸的都有,後來大幅提高了反共中國問題研究的影響力。他們和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來的學者不同,許多都帶有特定的政治企圖。這些學者和美國持有類似意識形態觀點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結盟,日後在與亞洲議題相關的美國學術圈形成一個重要的派別,影響力很大。
當時已經有一些關於印度的著作,不過主要限於梵語學生閱讀的書籍,受到歐洲東方主義的影響,而不是關於當代殖民地印度的作品。除了一、兩位人類學者之外,幾乎沒有人研究非洲、中東、中亞或東南亞。正經研究東南亞(菲律賓除外)的專家,一隻手就數得出來: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與葛瑞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研究峇里島(Bali)、珂拉.杜布瓦(Cora Dubois)研究印尼亞羅島(Alor),魯伯特.愛默森(Rupert Emerson)研究馬來亞(Malaya)。遲至一九五八年我開始在康乃爾大學政府系就讀時,為數不多的教師絕大多數都在研究美國。有一位教授負責蘇聯,另一位負責西歐,而卡欣則負責整個亞洲。整個系上都沒有老師教授關於拉丁美洲、東歐、非洲或中東的課。
第二次世界大戰急遽改變了所有事物。美國忽然成為世界霸主,德國和日本徹底戰敗,英國和法國雖然是勝利的一方,卻遭受參戰的代價拖累,昔日世界帝國強權的地位迅速衰落。唯有蘇聯不動如山,但仍然是區域性大國,而不是全球強權。雖然美國先前不肯加入國際聯盟,此時也已成為聯合國的核心組織者,這點從紐約被選為聯合國總部就看得出來。在這些新的情況之下,更多有權有勢的美國菁英分子清楚察覺到,自己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認識少得可憐,畢竟他們如今指望在那些地方的政治局勢中扮演關鍵角色。由於亞洲和不久之後的非洲正以如火如荼的速度推動去殖民化,了解這些國家就變得更迫切了。
戰後美國區域研究的崛起,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新霸權地位。美國開始投入大量財務資源和其他資源,著重研究西歐以外國家的「當代」政治學和經濟學,較少研究其歷史、人類學、社會學、文學、藝術。等到冷戰伊始,學術界對政策研究越來越感興趣,尤其關切他們所理解的「世界共產主義」所構成的真實威脅或想像的威脅。促進學術界這波擴張的背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國防部的推動力。不過極大型私人機構也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一部分的作用是平衡國家的「政策」焦點。
這些基金會的高階人員通常教育水準很高,他們在小羅斯福總統(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漫長的執政期間長大,比國家機關公務員的觀點更偏自由派,也比較不執迷於打擊「世界共產主義」。他們很多都堅信較有深度、以歷史作基礎的學術研究很重要,認為相較國家機構,在開放的大學裡更有可能健全發展這類學術研究。他們也比較注意長期規劃的需求,以及某些議題的急迫性,例如闢建足夠的研究圖書館,以及戰前乏人問津的那些語言種類的教學效率。
西方人眼裡的「東南亞」是什麼樣的?中文自古就有「南洋」一語,這個模糊的地理名詞大概的意思是「南方地區」,而且帶有「水」的意涵,象徵地處北京以南,可以經由河道或海路抵達的南方地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南洋指的可能是中國自己的東南沿海省分,或是菲律賓、印尼群島、馬來半島,但不指只能經由陸路抵達的緬甸和寮國。日文也有同源的用詞「南浦」,是明治時代才有的,在意義上更明確也更政治性,涵蓋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的一大部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受託統治該地。
第一位出於完整現代意識使用「東南亞」這個詞的西方學者,是傑出的緬甸專家約翰.佛尼瓦爾(John Furnivall),他在一九四一年出版了《東南亞的繁榮與進步》(Welfare and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然而決定性的改變,是大戰期間盟軍創造東南亞戰區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由路易.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擔任總司令,宗旨是「解放」美屬菲律賓以外的整個東南亞——至於菲律賓則交由華府處理。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不僅(短暫)恢復英國在緬甸、馬來亞、新加坡殖民,當荷蘭和法國效法英國,分別在當今的印尼和中南半島企圖恢復殖民時,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也扮演類似的襄助角色。儘管如此,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不久,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便廢除了。
「東南亞」這個詞最早是經由美國才定型變成一般用語,像過去的日本一樣,美國的野心也是主宰印度和中國之間這整片地區。過去歐洲諸帝國只要瓜分此地區就已經心滿意足,所以焦點多半放在自己擁有的殖民地上。這項重大的政治改變無可避免的對學術界產生根本的影響。
戰前關於東南亞不同部分的最佳研究,都出自學養深厚的殖民地官僚,而非都會區大學的教授。這些官僚在特定殖民地一住多年,往往通曉當地的當代或古典語文,有時候還會和原住民婦女通婚或外遇(有一小部分官僚是同性戀者,必須盡可能掩飾),他們經常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當作一種嗜好,主要興趣是考古學、音樂、古代文學、歷史。整體來說,這些是他們可以堂而皇之表達希望研究的領域,相對而言,就沒那麼熱衷政治或經濟研究,因為作者通常必須和殖民政權保持一致立場。
最重要的是,學者型官僚一般只研究一個殖民地,也就是自己派駐的那一個,對於其他地方興趣不大,也不了解。撰寫系統性比較研究成果的重要學者佛尼瓦爾,是在離開官僚崗位後才動筆的,他寫的《殖民政策與實務》(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主題是英屬緬甸和荷屬印尼。因此到了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初期,關於東南亞的美國傑出研究作品依然十分稀少,所以我這一輩必須非常仰賴學者型官僚,而且被逼得去學習法語或荷蘭語,才能閱讀他們的作品。我們都閱讀佛尼瓦爾和高爾登.盧斯(Gordon H. Luce)寫的緬甸;保羅.繆伊(Paul Mus)和喬治.賽代斯(George Coedès)寫的中南半島;理察.溫斯泰德(Richard Olof Winstedt)和理察.威爾金遜(Richard James Wilkinson)寫的馬來亞;貝爾特姆.施瑞卡(Bertram Schrieke)、提歐多.琵侯(Theodoor Gautier Thomas Pigeaud)、雅各布.范立爾(Jacob Cornelis van Leur)寫的印尼…(未完)
第一章 漂泊的年少時光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在雲南昆明出生,時值日本對中國北方發動大規模侵略的前夕,短短三年之後,歐洲便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一年夏天,就在我快滿五週歲的時候,生病的父親決定帶全家人取道美國返回維持中立的愛爾蘭。
然而我們搭乘的船在舊金山碼頭靠岸後,父親才明白當時大西洋上潛水艇交戰頻繁,根本沒辦法回老家。於是我們只好待在加州,後來又遷到科羅拉多州(Colorado),直到納粹德國戰敗為止。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搭船前往愛爾蘭,船上依然擠滿了遠赴歐洲戰場的美國士兵。那時候我已經...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漂泊的年少時光
第二章區域研究
第三章田野調查
第四章比較的架構
第五章跨學科研究
第六章退休與解放
後記
導言
第一章 漂泊的年少時光
第二章區域研究
第三章田野調查
第四章比較的架構
第五章跨學科研究
第六章退休與解放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