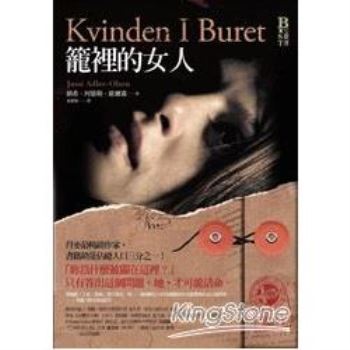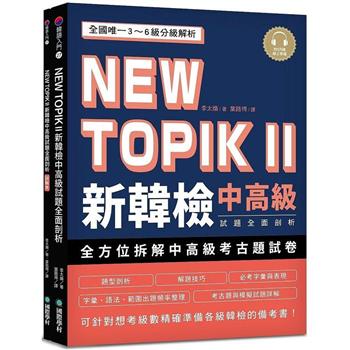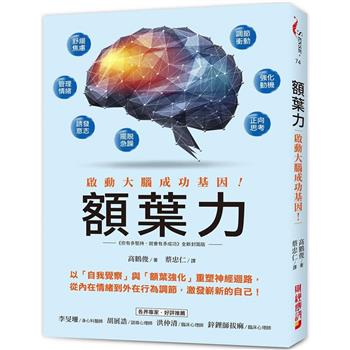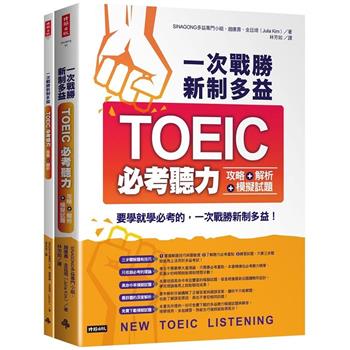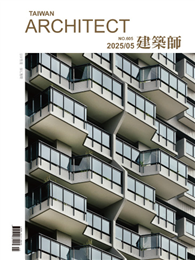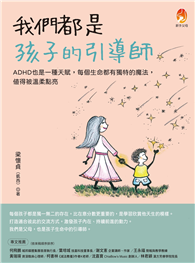追尋文化脈絡,解讀遠古傳承
重返歷史現場
帶領讀者見證華夏文明的誕生與成長
⚑ 華夏文明的發祥之地
本書探討了華夏文明的起源,從考古證據和歷史資料中揭示其早期形成的過程。作者指出,華夏文明作為人類四大古文明之一,與尼羅河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一樣,擁有顯著的農耕特色和沿河流域的發展特點。透過對比四大文明的地理和文化特徵,書中強調了華夏文明的獨特性。
⚑ 地理條件
書中詳細分析了華夏文明發祥地的自然地理條件,包括肥沃的黃土地、適宜的氣候、豐富的水源和植被,這些為農業的興起和人類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礎。當地的地形特點,如天然屏障和通道的結合,既保護了原生文化,又促進了與外界的交流,形成了開放與封閉相結合的文化地理格局。
⚑ 歷史演進
作者梳理了從仰韶文化到陶寺文化的過渡,並分析了各階段的重要考古發現,例如彩陶文化的發展及其對民族認同的塑造。陶寺文化的形成被視為華夏文明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其展現了社會階層分化、城市規劃和初步的禮樂制度。
⚑ 軸心地位
書中引用了多位考古學家的研究,認為華夏文明的發展路徑展示了「軸根系」的特性,即其核心地區在整個文明起源中的突出地位。從陶器和玉器的技術提升到青銅器的發明,這一區域的文化特徵對後來的夏、商、周三代影響深遠,成為中華文明的基石。
⚑ 華夏與中華
書中深入探討了華夏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概念差異。作者指出,華夏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部分,在其後來的演化中吸納了周邊多元文化,逐步形成了以華夏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明。這種文化融合促進了早期國家的形成和社會結構的複雜化。
⚑ 開端與傳承
全書在論述華夏文明起源的同時,也強調了這一文明對歷史和文化的深遠影響。作者以豐富的考古資料和嚴謹的學術分析,展現了華夏文明如何從分散的部落文化逐步演進為完整的文明體系,並最終奠定了文化根基。
本書特色:本書以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為基礎,探討華夏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展現從遠古文化到早期文明的演進。作者分析自然地理、文化與技術進步,強調多元文化交融對國家形成的影響,提出華夏文明作為中華文化核心的歷史意義與延續性,內容詳實,視角獨到。
作者簡介:
杜學文,長期從事文藝評論及文化理論、文明史研究,已發表研究成果300多萬字。出版有文藝評論著作《藝術的精神》、《中國審美與中國精神》等;文明史研究著作《我們的文明》、《被遮蔽的文明》等;主編的作品有《聚焦山西電影》、《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山西抗戰文學》、《劉慈欣現象觀察》等。
章節試閱
第三節 石器時代的山西
在我們討論了人類進化的過程之後,發現山西在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顯現了中國具有人類形成的獨立性。特別是在垣曲一帶發現的世紀曙猿、西侯度與匼河發現的人類用火遺存以及丁村發現的古人類化石等,均具有文化上的連續性、一致性。以大三稜尖狀器為代表的舊石器在這些遺址中均有存在,鏟形齒的存在也證明了這些地區具有人種意義上的獨立性與一致性,且這種文化上的一致性表現得非常典型。
那麼,什麼是舊石器時代?是不是還有新石器時代呢?我們知道,石器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最早使用的勞動工具,也是當時人類能夠製造的最先進的工具。由於人類掌握的技術手段不同,石器的製造方法也不同。在早期,人類只會採用擊打的方法來製造石器。隨著技術的進步,人類逐漸在擊打的基礎上學會磨製技術,使這些石器工具的功能更加突顯、更好使用。當人們還只會用擊打的方法製造石器工具時,就被認為是處於舊石器時代,一旦能夠用磨製的方法製造石器,就進入了新石器時代。儘管不同地域的人們掌握的製造方法並不一致,存在或先或後的問題,但一般而言,在距今300萬年至1萬多年的時期內,人類主要使用打製石器,處於舊石器時代;在距今1萬餘年至距今5,000餘年到2,000餘年的時期內,人類普遍使用磨製石器,處於新石器時代。由於各地技術發展不同,使用石器的情況也不同,我們還不能絕對地以時間來劃分新舊兩個石器時代,但大致來說可以分為這樣兩個時期。
在舊石器時代,人類製造工具的能力還比較簡單,石器是最主要的工具。這一時期,人類已經能夠使用火,這是一次人類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技術革命,代表著人類由生食階段進入了熟食階段,對人的體能、智慧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此外,這一時期的人類仍然依靠採摘技術獲取植物果實,依靠捕獵來獲取動物充飢,開始使用弓箭等新的工具。這一時期出現了簡單的藝術形式,人類對審美有了原始的意識。進入新石器時代,製造技術快速進步,磨製的方法使石製工具更為理想化、精細化;農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開始由採摘向種植轉化;磨製食物的技術也得到了普及,製陶技術得到發展,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青銅器;審美更為普遍,出現了某種具有信仰意義的色彩與圖案以及比較複雜的裝飾。
與丁村文化存在的時間大致相當,在山西北部大同陽高縣的許家窯發現了距今約1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其中發現了許多動物殘骸以及十多個人類個體的化石遺存。經研究發現,這些人類化石具有形成演化的獨立性。此外,許家窯還發現了大量的石器工具,其最大的特點是細小石器的出現,直接影響了之後發現的峙峪文化。峙峪遺址大約距今2.8萬年,位於朔州桑乾河流域,最早由賈蘭坡先生等主持挖掘。在這裡,人們發現了人類枕骨化石、石墨裝飾品。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發現了大量的動物化石,其中,馬、驢類草食性動物占絕大多數。這在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中極為少見。峙峪的石器遺存中最特別的是箭鏃的存在,說明這一帶的狩獵技術得到了新的發展。由此,峙峪人也被稱為「獵馬人」。峙峪的細小石器承許家窯文化而來,是中國細小石器晚期的代表,其中的尖狀器以小型化為主。賈蘭坡先生認為,中國北方、東北亞、日本列島、北美細石器的起源問題將有望在山西北部的桑乾河流域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峙峪的細小石器可能存在著向東擴展的現象,直接影響了中國北部更東更遠的區域,具有某種國際性意義。
與峙峪文化在時間上比較接近的是晉城沁水縣的下川遺址,分布於中條山主峰周邊的陽城、沁水、垣曲等地,距今2.3萬年至1.6萬年。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下川遺址中發現了石磨等加工農作物的工具,表明這一帶的農業發展十分傑出,是中國粟作植物原生地的重要實證。在近來的考古發掘中,下川也發現了粟作植物的種子,使這一證據更為可靠。同時,下川遺址發現的石器也非常重要,特別是細小石器,加工細緻,工藝複雜。這裡發現的三稜尖狀器出現了小型化的模式,其中的箭鏃採用壓製法製出銳尖與周邊。琢背小刀是其石器中的典型器物。錛狀器是下川地區出現的新的磨製技術製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石器,與新石器時代東北亞的款式一致,也可以說對其有重要的影響,為探索研究與之技術傳統相同,廣泛分布於中國、蒙古、俄羅斯、西伯利亞、日本、北美阿拉斯加等地的細石器文化之起源與發展提供了新的實證。
人們在臨汾吉縣柿子灘遺址也發現了許多重要的文化遺存,其存在時間為距今2萬年至1萬年。柿子灘發現的兩幅用赤鐵礦赭紅色繪製的巖畫,應該是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巖畫之一,描繪了人們耕作與舞蹈的形態。也有人認為是伏羲與女媧圖,但這一觀點與伏羲、女媧出現的時間不相合。此外,還有很多動物化石與燒骨、灰燼等遺存。柿子灘遺址中還發現了大量的石器工具,其中也存在細石器工具,其尖狀器等與山西地區的舊石器有文化上的相似性,表明它們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最典型的是在這裡發現了一系列石磨盤,透過對其表面提取物的研究,發現大多為黍類植物以及根塊類、豆科類植物。說明在這一時期,柿子灘一帶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大發展,人們的飲食方式出現了新的變化,需要經過較為精細的加工才可以食用。
透過對這些考古遺存的分析,我們發現,人類的形成,在山西的晉南地區具有獨立性。同時,舊石器時代石器文化具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殊性的文化形態,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大三稜尖狀器與細小石器。可以看出,經過漫長的努力,這裡逐漸發展出了新的文化,並對其他地區,包括遠東地區、北美地區等產生了影響。在採集、狩獵的過程中,人類逐漸學會了使用火,對動物的捕獲量越來越大,新技術製作的弓箭成為常用工具。農業由自然形態的採摘向集中採摘轉化,並向種植演進。審美功能也逐漸豐富起來。人類將迎來一個新石器與陶器並用的新時代,一個創造了異彩紛呈、斑斕多姿的新文化的時代。
第三節 石器時代的山西
在我們討論了人類進化的過程之後,發現山西在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顯現了中國具有人類形成的獨立性。特別是在垣曲一帶發現的世紀曙猿、西侯度與匼河發現的人類用火遺存以及丁村發現的古人類化石等,均具有文化上的連續性、一致性。以大三稜尖狀器為代表的舊石器在這些遺址中均有存在,鏟形齒的存在也證明了這些地區具有人種意義上的獨立性與一致性,且這種文化上的一致性表現得非常典型。
那麼,什麼是舊石器時代?是不是還有新石器時代呢?我們知道,石器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最早使用的勞動工具,也是當...
推薦序
引言 華夏文明與中華文明及其軸根(節錄)
關於中華文化,我們仍然需要對一些基礎性的東西進行梳理研究。人們常說,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華夏文明看山西。還有人認為,如果不了解山西的歷史,就很難了解中國的歷史。這些說法儘管不太一樣,但都在強調山西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那麼,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山西與華夏文明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這裡,我們就山西與中華文明的關係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以拋磚引玉,就教於大家,並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與研究。
考古學家蘇秉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指出,中華古文化的發展演變有一條從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連結帶,這一文化連結帶就在今山西沿汾河流域北上,再返回至晉南的區域中。他認為,「它在中華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間中華大地如滿天星斗的諸文明火花,這裡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帶,所以,它也是中華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軸根系」。蘇秉琦先生進一步對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紅山文化兩者之間「花」與「龍」的融合進行了分析,認為陶寺遺址中表現出來的具有從燕山北側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表現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地位,使我們聯想到今天「華人」、「龍的傳人」和「中國人」的稱呼所來。「中華民族傳統光芒所披之廣、延續之長,都可以追溯到文明初現的5,000年前後。正是由於這個軸根系在中華民族總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1990年代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系統完整的論證也是以這一地帶為主要依據提出的。」(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遼寧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2頁)蘇秉琦先生的這些論述十分重要,影響極為深刻。其間有幾個關鍵詞:一是「陶寺遺址」與「晉南」,強調了一個對華夏文明的形成來說十分重要的地域;二是「中華」,強調了是在晉南地區;三是「軸根系」,強調了中華文明在其總根系中存在一個軸根系,而這個軸根系就在晉南。那麼,我們就要較為詳細地探討梳理一下,存在於晉南的被稱為華夏文明的軸根系為什麼是軸根。
引言 華夏文明與中華文明及其軸根(節錄)
關於中華文化,我們仍然需要對一些基礎性的東西進行梳理研究。人們常說,山西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華夏文明看山西。還有人認為,如果不了解山西的歷史,就很難了解中國的歷史。這些說法儘管不太一樣,但都在強調山西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那麼,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山西與華夏文明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這裡,我們就山西與中華文明的關係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以拋磚引玉,就教於大家,並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與研究。
考古學家蘇秉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指出,中華...
目錄
引言 華夏文明與中華文明及其軸根
第一章 山西的自然地理條件
第二章 華夏文明的演進
第三章 陶寺遺址與華夏文明的形成
第四章 傳說中的山西
第五章 從華夏到中華
第六章 山西地區的貢獻
結語
引言 華夏文明與中華文明及其軸根
第一章 山西的自然地理條件
第二章 華夏文明的演進
第三章 陶寺遺址與華夏文明的形成
第四章 傳說中的山西
第五章 從華夏到中華
第六章 山西地區的貢獻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