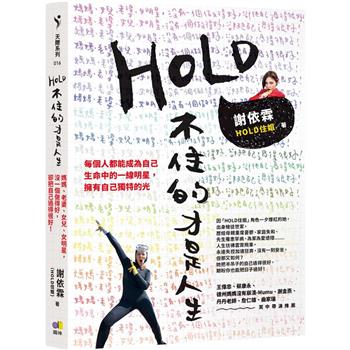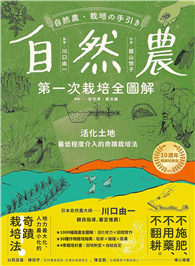20世紀被某些西方學者稱為「哲學中的孿生兄弟」的兩位哲學大家羅素(William Russell, 1872-1970)與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一生曾有數次交集,他們彼此分享了對於國際主義、科學方法與社會問題的觀點,同樣地懷疑教條──特別是宗教的教條;然而,兩人的思想終究異多於同,一種絕對的障礙將他們分開,那便是杜威的實用主義。
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別具意義的是這兩位享譽世界的西方大哲幾乎同時訪華,並對中國產生極大影響。羅素與杜威皆尖銳批判18世紀以來歐洲主流的「恐華觀」,抱持相對「崇華」的熱情來到中國,他們造成的衝擊是空前的,不僅被中國知識界稱為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化身,還都曾被譽為「西方孔子」或「孔子第二」。可以說,1920年代的中國經歷了一個「羅素化」與「杜威化」的交叉過程。本書探討這兩位西方大哲及其思想對於中國產生的不同影響,並進行深入比較。
本書特色
從羅素與杜威在中國的重大演講與影響,看中西知識界的交流;
羅素&杜威著作表、羅素&杜威訪華大事紀、羅素&杜威生平年表,一次收錄!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17 |
中文書 |
$ 607 |
西方哲學 |
$ 607 |
Others |
$ 621 |
社會人文 |
$ 621 |
當代思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丁子江
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北京大學哲學碩士,美國普渡大學哲學博士。加州州立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現兼任英文《東西方思想雜誌》(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主編,中文《東西方研究學刊》主編。曾任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IAES)前會長等。曾研究或任教於北京大學,美國普渡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等。著有《思想的再對話》、《羅素與分析哲學》、《羅素與中華文化》、《羅素與中西方思想對話》(臺灣版)、《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思貫中西》、《中國當代民營經濟史評》、《險道三十年》、《經濟大逃亡》、《美國之劫》、《吾輩》等十餘部書作,主編過《東西方思想家叢書》(四卷本)、《國際新比較學派文庫》(六卷本)以及大量中英文論文及各類作品。
丁子江
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北京大學哲學碩士,美國普渡大學哲學博士。加州州立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現兼任英文《東西方思想雜誌》(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主編,中文《東西方研究學刊》主編。曾任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IAES)前會長等。曾研究或任教於北京大學,美國普渡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等。著有《思想的再對話》、《羅素與分析哲學》、《羅素與中華文化》、《羅素與中西方思想對話》(臺灣版)、《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思貫中西》、《中國當代民營經濟史評》、《險道三十年》、《經濟大逃亡》、《美國之劫》、《吾輩》等十餘部書作,主編過《東西方思想家叢書》(四卷本)、《國際新比較學派文庫》(六卷本)以及大量中英文論文及各類作品。
目錄
自序
導言︱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第一節 「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
第二節 「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
第三節 「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
第四節 「羅素熱」與「杜威熱」
【上篇】「羅素化」與「杜威化」的比較
第一章︱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貴族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大眾主義」
小結
第二章︱羅素的「原子主義」 與杜威的「整體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原子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整體主義」
小結
第三章︱羅素的「浪漫主義」 與杜威的「務實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浪漫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務實主義」
小結
第四章︱羅素的「激進主義」 與杜威的「漸進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激進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漸進主義」
小結
第五章︱羅素的「悲觀主義」 與杜威的「樂觀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悲觀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樂觀主義」
小結
第六章︱羅素的「主智主義」 與杜威的「反智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主智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反智主義」
小結
第七章︱羅素的「批蘇主義」 與杜威的「贊蘇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批蘇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贊蘇主義」
小結
第八章︱兩位大哲交往中的互尊與互斥
小結
第九章︱「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與復甦
第一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
第二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復甦」
小結
本篇簡評︱在特定文化語境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下篇】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
第十章︱對兩位大哲知識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知識觀
第二節 杜威的知識觀
小結
第十一章︱對兩位大哲邏輯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邏輯觀
第二節 杜威的邏輯觀
小結
第十二章︱對兩位大哲教育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教育觀
第二節 杜威的教育觀
小結
第十三章︱對兩位大哲道德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道德觀
第二節 杜威的道德觀
小結
第十四章︱對兩位大哲美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美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美學觀
小結
第十五章︱對兩位大哲科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科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科學觀
小結
本篇簡評︱兩種哲學體系的撞擊與互動
【補篇】羅素與杜威訪華演講 及其影響的比較
第十六章︱羅素與杜威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一節 羅素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二節 杜威重要演講及其影響
本篇簡評
後記︱在遨遊的歷史時空穿越
本書參考文獻
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
羅素訪華大事記
杜威訪華大事記
羅素生平年表
杜威生平年表
導言︱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第一節 「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
第二節 「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
第三節 「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
第四節 「羅素熱」與「杜威熱」
【上篇】「羅素化」與「杜威化」的比較
第一章︱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貴族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大眾主義」
小結
第二章︱羅素的「原子主義」 與杜威的「整體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原子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整體主義」
小結
第三章︱羅素的「浪漫主義」 與杜威的「務實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浪漫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務實主義」
小結
第四章︱羅素的「激進主義」 與杜威的「漸進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激進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漸進主義」
小結
第五章︱羅素的「悲觀主義」 與杜威的「樂觀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悲觀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樂觀主義」
小結
第六章︱羅素的「主智主義」 與杜威的「反智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主智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反智主義」
小結
第七章︱羅素的「批蘇主義」 與杜威的「贊蘇主義」
第一節 羅素的「批蘇主義」
第二節 杜威的「贊蘇主義」
小結
第八章︱兩位大哲交往中的互尊與互斥
小結
第九章︱「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與復甦
第一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
第二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復甦」
小結
本篇簡評︱在特定文化語境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下篇】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
第十章︱對兩位大哲知識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知識觀
第二節 杜威的知識觀
小結
第十一章︱對兩位大哲邏輯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邏輯觀
第二節 杜威的邏輯觀
小結
第十二章︱對兩位大哲教育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教育觀
第二節 杜威的教育觀
小結
第十三章︱對兩位大哲道德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道德觀
第二節 杜威的道德觀
小結
第十四章︱對兩位大哲美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美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美學觀
小結
第十五章︱對兩位大哲科學觀的比較
第一節 羅素的科學觀
第二節 杜威的科學觀
小結
本篇簡評︱兩種哲學體系的撞擊與互動
【補篇】羅素與杜威訪華演講 及其影響的比較
第十六章︱羅素與杜威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一節 羅素重大演講及其影響
第二節 杜威重要演講及其影響
本篇簡評
後記︱在遨遊的歷史時空穿越
本書參考文獻
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
羅素訪華大事記
杜威訪華大事記
羅素生平年表
杜威生平年表
序
自序
這部題為《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的拙作,是著者三十多年教學與研究生涯的重要心得體會之一,也是對一代大哲羅素思想和方法進行審思與探討的學術結晶。可說是與著者其他三部拙作《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羅素與中華文化──東西方思想的一場直接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版;本書經過重大的修改與增刪,以《羅素與中西方對話》為書名由臺灣的秀威出版社推出了2016 年繁體版)以及《羅素與分析哲學──現代西方主導思潮的再審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版)構成了「羅素研究四重奏」。這四者所不同的是,前三者注重的是人物評傳、跨文化研究以及「純粹」哲學思想;而這本書稿則強調對羅素與杜威,即對直接影響現代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加以比較。對他們所進行分別研究的著述也許可達成千上百,數不勝數,但對他們加以緊密相聯而進行更全面深入詳備的比較研究,恐怕少之又少,甚至空白。
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20 世紀的兩位卓越的西方哲學家。有意思的是,西方竟有人稱他們倆是「哲學中的孿生兄弟」。有西方學者指出,杜威和羅素的相似之處是二者皆為20 世紀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在他們漫長的一生中(他倆都活到九十歲以上),兩者的道路曾有數次交集。
尤其是羅素與杜威都於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幾乎同時訪問了中國。不過,雖然彼此友好,但兩人絕對不是最好的朋友。認識並欽佩他們的胡克(Sidney Hook)曾經說過,只有兩個男人是杜威最不喜歡的:即阿德勒(Mortimer Adle)和羅素。對他而言,羅素永不停歇地貶損一般的實用主義者,杜威尤其為此而激怒無比。不過,這兩人分享了許多哲學的特徵:國際主義的觀點,對科學方法的高度重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並懷疑教條,特別是宗教的教條。羅素與杜威之間的區別更為顯著,一種絕對的障礙將他們分開:即杜威的實用主義。無論如何,對羅素來說,「實用主義是一種世俗的褻瀆(secular blasphemy)」。杜威說到:我要重述在羅素先生的《探究意義與真理》(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一書中對我的批評。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他的觀點與我的觀點有很大的區別,除非我們能相互理解,否則不會引起這些區別」。對中國知識界來說,最有意義的是,這兩位享有世界盛名的西方大哲,竟於華夏重大的社會轉型期,幾乎同時訪華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杜威與羅素對中國的影響和衝擊是空前的,儘管不一定是絕後的;但歷數訪華過的西方哲人或著名學者,至今還沒有哪一位能達到這種熱烈程度。這種「空前」至少表現在:一、杜威與羅素訪華之前,歷史從未有過任何重要西方哲學家或著名學者(傳教士除外)來過中國;二、綜合來說,當時杜威與羅素的博學智慧與文理皆通的學術造詣、思想的敏銳與豐富的閱歷、人格的力量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盛名於世;三、當時的中國正處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後社會轉型與重建的關鍵時期,也是動亂暫停百廢待興而相對和平發展的短瞬階段,思想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的理性、求知、包容、活躍,科學態度以及追求真理和批判探索精神是古今未有的;四、杜威在華超過兩年多,羅素在華也有十個多月,他們都作過大量的演講,也進行了相當廣泛的社會接觸,在後來的各種著作和場合經常提及中國,以致形成了獨到的中國觀與難以忘懷的中國情結。大哲杜威與羅素與中華文化難以割捨的關係,正是形成於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社會轉型期,即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剛剛發生的時期。當羅素與杜威訪華時,不僅被人們稱為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化身,還都曾被譽為「西方孔子」或「孔子第二」。杜威與羅素是擯棄18 世紀以來歐洲「恐華觀」的主流思潮,而作為「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鼓吹者與踐行者來到中國的。可以說,1920 年代的中國經歷了一個「羅素化」與「杜威化」的交叉過程。
杜威與羅素在中國各自都作了所謂五大演講。杜威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維的方式」;「我們時代的三大哲學家(柏格森、羅素、詹姆斯」;以及「論倫理學」;其實杜威一共作了五十八次大大小小的演講。而羅素的題目是:「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數理邏輯」;以及「社會的結構」;此外羅素還作了近二十次其他各種題目的演講。
在杜威與羅素之間有一些相似性:1.在政治上,都相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2.在文化上,都主張了無神論、科學主義、聖像破壞以及反宗教主義,這些都會適應新中國知識分子的需要,如反儒家、反規範、反倫綱等;3.在哲學上,都強調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4.在教育上,都傾向進步主義與功能主義。然而,我們應當考察兩位哲學家的區別而並非那些相似性。有三種可能的方法討論這個問題:1.通過兩位哲學家之間的辯論;2.通過中國知識界和西方學術界對兩位哲學家的評論或批判;3.通過兩位哲學家活動的結果。本書將集中討論關於1920 年代他們對中國不同影響的比較。
本書除導言外,分上篇下篇補篇共16 章。導言從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談起,闡述了「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以及當時所形成的「羅素熱」與「杜威熱」等。在上篇中,著者從「羅素化「與「杜威化」出發,接著深入比較了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羅素的「主智主義」與杜威的「反智主義」;羅素的「原子主義」與杜威的「整體主義」;羅素的「激進主義」與杜威的「漸進主義」;羅素的「浪漫主義」與杜威的「務實主義」;羅素的「悲觀主義」與杜威的「樂觀主義」;羅素的「批蘇主義」與杜威的「讚蘇主義」等。在下篇中,作者更進一步對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如二者不同的知識觀、邏輯觀、倫理觀、教育觀、美學觀、科學觀等。其中值得強調的是,著者對羅素為何沒有美學專著和杜威為何美學著作大放異彩作了較為深入的闡述。在補篇中,著者還比較了羅素與杜威各自在中國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這兩位大哲在中國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活動就是他們的演講,其中他們各自都有「五大演講」最受關注。
然而,很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演講的英文原稿並沒有得到保留。本書著者並不單純複述當年出版的中文譯稿,而是結合他們對這些演講論題的一貫思想,尤其是其英文原著,並聯繫最近一些西方學者對這些演講的重新追溯與深究,而再加以評述、闡釋與比較。為方便讀者,本書提供了羅素著作列表、杜威著作列表、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羅素訪華大事記、杜威訪華大事記、羅素生平年表、杜威生平年表等,並刊登羅素與杜威訪華圖片約30 張。
羅素在其後期最成熟的名著《人類知識》一書的序言中,稱自己與笛卡爾、萊布尼茲、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著作一樣,都並非為職業哲學家,而是為非專業的普通讀者而作的。實際上,他的這本書以及幾乎所有著作所產生的效應可說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杜威的各種著述也是如此。也許這就是哲學著述應達到的一種境界。本書的寫作目的正是朝這個方向的努力。
丁子江 2021 年5 月修改稿
這部題為《羅素與杜威──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之比較》的拙作,是著者三十多年教學與研究生涯的重要心得體會之一,也是對一代大哲羅素思想和方法進行審思與探討的學術結晶。可說是與著者其他三部拙作《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九州出版社,2012 年版)、《羅素與中華文化──東西方思想的一場直接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版;本書經過重大的修改與增刪,以《羅素與中西方對話》為書名由臺灣的秀威出版社推出了2016 年繁體版)以及《羅素與分析哲學──現代西方主導思潮的再審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版)構成了「羅素研究四重奏」。這四者所不同的是,前三者注重的是人物評傳、跨文化研究以及「純粹」哲學思想;而這本書稿則強調對羅素與杜威,即對直接影響現代中國的兩位西方大哲加以比較。對他們所進行分別研究的著述也許可達成千上百,數不勝數,但對他們加以緊密相聯而進行更全面深入詳備的比較研究,恐怕少之又少,甚至空白。
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20 世紀的兩位卓越的西方哲學家。有意思的是,西方竟有人稱他們倆是「哲學中的孿生兄弟」。有西方學者指出,杜威和羅素的相似之處是二者皆為20 世紀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在他們漫長的一生中(他倆都活到九十歲以上),兩者的道路曾有數次交集。
尤其是羅素與杜威都於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幾乎同時訪問了中國。不過,雖然彼此友好,但兩人絕對不是最好的朋友。認識並欽佩他們的胡克(Sidney Hook)曾經說過,只有兩個男人是杜威最不喜歡的:即阿德勒(Mortimer Adle)和羅素。對他而言,羅素永不停歇地貶損一般的實用主義者,杜威尤其為此而激怒無比。不過,這兩人分享了許多哲學的特徵:國際主義的觀點,對科學方法的高度重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並懷疑教條,特別是宗教的教條。羅素與杜威之間的區別更為顯著,一種絕對的障礙將他們分開:即杜威的實用主義。無論如何,對羅素來說,「實用主義是一種世俗的褻瀆(secular blasphemy)」。杜威說到:我要重述在羅素先生的《探究意義與真理》(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一書中對我的批評。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他的觀點與我的觀點有很大的區別,除非我們能相互理解,否則不會引起這些區別」。對中國知識界來說,最有意義的是,這兩位享有世界盛名的西方大哲,竟於華夏重大的社會轉型期,幾乎同時訪華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杜威與羅素對中國的影響和衝擊是空前的,儘管不一定是絕後的;但歷數訪華過的西方哲人或著名學者,至今還沒有哪一位能達到這種熱烈程度。這種「空前」至少表現在:一、杜威與羅素訪華之前,歷史從未有過任何重要西方哲學家或著名學者(傳教士除外)來過中國;二、綜合來說,當時杜威與羅素的博學智慧與文理皆通的學術造詣、思想的敏銳與豐富的閱歷、人格的力量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盛名於世;三、當時的中國正處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後社會轉型與重建的關鍵時期,也是動亂暫停百廢待興而相對和平發展的短瞬階段,思想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的理性、求知、包容、活躍,科學態度以及追求真理和批判探索精神是古今未有的;四、杜威在華超過兩年多,羅素在華也有十個多月,他們都作過大量的演講,也進行了相當廣泛的社會接觸,在後來的各種著作和場合經常提及中國,以致形成了獨到的中國觀與難以忘懷的中國情結。大哲杜威與羅素與中華文化難以割捨的關係,正是形成於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社會轉型期,即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剛剛發生的時期。當羅素與杜威訪華時,不僅被人們稱為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化身,還都曾被譽為「西方孔子」或「孔子第二」。杜威與羅素是擯棄18 世紀以來歐洲「恐華觀」的主流思潮,而作為「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鼓吹者與踐行者來到中國的。可以說,1920 年代的中國經歷了一個「羅素化」與「杜威化」的交叉過程。
杜威與羅素在中國各自都作了所謂五大演講。杜威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維的方式」;「我們時代的三大哲學家(柏格森、羅素、詹姆斯」;以及「論倫理學」;其實杜威一共作了五十八次大大小小的演講。而羅素的題目是:「哲學問題」;「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數理邏輯」;以及「社會的結構」;此外羅素還作了近二十次其他各種題目的演講。
在杜威與羅素之間有一些相似性:1.在政治上,都相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2.在文化上,都主張了無神論、科學主義、聖像破壞以及反宗教主義,這些都會適應新中國知識分子的需要,如反儒家、反規範、反倫綱等;3.在哲學上,都強調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4.在教育上,都傾向進步主義與功能主義。然而,我們應當考察兩位哲學家的區別而並非那些相似性。有三種可能的方法討論這個問題:1.通過兩位哲學家之間的辯論;2.通過中國知識界和西方學術界對兩位哲學家的評論或批判;3.通過兩位哲學家活動的結果。本書將集中討論關於1920 年代他們對中國不同影響的比較。
本書除導言外,分上篇下篇補篇共16 章。導言從1920 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談起,闡述了「德先生」、「賽先生」與「西方孔子」,「恐華觀」的尖銳批判者與「崇華觀」的熱情知行者,「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形成以及當時所形成的「羅素熱」與「杜威熱」等。在上篇中,著者從「羅素化「與「杜威化」出發,接著深入比較了羅素的「貴族主義」與杜威的「大眾主義」;羅素的「主智主義」與杜威的「反智主義」;羅素的「原子主義」與杜威的「整體主義」;羅素的「激進主義」與杜威的「漸進主義」;羅素的「浪漫主義」與杜威的「務實主義」;羅素的「悲觀主義」與杜威的「樂觀主義」;羅素的「批蘇主義」與杜威的「讚蘇主義」等。在下篇中,作者更進一步對羅素哲思與杜威哲思的深入比較:如二者不同的知識觀、邏輯觀、倫理觀、教育觀、美學觀、科學觀等。其中值得強調的是,著者對羅素為何沒有美學專著和杜威為何美學著作大放異彩作了較為深入的闡述。在補篇中,著者還比較了羅素與杜威各自在中國的重大演講及其影響。這兩位大哲在中國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活動就是他們的演講,其中他們各自都有「五大演講」最受關注。
然而,很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演講的英文原稿並沒有得到保留。本書著者並不單純複述當年出版的中文譯稿,而是結合他們對這些演講論題的一貫思想,尤其是其英文原著,並聯繫最近一些西方學者對這些演講的重新追溯與深究,而再加以評述、闡釋與比較。為方便讀者,本書提供了羅素著作列表、杜威著作列表、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杜威著作中文譯本列表、羅素訪華大事記、杜威訪華大事記、羅素生平年表、杜威生平年表等,並刊登羅素與杜威訪華圖片約30 張。
羅素在其後期最成熟的名著《人類知識》一書的序言中,稱自己與笛卡爾、萊布尼茲、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著作一樣,都並非為職業哲學家,而是為非專業的普通讀者而作的。實際上,他的這本書以及幾乎所有著作所產生的效應可說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杜威的各種著述也是如此。也許這就是哲學著述應達到的一種境界。本書的寫作目的正是朝這個方向的努力。
丁子江 2021 年5 月修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