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不孕症的例外
在兩年前,當我尚未閉門謝客的時候,我的靈算早已轟動海內外,在那時候,家裡的小客廳天天高朋滿座,星期日我從上午八時開始,一日演算兩百人之眾。後來,由於人潮洶湧不止,體力不支,人們找我不分白天深夜,我連吃飯睡覺都成問題。於是,就在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正式登報寫書聲明,謝絕一切訪客,堅決不再替人演算,如此才算漸漸緩和下來,也總算保住了自己的小小生命。
到今天為止,每日仍有人登門求見,來信每日平均五十封左右,因此,在本書第一篇文章的開始,我仍然鄭重聲明,目前我依然閉門謝客期間,請勿來找,也勿來信。我現在仍在等待,等待時間有了,體力有了,閉門謝客期滿,再繼續為人服務。
那是好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客人都走光了,我收拾了桌子上一些零亂的碎紙片,倒了一杯茶,坐在沙發椅上,正準備休息的時候,內人走到電視機前,準備關掉電視。
「慢點關。」我說。
「為什麼,這麼晚了?」
「我今天的興致很高,精神愉快,想看完『勇士們』後再睡覺。」
「大概你今天替人靈算,次次準確,言必有中吧!」麗香說。
「說的也是,連我自己有時候也不免吃驚異常。」這是我的真心話。每當我替人靈算,非常準確的時候,內心總要自己先高興一番,這樣更證實,我的「皇極數」和「一丈青」沒有錯,而且學習的境界,也在無形中次次的提高,愈來愈發現其奧妙之處。
就在這時候,門又「碰,碰」的響了起來,又來了兩名不速之客,是一對年輕的夫婦,男的西裝筆挺,女的穿戴高雅,面目秀麗。
「對不起,打擾了,我們慕名而來,因為你這裡很偏僻,計程車兜了一大圈,所以這時候才到,能偏勞一番嗎?」女的很客氣的說。
「好吧!」我說。內人拿了一張白紙給他倆,要他們寫下姓名、地址、年齡。於是,我在桌子前占了一課,此課為皇極數內的「孤陰」之卦,卦意是「一竅豈可以窺其髓,占法不可以執一也,精神之氣獨流一旁,人丁求之而不可得也。」我回頭對這對夫婦說:「若問子息,求之不得。」
「先生已知我們來意?」男的問。
「自然,卦意已明顯表示矣!」
「我們連一個子女都沒有?」
「是的。」我截釘斷鐵的說。
「我們求神拜佛?」那女的很焦慮的說。
「無法。」
這對夫婦,男的叫施金鐘,女的叫文秀容。他們對我說,他們夫婦結婚已經五載,始終不曾受孕,兩個人都找過名醫檢查,檢查的次數相當多,但檢查結果都認為「正常」,然而始終信息一直不來,夫婦生活雖然美滿,卻有這件憾事。
「盧先生,無論如何,想想看,有無方法?」
「沒有,絕對沒有。皇極數的孤陰表示連一點少陽之氣均無,二者皆是孤陰,無法達成陰來陽受和陽來陰受之數,其數為零,零則不生,故絕無後嗣可言。」
他們夫婦垂頭喪氣,我也為他倆內心難過。
這件事過了之後我也就忘了。大約是八個月之後吧!是冬天的晚上,文秀容女士單獨一個人來找我,她這次來,不是問子息來的,而是為了先生的調職問題而猶疑不決。然而,令我大大吃驚的是,文秀容女士的肚子已經高高隆起,雖是冬天,衣服穿得較厚,但那明明是有了身孕。我內心微微感到震撼與難過,是我占卜錯了?還是我起課時疏忽了某些細節?此時,我臉孔紅了,羞愧得無地自容,當初我判斷他倆終生無子息,現在文女士好端端的站在面前,表示她已有了身孕,她雖不開口責難我,但這種無言的抗議,實在比針刺還難過。
「妳......。」我的喉嚨就像被骨頭卡住一樣。
「我今天不是問子息,而是問先生調職的吉凶?」文秀容女士態度自然。
她愈是表現的從容不迫,我愈是難過。
「哦!是嗎?」我用懷疑的眼光看她。
她紅了臉,低下了頭。
「告訴我,文女士,無論如何告訴我,皇極數是不容易出差錯的,請告訴我,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妳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一回事,妳今天來,令我毫無信心,真的!令我毫無信心,我無法再替人占算,像這樣子﹔我如何再替施先生占算調職的吉凶呢?」
她不說話,嘴咬著嘴唇。
「一定要告訴你嗎?」
「這是我求妳,皇極數從未失算,這次失算,我極不甘心。」
「我先生對你著的書極讚賞,但自從你告訴我們毫無子嗣之後,而我又開始空嘔頭暈,一檢查卻有孕了,他從此不再談到你,不再看你的書,別人談到你,他只是淡淡的反應了一句:事實可以證明一切。」
「我不聽這些,我要你告訴我原因。」
「好吧!」她含羞帶愧的說:「我遭到一個惡棍......強暴......。」
「強暴」──天!是強暴。
在我的腦海中,昇起了一副幻覺的景象,文秀容姍姍的走在一條暗夜的小巷,夜黑風大,文女士窈窕的背影,容易使登徒子引起一片遐想,於是,黑暗的大地伸出一隻怪手,矇住了文女士的眼睛,另外一隻怪手攔腰抱住。她用手擋,用身子扭,無濟於事,暴徒總是孔武有力的。於是,天整個的崩潰,地也開始震動,風呼嘯的吹了過去,星星被雲層遮蓋,假如有雲,就會有雨,雨會把黑暗的世界洗涮得乾乾淨淨。
「你沒有罪。」我告訴她。「當做是一種命運的意外吧!孩子生出來,帶來讓我看看,也許孩子將來的成就是另外一個令人驚奇的事。」
「我這樣算什麼?」她有些無助,楚楚可憐。
「把一切看淡看開,人生的一切,看淡看開就沒有苦惱,若執著,會痛苦一輩子。」
但,今之世人,有誰真正看得開呢?
據皇極數,我占的課是丁火,朱雀火,河魁土,卯木。卯為門,以土木塞住,故皆無孕也。又經中有言曰:如果比喻甲為木,乙為草,丙是火,丁是煙。所以甲陽木而燥,所以能生丁煙。乙陰草能生丙火,陽產於陰,陽為父,陰產於陽,陰為母。若陽見陽,陰見陰,陰陽拮据,如密雲而不雨,當然無孕。
另外,我曾替人占算,占出「二水一木一土」,有口訣曰:「二水一木一土當,性強還恐少年郎,乞得外姓為兒女,日久年深改趙張。」
「二水一木一土」,其大意亦無後嗣。
002 西南方的一棟小屋
人生命運如浩浩長流滾滾奔濤,我們若客觀的玩味人生,站在高山的巔峰遠眺,隱隱約約可以看見地平線伸延在遠處,宇宙四方的氣勢,使每一個人的心胸皆開闊起來。我覺得每個人的命運,可以形容成為大江的小支流,雖然不夠雄渾的氣派,但也是很美的,充滿了追思、遐想,如詩、如畫。
蔡義宏和沈守篤兩位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們兩個是中興大學的教授,蔡義宏教化學,沈守篤教數學和電子,閒暇時,三個人研究道學,互切互磋,我們曾和道教會的理事長陳仙洲先生討論成立道學研究中心,可惜事未成,陳仙洲卻已去世。
蔡義宏治學認真,他不但看《易經》,也看《河圖》、《洛書》,對熊十力的著作和牟宗三的著作,經常參研比較。他們對占卜有興趣,也學排卦,遇有不解的地方或疑難之處,便急急跑來找我。沈守篤曾笑著對我說,我成了蔡義宏解決疑難的專家了。在道學方面,蔡義宏教授提出壹百零捌問,而我一題一題的解答,此問答將印成單行本傳世呢!
有一天。
「老盧,我們學校准了一批錢,給我們貸款買房子。」蔡義宏說。
「恭喜你,總算你熬了半輩子,上有片瓦,下有立錐之地了,一共貸款多少錢?」
「十九萬。」蔡義宏說:「我找遍了整個臺中市房子,找不到合適的,而貸款的限期已經快到了,今天特來請你指點迷津,指示一條明路。」
「你又來了。」
「無事不登三寶殿,拜託,拜託。」
於是,我擺香案,置上卦盤,略一占卜,我說:「西南方的一棟小屋。」
「多少錢買成?」
「二十三萬成交。」
我再替西南方的小屋占得一卦,此乃「壬勾陳寅」,水行土上,所以恐有水患之災。我再運用靈機神算,指示謂:「蔡義宏與此屋緣分甚重,雖水行土上,略有水患,但無大礙。」我把水患一事隱起不說,因為我若把水患一事說出來,蔡義宏這位篤實的教授,這輩子恐怕找不到房子住了。
一個月後,蔡義宏興奮的跑來告訴我。
「找到了,找到了,果然在西南方,門朝西,屋子座南,由我以前租的房子算起,也是西南方。地點在臺中縣草湖塗城路,那位建築商開口是二十七萬,我殺了二萬,成了二十五萬,到此為止,那位建築商無論如何咬定二十五萬,一點也不肯相讓,我們繼續商談好幾天,我想,二十五萬就二十五萬吧!因為機緣一閃即失,聽說還要漲價呢?然而,說來奇怪,那位建築商睡了一覺,隔了一天,卻自動減價成二十三萬,這樣一來,一切全符合了。二十三萬成交,真是奇準,真是奇準。」
「這不算什麼的。」我說。
「當建築商突然神經般的自動便宜兩萬之後,我曾經要求他再少五千元,然而,花費了多少的交涉,結果還是斬釘截鐵的二十三萬,一塊錢也不能少。還有更妙的是我供奉的太上老君神桌,一擺入房子中,連分寸都不差,剛剛好和牆壁一樣長,沈守篤說,這神桌的尺寸是老盧演算出來的,而房子的尺寸是建築商設計建造的,然而卻完全密合,真是令人驚奇,令人驚奇。」
我淡淡一笑,不說什麼。有一回傍晚,那是農曆十月十五日,雨淅瀝淅瀝的下著,我乘車到草湖,車窗外一片朦朦朧朧,東方的山頭隱去,到處都是飛霧。車到巷子底,我發覺水聲淙淙的排水溝不見了,擋在排水溝之前是約有一人高的土牆。
「這土牆?」
「擋水用的。」蔡義宏說:「每逢大雨,排水溝的水高漲,這裡的地勢略低,因此水會倒灌,這巷子的人,合力建了這水泥牆擋水。」
「老盧當初何不說有水患?」沈守篤問。
我淡淡一笑。此事只有我內心明白了。
回家後,特書一偈,聊以自嘲。
占卜問居向,遙指西南方﹔
定數二三萬,唯患來水慌。
吉屋供老君,山水伴溪流﹔
景色依然故,淡笑解心愁。
003 謎中謎
新竹有一位小孩童,八歲,跟著鄰居的小孩到河邊垂釣,鄰居的小孩都回家了,而那位小孩卻沒有回家。小孩叫葉明哲,很聰明,長得也很清秀。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但葉明哲就像突然消失在地球上一樣,無緣無故失蹤了,神不知鬼不覺,沒有人曉得他到底到那裡去。葉明哲的家人四處奔走尋找,親朋之處,可能到的地方全找遍,結果非常的失望,一家人陷入無窮盡的悲淒之中。
葉明哲死了?很多人都認為他跟著人去釣魚,極可能失足落河而溺斃,然而,他的家人也想到這一點,曾經從河的上游搜索到河的下游,一連來回好幾次,可以說只差一點沒有把河底給翻了起來,然而,蹤跡全無,絲毫的跡象都找不到。
是綁票?葉家本身並不富有,不能構成綁票的要件,同時葉明哲的父親,僅僅是一位老實的公務人員,他們也報警,警方也考慮到這一點,但很快的便否決了。同時,綁票若發生,葉明哲的家人一定會接到歹徒的通知,事實上,連一點訊息也沒有。
是拐誘嗎?葉明哲是男孩不是女孩,女孩長大也許還可當搖錢樹。有人說也許給歹徒看上,訓練他成為三隻手的。也有人說,拐去殺害,取其身體某一部分煉藥,這種說法較無稽,也實在太慘無人道了。種種的想法和假設都被一一推翻,但,孩子失蹤就是失蹤。家人盼望奇蹟出現,他會突然回來,但,這種想法變成無止盡的奢想。
人在絕望的時候,總會想起虛無的神明,於是人們的饒舌就變成他們奔波的目標,他們開始求神,跑到苗栗去問山頂的王爺公,王爺公說死了這條心吧﹗人早死了,屍體在某某地方。結果他們跑去找屍體,大失所望,什麼也沒有。他們又到梧棲拜王母娘娘,神說三個月後出現,結果連影子也沒出現。他們又找到竹東一位占米卦的,占米卦的告訴他,死矣!死矣!他們又聽人傳聞,跑到埔里的一間呂仙公廟,呂仙公告訴他,葉明哲的靈魂早入了地獄,正在枉死城受苦,說得他們眼淚直流。他們找到民雄一位相師,相師說,此人命星已絕。又跑到後龍的廟去問神,更絕的是,神說葉明哲是上界仙師下凡塵,如今又回天上去了。他們又......。總之,全寶島的神全問遍。
最後他們找到草屯的下茄洛地方的玄天上帝廟,結果那位玄天上帝說:「去找盧勝彥,速速尋訪盧勝彥。」
這豈不是玄天上帝找我的碴嗎?自己不指示他,卻往我的身上推,存心尋我開心。
他們來了很多人,我聽了前因後果之後,很仔細的占卜,卦是「二金一水一木,有偈曰:「二金一水一木強,暫時分離卻無妨,日後兒孫多俊麗,家中和會喜非常。」
我由卦意推斷:「還活著。」
「活著?」他們都不信。
「盧先生,你敢保證?」一位年輕人粗聲蠻橫的問。
「勝彥但問卦意,不敢作證。」
大家哄堂大笑。
「盧先生,目前只有你一個人說活著,我們相信神明,那些神明都說死了,我很感謝你給我一線希望,但,活著人在哪兒呢?」葉明哲的父親沉住氣問我。
「目前我不知道在哪兒。」我說。
「不知道在哪兒,還敢說活著!」那位年輕人露齒冷笑。
「對不起,請原諒,我僅僅是憑卦意的。」我轉頭對葉明哲的父親說:「請你在農曆十五的晚上一個人來好嗎?我很樂意替你指示出葉明哲的目前下落,到時候我會用一丈青的靈示方法,請求靈示出他的地點,然後你再去找他。」
一堆人走了,吱吱喳喳。
有人說:「神都說死了,他卻說活著,他算什麼?」
有人說:「騙子,耍花招的騙子。」
有人說:「失蹤一年多,若活著一定會回來。」
農曆十五日,晚上。
我在牆壁上貼了幾張紙條,這些紙條包括了全世界的國名,還有本省各地方的地名,從北至南,我又貼上一張「活著」與「死亡」的字條。然後我取來一根新的綠色竹子,竹子長有「一丈」,請一位少年人,雙眼閉起,少年人手扶竹桿的中央。
葉明哲的父親來了。於是,我使用了青城山清真道長的「一丈青」方法,用「生命滋氣」加注在少年人的頭頂,一遍又一遍,那位少年人定住了,手完全不動,但竹子開始微微顫抖,此時我把握機會發問。
「一丈青,葉明哲人在哪裡?」
竹桿拚命的顫抖,一直向上移動,這種移動不是人的意識,而是靠著生命滋氣的靈力,竹桿指著「活著」二字。
「活著我知道,請靈示人在何處?」
竹桿一直的轉圈,轉圈,依我的經驗,竹桿轉圈圈,表示祂尚在調查,轉了約三分鐘之後,竹桿停住在「高雄」二字上。
「在高雄何方?」
「南方。」
「目前做什麼事?」
「在工地上建築工程做小工。」這幾個字,是我臨時找來紙筆,寫好迅速貼上去的,當然貼的工作共有二十幾種,反正想到的全寫了上去。
葉明哲的父親,此時有一點淚眼模糊了,他說:「半年前,明哲的母親夢見好多船好多船,接著看見自己的兒子站在船邊,那是一個很大的碼頭,兒子在夢中向母親直喊高雄,高雄,高雄啊!明哲的母親醒來後,曾要我到南部高雄找找看,我一想高雄人口近百萬以上,大海撈針如何找起,同時只憑一場夢如何當真呢!沒想到靈示的結果仍在高雄。」
葉明哲的父親終於帶著一絲希望去找葉明哲,他從新竹乘火車南下到高雄,特別注意到高雄的南方一帶,一日又一日的奔波在旅途之中,不管刮著大風,下著大雨,日出日落,豔陽高照,他找遍了前鎮區草衙一帶,找遍了林園小港一帶,找遍了新興區和前金區,含著淚水,腳磨破了皮,每見有新建樓房住宅的工地,便迎了上去,然而,每一次皆失望,搖頭嘆氣。
他一直找到鳳山市和高雄市的中間五塊厝,一個黃昏日落的時候,他看見一個瘦小的背影在工地撿拾散落地上的水泥袋,他跨過幾塊板模,進入工地的屋中,屋頂滴下水和沙,流了整個的臉,工程灌漿剛完畢。他喊:「明哲。」
那孩子回頭,驚得手上的水泥袋散落一地。兩人相擁大哭。
事情的真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葉明哲在河邊遇到一位工人,他要求工人帶他去做工賺錢,他自稱是孤兒,沒有家,只想賺錢,而那位工人就帶他到高雄做工。
「你要錢做什麼?」
「我看爸爸賺錢很辛苦,只想自己幫爸爸的忙,只做兩年苦工,再讀書。」
「怎不回家說一聲?」
「我知道回家告訴你們,你們絕不會答應。」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命運的驚奇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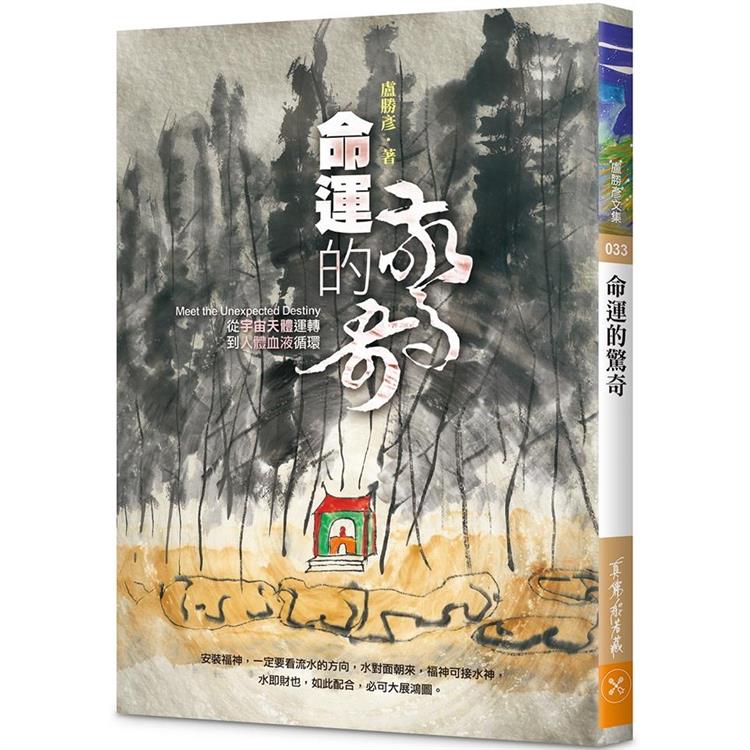 |
命運的驚奇【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盧勝彥 出版社: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出版日期:2023-12-1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真佛宗 |
$ 234 |
中文書 |
$ 234 |
佛教 |
$ 234 |
宗教命理 |
$ 234 |
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命運的驚奇
「命運」到底有無?這是從古至今人人爭論的問題,其實,作者認為命運不必去爭論有或無,因為爭論命運毫無益處,倒不如我們去認識自己的命,努力去實踐我們的運,我們由知命來發揮自己的專長,以這人生短短的生命過程,貢獻給國家和社會。
本書寫作的內容,以作者過去替人演算的事實為經,以命運的演算法則為緯,說明命運格局的底定,真理如何水落石出,因果關係與邏輯,並且談到「靈感」,形而上的一些契機,在在說明宇宙與人類的原理原則,假如你靜下來想一想,這宇宙很奇妙,這世界很奇妙,這人間也很奇妙,甚至你這個人也很奇妙,等你想通了,你會拍案驚奇,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商品特色
我們不必去迷信「命運」,但是,我們至少要「知命」,知道自己如何去努力開創自己的前途,知道怎麼走才會成功
有人種樹,有人乘涼;有人播種,有人收成;有人抬轎,有人坐轎;有人犧牲,有人享受。
誰說這不是命運?看完此書,你驚奇嗎?
【附贈封面使用作者複製畫一幅】
作者簡介:
蓮生活佛盧勝彥,西元1945年生於二戰下憂患的台灣,
現旅居於煙雨微微的西雅圖,每日修行、寫作及繪畫,
以實證和慈悲勾勒度眾的文字,如月河流水閃耀智慧的光環。
是真佛宗創辦人
平易親切、慈悲為懷的開解病難憂苦,獲得千萬弟子的景仰皈依。
是一位演說家
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的闡述佛法哲理,具有獨樹一格的講演藝術。
是一位畫家
天賦異稟、微妙觀察的書畫自然景物,成就自在任運的揮毫創作。
更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
多元題材、精勤撰寫的抒發心境體悟,紀錄親身經歷的數百冊文集。
1967年第一本創作《淡煙集》問世。
1992年5月完成《第一百本文集》。
2008年5月出版第二百本文集《開悟一片片》。
他是當代能將佛法與藝術結合的第一人,精進與毅力不同凡響。
章節試閱
001 不孕症的例外
在兩年前,當我尚未閉門謝客的時候,我的靈算早已轟動海內外,在那時候,家裡的小客廳天天高朋滿座,星期日我從上午八時開始,一日演算兩百人之眾。後來,由於人潮洶湧不止,體力不支,人們找我不分白天深夜,我連吃飯睡覺都成問題。於是,就在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正式登報寫書聲明,謝絕一切訪客,堅決不再替人演算,如此才算漸漸緩和下來,也總算保住了自己的小小生命。
到今天為止,每日仍有人登門求見,來信每日平均五十封左右,因此,在本書第一篇文章的開始,我仍然鄭重聲明,目前我依然閉門謝客...
在兩年前,當我尚未閉門謝客的時候,我的靈算早已轟動海內外,在那時候,家裡的小客廳天天高朋滿座,星期日我從上午八時開始,一日演算兩百人之眾。後來,由於人潮洶湧不止,體力不支,人們找我不分白天深夜,我連吃飯睡覺都成問題。於是,就在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正式登報寫書聲明,謝絕一切訪客,堅決不再替人演算,如此才算漸漸緩和下來,也總算保住了自己的小小生命。
到今天為止,每日仍有人登門求見,來信每日平均五十封左右,因此,在本書第一篇文章的開始,我仍然鄭重聲明,目前我依然閉門謝客...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
抬轎人與坐轎人
昔日,我由青城山嫡傳祖師清真道長,親自傳授「皇極數」和「一丈青」,皇極數是屬於先天的數字演算,而一丈青是由偶發的靈機演算。皇極數與一丈青,都是演算命運的巧妙方法,兩者最大的分別,皇極數可算出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準確性甚高(《了凡四訓》內,曾詳載袁了凡遇孔道人,孔道人精於此術),而一丈青可演算近期間任何事情的吉凶,推斷如神,絲毫不差。
「命運」到底有無?這是從古至今人人爭論的問題,其實,我覺得命運不必去爭論有或無,因為爭論命運毫無益處,倒不如我們去認識自己的命,努力去實...
抬轎人與坐轎人
昔日,我由青城山嫡傳祖師清真道長,親自傳授「皇極數」和「一丈青」,皇極數是屬於先天的數字演算,而一丈青是由偶發的靈機演算。皇極數與一丈青,都是演算命運的巧妙方法,兩者最大的分別,皇極數可算出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準確性甚高(《了凡四訓》內,曾詳載袁了凡遇孔道人,孔道人精於此術),而一丈青可演算近期間任何事情的吉凶,推斷如神,絲毫不差。
「命運」到底有無?這是從古至今人人爭論的問題,其實,我覺得命運不必去爭論有或無,因為爭論命運毫無益處,倒不如我們去認識自己的命,努力去實...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抬轎人與坐轎人
001 不孕症的例外
002 西南方的一棟小屋
003 謎中謎
004 兩包薪水袋
005 死亡的定數
006 陸橋下的福神
007 發財夢與六六八○五三
008 安靈的意外
009 沒有命運的人
010 試探另一章
011 開墳之所見
012 入門遁的第一步
013 突降的甘霖
014 風雷與雲雨
015 病家何處去
016 最忌三火卦
017 我的三不算
018 卜筮有神
019 魚目與珍珠
020 奇蹟
021 讀〈雲霄賦〉之領悟
022 瞬間的預測
023 論孔明借東風
024 對不起,我不能收
025 「西方勝景」的看見
026 高靈何不降人間?
027 同名同號的靈
028...
001 不孕症的例外
002 西南方的一棟小屋
003 謎中謎
004 兩包薪水袋
005 死亡的定數
006 陸橋下的福神
007 發財夢與六六八○五三
008 安靈的意外
009 沒有命運的人
010 試探另一章
011 開墳之所見
012 入門遁的第一步
013 突降的甘霖
014 風雷與雲雨
015 病家何處去
016 最忌三火卦
017 我的三不算
018 卜筮有神
019 魚目與珍珠
020 奇蹟
021 讀〈雲霄賦〉之領悟
022 瞬間的預測
023 論孔明借東風
024 對不起,我不能收
025 「西方勝景」的看見
026 高靈何不降人間?
027 同名同號的靈
028...
顯示全部內容
|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