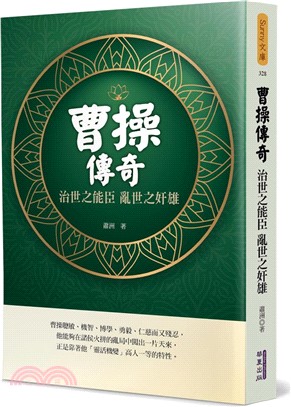曹操聰敏、機智、博學、勇毅、仁慈而又殘忍,他能夠在諸侯火拼的亂局中闖出一片天來,正是靠著他「靈活機變」高人一等的特性。
名作家司馬中原先生說:「本書緊扣著歷史的縱線,把筆墨用在樞紐漢末半世紀的曹操身上。最可貴的是,『史觀持平公正,寫得深刻而透澈,對長久以來神秘如謎的人物,有了客觀的評判和剖析』。」
事實上,歷朝歷代,身處滔滔亂世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有著多面的性格和複雜的心理狀態。也正如杜甫形容古柏云:「落落盤據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任何人到曹操那個位置,閒言閒語都是免不了的,他一生不廢漢獻帝,自己不取而代之,他認定若是沒有他一力周全,天下更不知亂成什麼樣子,這倒是實在話,三分後的曹魏地區,百姓還是能夠溫飽的。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曹操傳奇: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奸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58 |
社會人文 |
$ 510 |
中文書 |
$ 510 |
歷史人物 |
$ 522 |
中國史地總論 |
$ 522 |
歷代君主/帝王 |
$ 522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曹操傳奇: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奸雄
內容簡介
目錄
序 閒說曹操傳奇-司馬中原/007
第一章 生於宦家,聲帶秋肅之氣/013
第二章 棒打權貴,建立法治威信/027
第三章 偶逢舊識,興義兵伐董卓/041
第四章 割來使耳,促敵正面激戰/057
第五章 不思稱帝,謀士猛將齊來/073
第六章 猛將擒帥,降服黃巾餘黨/087
第七章 以父之名,起兵攻下徐州/102
第八章 死計誘敵,破呂軍於定陶/116
第九章 挾迎獻帝,使計離間呂劉/131
第十章 迎待劉備,曹身陷張繡營/144
第十一章 背敵除呂,水計三日敗呂/159
第十二章 煮酒論雄,劉備請軍殺袁/172
第十三章 計擒關羽,巧破文丑大軍/187
第十四章 官渡敗袁,燒密函獲人心/203
第十五章 料事如神,最奇謀士郭嘉/218
第十六章 假手殺人,招降荊州劉琮/233
第十七章 連環船計,赤壁戰天下分/247
第十八章 離間馬韓,平關西立魏公/261
第十九章 廣招賢士,疑心生殺異己/276
第二十章 功過難斷,亡後疑塚七二/290
第一章 生於宦家,聲帶秋肅之氣/013
第二章 棒打權貴,建立法治威信/027
第三章 偶逢舊識,興義兵伐董卓/041
第四章 割來使耳,促敵正面激戰/057
第五章 不思稱帝,謀士猛將齊來/073
第六章 猛將擒帥,降服黃巾餘黨/087
第七章 以父之名,起兵攻下徐州/102
第八章 死計誘敵,破呂軍於定陶/116
第九章 挾迎獻帝,使計離間呂劉/131
第十章 迎待劉備,曹身陷張繡營/144
第十一章 背敵除呂,水計三日敗呂/159
第十二章 煮酒論雄,劉備請軍殺袁/172
第十三章 計擒關羽,巧破文丑大軍/187
第十四章 官渡敗袁,燒密函獲人心/203
第十五章 料事如神,最奇謀士郭嘉/218
第十六章 假手殺人,招降荊州劉琮/233
第十七章 連環船計,赤壁戰天下分/247
第十八章 離間馬韓,平關西立魏公/261
第十九章 廣招賢士,疑心生殺異己/276
第二十章 功過難斷,亡後疑塚七二/290
序
序
閒說曹操傳奇
一般人對於曹操的印象,多來自家喻戶曉的一部書——《三國演義》,以及各種戲曲和各類說唱藝術;經過多代的誇張渲染,曹操這個人,早已被一張平劇臉譜蓋住了,變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大奸大惡之徒。這和正史中的魏武帝有很大的參差。
後世研究史學,除了講求「史據」、「史料」之外,更著重於「史觀」,持平公正的歷史觀點,應該是大匠著書立說的龍骨,能撥開迷霧、重現歷史的真容,還給歷史人物一份公道,這是非常緊要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本著正統正朔的觀點,在書中隨處都可見到「揚西蜀而貶魏晉」意念,尤其對曹操的作為充溢不滿之情,這樣的史觀雖吻合多數民間的傳統觀念,實際上並不持平。
《曹操傳奇》這部書,雖說是「傳奇」,事實上卻緊扣著歷史的縱線,把筆墨用在樞紐漢末半世紀的曹操身上,最可貴的是「史觀」持平公正,寫得深刻而透澈,對長久以來神祕如謎的人物,有了客觀的品評和剖析。
事實上,歷朝歷代,身處滔滔亂世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有著多面的性格和複雜的心理狀態。曹操聰敏、機智、博學、勇毅、仁慈而又殘忍,他能夠在諸侯火併的亂局中闖出一片天來,正靠著他「靈活機變」高人一等的特性。「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現實是冷酷無情的,在當時,他和董卓、袁紹、袁術、張繡、呂布、孫策、劉表、劉備,都被投在一個烈火熊熊的時代大熔爐裡,每一舉措都攸關生死存亡,煉出來的就是精鋼,煉不出來就成了廢鐵,從群雄紛起到三國分據,就證明魏、蜀、吳的領導人物各有所長,全非簡單人物。
攤開漢末的地圖來看,曹魏所占據地區,全是人口眾多、物產豐足,工業發展良好的菁華地區,不論是兵員、物產、糧草、武器裝備,都優於蜀與吳;又曹操摩下可說是謀臣如雨,猛將如雲,若不是曹操求賢若渴、愛才如命,這些異士能人也不會抵死追隨他。
反觀東吳,偏處東南一隅,當時除江蘇南部、福建北部、江西、湖北之一部外,大多是未曾開發的荒蠻之境,地廣人稀,雖靠長江天險可割據一時,其工業、國防力終竟難和中原之地抗衡。至於當時的西蜀,人口數遠遜曹魏,工業力更形薄弱,南方更有孟獲威脅;孔明精於「數」,不可能沒有比評,他之六出祁山也祇能說盡人事而已。
曹操的後半生,經常頭痛欲裂,性情大變,極可能患有腦瘤,加上精神分裂,躁鬱加妄想所致。把病人看成惡魔也不夠公平,也正如杜甫形容古柏云:「落落盤據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任何人到曹操那個位置,閒言閒語都是免不了的,他一生不廢漢獻帝,自己不取而代之,他認定若是沒有他一力周全,天下更不知亂成什麼樣子,這倒是實在話,三分後的曹魏地區,百姓還是能夠溫飽的。
漢末的曹操確是詩人的地位,他的詩雄莽渾厚,瀟灑而具悲情,在《曹操》這冊書裡所引用的詩,哪一首不蒼古奇倔,確具大家風範?深夜展卷讀這樣一部好書,真是如飲醇酒,芳春透骨。痛飲後,復有一縷悲情,使人泫然欲泣。曹孟德本身,何嘗不是成功又失落的悲劇呢?而他回歸田園、閒隱青山的夢,終其一生也是漸行漸遠,永不回來了。
司馬中原
閒說曹操傳奇
一般人對於曹操的印象,多來自家喻戶曉的一部書——《三國演義》,以及各種戲曲和各類說唱藝術;經過多代的誇張渲染,曹操這個人,早已被一張平劇臉譜蓋住了,變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大奸大惡之徒。這和正史中的魏武帝有很大的參差。
後世研究史學,除了講求「史據」、「史料」之外,更著重於「史觀」,持平公正的歷史觀點,應該是大匠著書立說的龍骨,能撥開迷霧、重現歷史的真容,還給歷史人物一份公道,這是非常緊要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本著正統正朔的觀點,在書中隨處都可見到「揚西蜀而貶魏晉」意念,尤其對曹操的作為充溢不滿之情,這樣的史觀雖吻合多數民間的傳統觀念,實際上並不持平。
《曹操傳奇》這部書,雖說是「傳奇」,事實上卻緊扣著歷史的縱線,把筆墨用在樞紐漢末半世紀的曹操身上,最可貴的是「史觀」持平公正,寫得深刻而透澈,對長久以來神祕如謎的人物,有了客觀的品評和剖析。
事實上,歷朝歷代,身處滔滔亂世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有著多面的性格和複雜的心理狀態。曹操聰敏、機智、博學、勇毅、仁慈而又殘忍,他能夠在諸侯火併的亂局中闖出一片天來,正靠著他「靈活機變」高人一等的特性。「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現實是冷酷無情的,在當時,他和董卓、袁紹、袁術、張繡、呂布、孫策、劉表、劉備,都被投在一個烈火熊熊的時代大熔爐裡,每一舉措都攸關生死存亡,煉出來的就是精鋼,煉不出來就成了廢鐵,從群雄紛起到三國分據,就證明魏、蜀、吳的領導人物各有所長,全非簡單人物。
攤開漢末的地圖來看,曹魏所占據地區,全是人口眾多、物產豐足,工業發展良好的菁華地區,不論是兵員、物產、糧草、武器裝備,都優於蜀與吳;又曹操摩下可說是謀臣如雨,猛將如雲,若不是曹操求賢若渴、愛才如命,這些異士能人也不會抵死追隨他。
反觀東吳,偏處東南一隅,當時除江蘇南部、福建北部、江西、湖北之一部外,大多是未曾開發的荒蠻之境,地廣人稀,雖靠長江天險可割據一時,其工業、國防力終竟難和中原之地抗衡。至於當時的西蜀,人口數遠遜曹魏,工業力更形薄弱,南方更有孟獲威脅;孔明精於「數」,不可能沒有比評,他之六出祁山也祇能說盡人事而已。
曹操的後半生,經常頭痛欲裂,性情大變,極可能患有腦瘤,加上精神分裂,躁鬱加妄想所致。把病人看成惡魔也不夠公平,也正如杜甫形容古柏云:「落落盤據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任何人到曹操那個位置,閒言閒語都是免不了的,他一生不廢漢獻帝,自己不取而代之,他認定若是沒有他一力周全,天下更不知亂成什麼樣子,這倒是實在話,三分後的曹魏地區,百姓還是能夠溫飽的。
漢末的曹操確是詩人的地位,他的詩雄莽渾厚,瀟灑而具悲情,在《曹操》這冊書裡所引用的詩,哪一首不蒼古奇倔,確具大家風範?深夜展卷讀這樣一部好書,真是如飲醇酒,芳春透骨。痛飲後,復有一縷悲情,使人泫然欲泣。曹孟德本身,何嘗不是成功又失落的悲劇呢?而他回歸田園、閒隱青山的夢,終其一生也是漸行漸遠,永不回來了。
司馬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