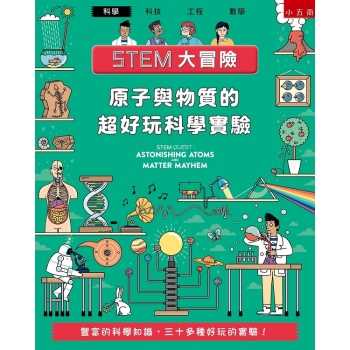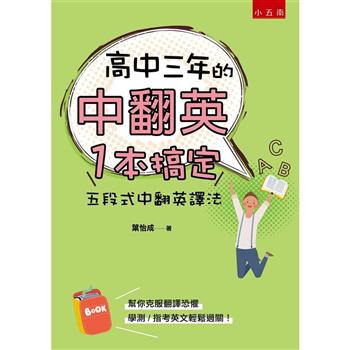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節錄自本書第二章〈毆期親尊長的律例規定〉)
第二節 修法爭議:「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尊本律」的探討
本節從一起道光四年(1824)〈江西司審擬文元毆死胞姪伊克唐阿〉案(下稱「文元案」)的覆議過程,探討清代「毆期親尊長」第11條例文修法突顯的問題。前人已有對此進行研究。顧元《服制命案、干分嫁娶與清代衡平司法》一書第二章,從毆期親尊長律本文的制定談起,次就「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死以次尊長致死」的例文演變論之。最後,則就《刑案匯覽》裡的實際判決情況析論。其指出,被尊長主使毆殺以次尊長的聽從者(筆者按:多指卑幼),是在道德和法律衝突時,無奈的犧牲者。該章所論已屬完備。不過,筆者認為,有若干細節可再行商榷,故仍選擇此議題再探討。
聽從尊長共毆以次尊長,也涉及「共犯」的議題。梁弘孟〈共犯關係下的「準服制以論罪」──以《刑案匯覽》「聽從尊長殺害以次尊長」類案件為例〉一文,以「親屬共同犯罪」的角度,探討清代的立法處置與實務運作。清代親屬互相殺傷的規範,計有謀殺祖父母父母、毆大功以下尊長、毆期親尊長和毆祖父母父母共4個門類,而服制可說是科刑論罪的重要因素。梁氏指出,在「準服制以論罪」的禮教立法格局下,即使官方確實有心減輕卑幼的不利處罰地位,但效果依然有限。梁氏的文章,融合現代刑法共犯觀念的解說,亦強調清代尊尊和倫常體系的展現,是本節在書寫模式上,可以注意和參酌之處。
綜上所述,本節採顧氏一文的書寫模式。先就清代「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以次尊長」例的沿革談起。該例經過乾隆十一年(1746)、嘉慶六年(1801)、嘉慶九年(1804)、同治九年(1870)的修改歷程,涉及「毆大功以下尊長」和「毆期親尊長」兩個律例門類,在這四個時間點中,刑部官員依照不同的形式,纂為定例或通行,甚至是門類的移改。其次,依序就該案的緣起、兩位江西道御史的意見、刑部之看法,以及《刑案匯覽》記載的裁判實態樣,逐一展開論述。
本節與顧氏一文的不同處有二。其一,「下手輕傷之卑幼,止科傷罪」存廢的議題裡,奏摺題本內敘及的一些制度用詞有再討論的必要。其次,道光十三年(1832)擔任江西道監察御史的俞焜,其主張恢復「不論下手輕重,悉照本律問擬」的例文規範。本節欲從其在道光十四年(1833)的一份奏摺裡,再次證實其「維護倫常」的積極心態。此外,檢視曾任刑部尚書的薛允升對該例文的評析意見,疏理「聽從尊長共毆以次期親尊長」的修法脈絡。
一、有關毆大功以下尊長
例文的制定和改變,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應對。在探討「聽從尊長共毆以次期親尊長,止科傷罪」的修例問題前,有必要先就史料內相關立法資訊的「前因後果」進行提點和爬梳。意即,「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原先的例文規範如何?其實,聽從尊長共毆的狀態,並非剛開始就規定在「毆期親尊長門」內,而是先從「毆大功以下尊長門」發跡,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大學士會同九卿議奏定例,纂輯遵行:
「凡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姊及尊屬致死者,除實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仍照律減等科斷外,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疊毆多傷致死者,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
從定例的內容可知,即使是迫於威嚇,聽從尊長毆尊屬的情狀,仍要照律科斷,惟可以減等;至於尊長如果僅令毆打,而卑幼做出逾越尊長預期的情事時,按例規定,將下手之犯(不論是尊長或卑幼)擬斬監候。這是「卑幼聽從下手」的原始規範。
嘉慶六年(1801),刑部意識到「凡人威力主使」和「毆死期親胞兄」身分等差的不同,應論以不同的罪刑,故又進行例文的內容調整,將其改為:
「凡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及尊屬致死者,審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照威力主使律,為從減等擬流。若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迭毆、多傷致死者,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至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長、尊屬之案,仍擬斬立決,夾簽聲請。其聽從下手毆死緦麻尊長、尊屬之案,依律減等擬流。」
例文有很明顯的增刪。特別是原先「按律減等」的律,更明確指出是「威力主使律」外,後半部分新增「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長、尊屬」,仍擬斬立決,夾簽聲請。夾簽的規定,自始出現在例文內,至於修訂的原因是:
「威力主使,毆死凡人,將主使之人,絞候;聽從下手之人為從,減等擬流。若毆死期親胞兄,則不分首從,俱擬斬決。二條分別輕重、詞義明顯。至毆死大功兄一條,律例既不言,皆自應分別首、從,但究係服制攸關,未便竟照凡人為從,一體擬流,其應如何與凡人分別治罪之處,律內又無明文。若因係為從,俱減等杖流,是毆死功服尊長與毆死凡人毫無區別,推原律意,必不若此,自應酌定章程,免致參差。」
刑部比照威力主使,凡人論罪科刑和毆死期親胞兄的規範,認為兩條輕重分明,但是,有問題的是毆死大功兄,既然律例未明文,那麼依照首從來分更為妥適。只是刑部考慮到服制,若跟凡人同等論罪科刑,則絲毫無區別實益,從而,應酌定章程,避免參差辦理。
尚待解決的問題,還有「照律減等科斷」應如何解釋。刑部認為,係指「照威力主使律,為從減等」,可是並未晰明,故應增改;又聽從毆死期親尊長尊屬的案件,向來按照情輕之例,夾簽聲明,亦應敘明其中。嘉慶九年(1804),由於「主使之尊長」應如何論罪,例內未聲明,導致各省辦理不畫一,修法的問題再浮出檯面,此次例文改成:
「凡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及尊屬致死者,除主使之尊長,仍各按服制以為首科斷外,下手之犯,審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照威力主使律,為從減等擬流。若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迭(疊)毆、多傷致死者,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至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長、尊屬之案,仍擬斬立決,夾簽聲請……」
例文很明顯地區分主使之尊長和下手之犯如何論罪的問題,原則上,主使之尊長要求按服制以為首論處,而下手之卑幼如修法前的規定,擬斬監候。至於為何修改,刑部指出,乾隆十一年之例雖已纂入例冊,成為定例,按照邏輯推斷,聽從下手的卑幼,既然以為從定擬,則主使的尊長,自然要依服制,以為首論。可是,由於未在例內聲敘主使之文,所以各省在辦理時,有的按照服制,將主使之人為首科斷;有的按照餘人定擬,導致辦理時的不足畫一。歷經駁改,仍屬例無明文,故此次修例納入例內,以昭完備。
以上是「毆大功以下尊長」卑幼聽從尊長共毆的情形。然而,毆期親尊長門相關例文的制定,直到道光四年(1824)才正式編纂成例。同治九年(1870)將「毆大功以下尊長門」第4條例文「毆期親尊長」部分獨立後,未再做任何修改。
二、有關毆期親尊長
「卑幼聽從尊長共毆以次期親尊長,止科傷罪」的規範,其實直到道光四年和五年,才以「續纂」的理由編入「毆期親尊長」門的例文裡,在此之前,法無明文,故以相類似案件援引,不過,在例文修訂後獲得一段時間的適用,內容是:
「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尊屬致死,若主使之尊長亦係死者之期親卑幼,如聽從其父共毆胞伯,及聽從次兄共毆長兄致死之類。律應不分首、從者,各依本律問擬。核其情節,實可矜憫者,仍援例夾簽聲請。其聽從尊長主使,勉從下手共毆,以次期親尊長致死,如聽從胞伯共胞叔,及聽從長兄共毆次兄致死之類。係尊長下手傷重致死,卑幼幫毆傷輕,或兩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內一卑幼傷重致死,一卑幼傷輕,或內有凡人聽從幫毆,係凡人下手傷重致死,承審官悉心研訊,或取有生供,或供證確鑒,除下手傷重致死之犯,各照本律、本例分別問擬外,下手傷輕之卑幼,依律止科傷罪。如係刃傷、折肢,仍依律例分別間擬絞決、絞候,不得以主使為從再行減等。」
至此下手傷輕的卑幼止科傷罪,已明顯成為定例,供斷案者作為審理案件時的依據。
當然律例在實務運作上,仍可能產生不足之處。因此,道光五年至十四年該條例刪除之前的這段期間,又續纂:「期親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以次尊長、尊屬之案,無論下手輕重,悉照本律問擬斬決。法司核擬時,夾簽聲請,恭候欽定。不得將下手輕傷之犯,止科傷罪」從例內提醒要求仍照本律擬斬、法司核擬夾簽聲請的情形來看,「下手輕傷止科傷罪」的問題逐漸在實務上被重視,認為應當再次解釋並納入立法裡。所以這般爭議,在道光四年覆議和十三年的通行裡被提出討論。
道光十三年的通行,刪除「聽從尊長共毆,下手卑幼止科傷罪」的例文後,同治九年(1870),該條修改「訊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至死者,仍照本律問擬斬決」字樣在「尊屬之案」下面,例末也新增「不得將下手輕傷之犯,止科傷罪。如尊長僅令毆打,輒行疊毆多傷至死者,即照本例問擬,不准聲請。道光十五年續纂,同治九年修改」顯見,「卑幼聽從尊長止科傷罪」在「毆期親尊長門」的部分,隨著道光至同治年間的例文內容修改,爭議結束。
綜上所述,「毆大功以下尊長」和「毆期親尊長」都有論及「卑幼聽從尊長共毆」這個議題,雖屬不同脈絡,卻相輔相成。在「毆期親尊長」第11條例文未制定前,定例的編纂入冊,是頗為重要的事情,原因在於,若遇到案情相類似的案件,如何定擬斷案,得到最適切的法律適用,是刑部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例的沒纂入例冊或未敘明清晰,終會成為審理案件時的阻撓。所以,乾隆十一年和嘉慶九年的例文修訂,才要求例文內容規定明白且愈趨詳細,另外在審判實務方面,既然未入例冊,則參照卑幼下手輕傷和聽從尊長之例,將卑幼聲明夾簽、論罪科刑,以求合適、符合服制的律例適用。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清代司法實務中的錯誤︰以《刑案匯覽.毆期親尊長》為中心的圖書 |
 |
清代司法實務中的錯誤:以《刑案匯覽.毆期親尊長》為中心 作者:王學倫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24-11-2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64頁 / 14.8 x 21 x 1.3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清代司法實務中的錯誤︰以《刑案匯覽.毆期親尊長》為中心
清代律例延續唐、明兩代的概念,比禮制所稱的期親範圍更廣。《大清律例》的「毆期親尊長門」計有13條例文,其定罪量刑的原則是,不同身分和不同情狀,應以示區別。當毆期親尊長案件裡的律例和司法實務衝突時,作為司法審判者的刑部,會嘗試綜合事實和律例,作出適當的審判,目的只有一個:追求情與罪的平衡,尤其是毆期親尊長這類涉及服制和尊卑議題的案件。
靜態的法條和動態的司法審判是法律史研究的主要課題。本書以《刑案匯覽》為史料,針對「毆期親尊長門」記載的案件進行分類,以及刑部法律推理的探討。分類方面,強調錯誤類型的區分,並以說帖事實描述為標準,指出刑部或律例館官員認為下級審斷案錯誤之處。法律推理部分,注重各別律和例實際的適用結果,特別是遇到疑難雜案的案情時,刑部如何論處。
作者簡介:
王學倫
輔仁大學歷史學暨法律學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專任助理。參加「中國法制史學會」及「唐律讀書會」。對清代法律史課題有高度的興趣,同時關注中國各朝法律制度如何在國家及社會之間被實踐。
章節試閱
(*節錄自本書第二章〈毆期親尊長的律例規定〉)
第二節 修法爭議:「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尊本律」的探討
本節從一起道光四年(1824)〈江西司審擬文元毆死胞姪伊克唐阿〉案(下稱「文元案」)的覆議過程,探討清代「毆期親尊長」第11條例文修法突顯的問題。前人已有對此進行研究。顧元《服制命案、干分嫁娶與清代衡平司法》一書第二章,從毆期親尊長律本文的制定談起,次就「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死以次尊長致死」的例文演變論之。最後,則就《刑案匯覽》裡的實際判決情況析論。其指出,被尊長主使毆殺以次尊長的聽從者(筆者按:...
第二節 修法爭議:「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尊本律」的探討
本節從一起道光四年(1824)〈江西司審擬文元毆死胞姪伊克唐阿〉案(下稱「文元案」)的覆議過程,探討清代「毆期親尊長」第11條例文修法突顯的問題。前人已有對此進行研究。顧元《服制命案、干分嫁娶與清代衡平司法》一書第二章,從毆期親尊長律本文的制定談起,次就「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死以次尊長致死」的例文演變論之。最後,則就《刑案匯覽》裡的實際判決情況析論。其指出,被尊長主使毆殺以次尊長的聽從者(筆者按:...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推薦序】用繡花針勾串歷史的幽微處
陳登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法學領域中的法制史研究議題,曾有過「虛學」與「實學」的爭論。其爭點是:法律系的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都準備從事司法實務工作,而法制史研究往往被視為「虛學」而不是「實學」,所以法律系的學生不太讀法制史。特別是國家公務員考試取消「中國法制史」之後,法制史更被視為冷門學科。另一方面,歷史系的學生也不太讀法制史,因為害怕自己的法學素養不夠,專業訓練不足。兩科系的人都有其對法制史研究的疑慮,因此法制史研究相對於其他領域就顯得比較不...
陳登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法學領域中的法制史研究議題,曾有過「虛學」與「實學」的爭論。其爭點是:法律系的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都準備從事司法實務工作,而法制史研究往往被視為「虛學」而不是「實學」,所以法律系的學生不太讀法制史。特別是國家公務員考試取消「中國法制史」之後,法制史更被視為冷門學科。另一方面,歷史系的學生也不太讀法制史,因為害怕自己的法學素養不夠,專業訓練不足。兩科系的人都有其對法制史研究的疑慮,因此法制史研究相對於其他領域就顯得比較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叢書」出版緣起/陳惠芬
推薦序 用繡花針勾串歷史的幽微處/陳登武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清代審判制度概論及裁判實態舉隅
第三節 研究回顧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二章 毆期親尊長的律例規定
第一節 毆期親尊長律例的沿革
第二節 修法爭議:「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尊本律」的探討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刑部「毆期親尊長門」案件的類型
第一節 誤傷誤斃期親尊長
第二節 聽從親屬或他人為之的犯罪
第三節 救護情切和有心無心相關案件
...
推薦序 用繡花針勾串歷史的幽微處/陳登武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清代審判制度概論及裁判實態舉隅
第三節 研究回顧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二章 毆期親尊長的律例規定
第一節 毆期親尊長律例的沿革
第二節 修法爭議:「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尊本律」的探討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刑部「毆期親尊長門」案件的類型
第一節 誤傷誤斃期親尊長
第二節 聽從親屬或他人為之的犯罪
第三節 救護情切和有心無心相關案件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