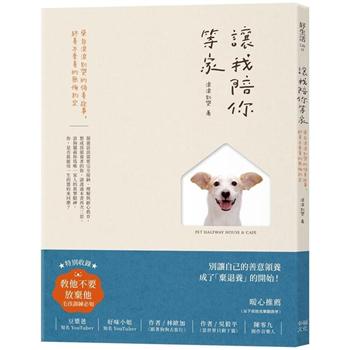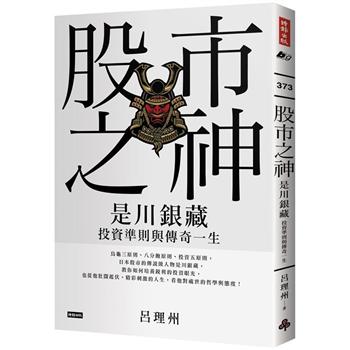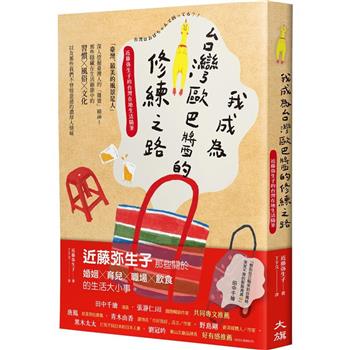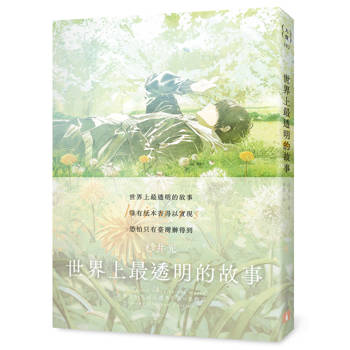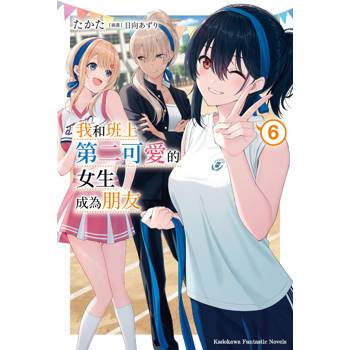前言
從數據之外看見美國社會真相
約翰.傅利曼
去年冬天,我飛回故鄉加州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在一個和暖的十二月夜晚,我穿上外套來到室外,步行至一個離議會大廈並不太遠的書店。
很快地,就像在其他的大部分美國城市,有人迎向我,跟我要錢。他們每一個人──清一色都是男性,而且也都說得出理由︰賞幾個小錢讓我過節吧!給退伍老兵一塊錢吧!有錢讓我買點吃的嗎?……他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只在要求一個最起碼的仁慈與施捨而已,就是︰你看到我了嗎?你會幫我嗎?當然,即便是我們當中最拮据的人,身上也總有一兩個銅板可以給餓肚子的人。所以,我給了,而且總是如此。雖然,我知道那些理由很可能只是個藉口,拿了錢卻去做別的事﹔但我無法對另一種可能性視而不見:他們真的有需求,而且境況悲慘。
在跟最後一個要錢的人聊完幾句後,我繼續步行,來到了目的地,在這個讓我沮喪又似曾相識國度中的書店。那年的秋天與冬天,我多次旅行,也在每一個我抵達的地方,看到了不友善的美國。一些固定重複的字句不斷在芝加哥、在西雅圖;在波特蘭、在邁阿密聽到:有零錢嗎?能幫個忙嗎?有錢賞給退伍老兵嗎?然而,還是有很多人就直接擦身而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因為大部分在美國居住或工作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理會這些請求;更精確地說,就是拒絕相互的人道關懷以便過自己的日子。但是,我的沮喪卻另有原因。事實上,去年十二月我飛到沙加緬度,是為了在「時間測試書店」(Time Tested Books)參加一個活動,那是一家二手書店,所討論的議題正是紐約的無家遊民與社會不公。我剛出版了一本文集,叫作《雙城記:當今紐約最好與最壞的時刻》(Tales of Two Cities: The Best of Times and Worst of Times in Today’s New York)。我之所以想要出去街上走走,是因為那本書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是出自親身經歷者之手,出自以個人步調看見紐約的人;所以,能發現故事本身說不出來的部分。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之後,了解到我記憶中的沙加緬度是一個被我以汽車速度來觀察的城市。我已記不得與祖父的任何一次散步,他在1933年搬來這個城市,而且幫忙蓋了我們做禮拜的教堂;我也記不得跟我父親的散步,他是在祖父搬來六年之後出生,而且在城裡長大;我當然也記不得有沒有跟弟弟散步,我和他是在1984年由賓夕法尼亞搬到沙加緬度郊區。我們總是開車,停車,然後步行一小段距離,就到了目的地。現在,三十年之後,我安步當車,而且看到了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城市;我都懷疑我是否曾經到過這些地方,還是有些重要的東西已經改變了。當我走到二十一街時,我開始更無奈了,因為我是到沙加緬度來談論紐約,但就在那當下,一個穿著牛仔褲和工作服的男子跨入了我的動線,看起來像是要問路。他是要問路,他問道:「先生,你知道流動餐車在哪嗎?」這完全顛覆了我記憶中的加州首府印象。
分裂的美國社會已成不爭的事實
美國是分裂的。你不需要一大堆的統計數字就可以知道。你只需要眼睛、耳朵與故事。去任何一個美國城市走走,破碎的社會縮影與人民生活的證據會自己呈現。在這些地方,你會看到損壞的馬路、超過人力負荷的學校、站在路邊的警察。有時候,成群結隊甚至看起來是整個城市中的無家可歸遊民,就在購物商場的視線範圍之內搭帳篷露宿,弔詭的景象反而有點像是有錢人的堡壘,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商場了。厚重的玻璃櫥窗與保安人員,就站在讓人夢寐以求的商品之間,但人們卻遠隔在外,這樣的場景在奧勒岡的波特蘭、在舊金山、在西雅圖、洛杉磯、紐約與邁阿密,隨處可見。高漲的生活成本,將這些地方變成奢華與創造性經濟活動的朝聖之地,只是卻必須依賴服務業的勞工來操作巨大的夢想機器,這與政府的作為有很大的關係。這些城市的中產階級居民,在薪資被租金與生活成本抵銷之後,擁有最低的實質收入。若放大到全國來看,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所賺取的收入相當於底層90%的人的九倍。
這不只是一個大城市的問題。在較小的城市鄉鎮,和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有錢人與沒錢人之間的鴻溝同樣寬廣,即便這些病癥並非如此易見。加州可能有超過百位億萬富翁,他們的總資產可以讓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的國民總生產毛額相形見絀,但卻有四分之一的加州人還很窮。因為有愈來愈多以前用手工完成的工作,現在改用機器來做。其他如阿帕拉契地區、紐約上州(upstate New York)、密西根,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也延展成難以想像的鴻溝。就算有人聽到許多關於經濟復甦與新工作機會的訊息,但這些新的工作通常都是短期的臨時工作,或是沒有福利的工作,由於工作如此短暫,甚至連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出來代表這群勞工:無保障無產階級(Precariat)。不過,這種社會不安倒成了2016年總統選舉的軸心議題。
政策對老百姓施暴
財力上的不公平,並非不良公共政策下的一個病癥,或是與選舉的力道串聯出現。這是幾十年以來美國的不正義與結構性不公平所塑造而成,其肇因有:以剝削勞工作為墊背而獲得經濟成長;產業結構重組失敗;文化中種族偏見的鴻溝;對移民的限制以及移民法律的執行不當;對毒品、性別偏見,性別不平等戰爭的餘波;以及金融服務業與掠奪式的貸放制度把受不公平所苦的人當作祭品等。幾十年來,美國都還沒有實施過任何有意義的累進稅率制度。美國這個曾經活力十足的福利國家所確保的任何人民福利,都已經因為深陷泥沼的制度性不公平而被破壞,使得處於風險當中的事物遠超過向上的社會流動,而且還將人民推入火坑。威廉.巴柏二世牧師(William BarberII)去年稍早在北卡羅來納夏洛特(Charlotte)的警察開槍致命事件後寫了一篇文章,他的看法是:當夏洛特貧苦黑人社區在與毒品的戰爭中被不成比例的執法偏執所折磨,大家譴責整個世代的不良債信與缺乏工作機會時,我們所選出的民意代表並不把這些視為制度暴力。當移民官員到家裡突襲,從公車站抓走沒有證件的幼童時,他們也不認為這是粗暴。但是,所有這些政策與執行,都在對好幾千位夏洛特居民的生命施暴。
壓抑性的制度已在美國根深蒂固,所以在提到不公平的議題時,甚至需要一個新框架來自圓其說。但我們必須看到統計數字與工資比率之外的真相,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可以說明住在美國是什麼樣感覺的框架,一種為事實提供故事空間,以便顯示出在工資之外,還有多少力量導致了所得不均衡,而這是不公平世界中的一個病癥。幾十年以來,陸續有許多作品發表,作者們除了專注於這些力量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本書就是試圖把最好的作者聚在一起,並且用他們的文字來重新述說美國的故事。
用文字重新描述立足美國的真實感受
一篇接著一篇,你會看到這些作者拆解了霍瑞修.艾爾傑(Horatio Alger,19世紀美國多產作家,其作品的主人翁都是白手興家致富,被視為「美國夢」的代表)的秘密,並以今天要在美國保有立足之地的真實感受取而代之。在曼紐.慕洛茲(Manual Munoz)的尖銳散文中,向他垂死的父親致敬;他從中非洲來到美國,光靠採收萵苣和棉花這類幾乎快消失的工作,卻能支撐一整個家庭的生計。美國桂冠詩人璜.菲律普.耶雷拉( Juan Felipe Herrera)貢獻了一首短詩,給那些沒有名字、沒有證件卻仍然在努力掙扎的工人們。愛德維琪.丹堤卡特(Edwidge Danticat)如魔咒般地喚醒了一位居家護理員,她的前男友回來向她尋求金錢的援助,因為他的新太太被綁架回了海地。
美國的問題確實並不只是落腳於美國境內.它們追隨著在地人口生根。詩人羅倫斯.約瑟夫(Lawrence Joseph)述寫著結構性的全球緊張力道被帶入底特律,那是個把工作機會輸出到海外、毀在落跑製造業手中的城市。提莫西.依根(Timothy Egan)仍然記得在西雅圖可以找到足以養家活口工作的日子,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小說家理查.羅梭(Richard Russo)所思考的是,當一個人的工作被奪走,會對他們的尊嚴產生多麼大的震撼,又將如何摧毀他們的靈魂。只是,除了束手無策之外,你還能做些什麼呢?莎拉.史馬許(Sarah Smarsh)的弟弟,像成千的美國人那樣,跑去找堪薩斯州的血漿公司賣自己的血漿。RS 迪倫(RS Deeren)的短篇故事中,講到兩位密西根男人在銀行最近重新回收的房子割草,這下他們可有做不完的工作了。潔絲.盧理福森(Jess Ruliffson)所描述的是退伍軍人從伊拉克回到北美大平原區,正面對著不確定的就業機會。
上述種種,當然無法阻止新家庭來到美國,只是想要走下貧困的階梯,難度更高而已。此外也有「美國究竟是什麼」的認同感危機,以及誰才可以算是個美國公民這樣的問題。在茹.傅利曼(Ru Freeman)的短篇故事中,提到了管家和保母的生活,他們身處一個家庭的正常運作軌道之中,但卻享有非常少的福利。派翠西亞.恩格爾(Patricia Engel)在她的散文中描述一些產業從古巴、加勒比海地區、墨西哥以及其他現在被稱為邁阿密家園的地方,引進勞動力;而於此當下,在同一個城市中的白種人,又如何依據種族的純粹性與排他性,重新界定他們對「家園」的概念。麗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對於舊金山槍擊案件的震撼性說明中,敘述被害人住家的鄰近地區屬於「城市優化區」,這應是導致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在被害人死亡那天打電話給警察的人們,如果已經在那個地區住了好幾年的話,應該都會認識他。
當警察不再是有色美國人的褓姆
警察與他們所應保護的人民處於一種對抗關係之中,這太常見了。在娜塔莉.迪亞茲(Natalie Diaz)強而有力的詩作中,傳達了一個事實:美國的原住民佔總人口不到1%,他們遭到殺害的比率,卻令人驚訝。「當我們瀕臨死亡,」她寫著;「該向誰求助?」凱斯.雷蒙(Kiese Layman)在他的出色散文中,回憶起一位朋友在他當時所在的大學城被逮捕,原因是被指控從事許多在校學生會做的事──賣毒品。不過,在他朋友的例子中,因為他不是學生,所以執法變得更加迅速、而且更為嚴厲。警察和有色美國人之間關係的崩壞,讓人有種兩個美國的感覺,一個黑的,一個藍的;美國告訴自己,夢想是可能的,只是,給人的感覺不像是一個夢,而是一個謊言──詩人達內斯‧史密斯(Danez Smith)在他的美麗詩篇中,環繞著這個主題。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很久了,凱文.楊(Kevin Young)在他的詩作《嚎叫的狼》中提醒我們︰需要一首抗議歌曲來發洩!
面對著這些活生生的事實,白種美國人要如何自處?他們要怎樣認知到這點,而同時又尊重不同族群的抗議?他們該知道,這些共同住在美國的兄弟姊妹們,若要為自己發聲,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在喬艾絲.卡羅.歐提斯(Joyce Carol Oates)的故事中,一位年長的白人婦女拜訪一間美國黑人教堂,那兒正在舉辦一個「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活動,卻發現自己像是個入侵者,而這樣的直覺也讓她有一番新的自我認知。
尤拉.畢斯(Eula Biss)在他的散文中,把觀念從「白種人的原罪」(white guilt)改變到「白種人的債務」(white debt),這是一個在面對身為白人的經濟好處時,遠遠較為有用的想法。布萊德.華生(Brad Watson)早年在密西西比時,就學到了這樣的課題,當時他的母親雇用了一位有色婦女做他們的管家,而她每日的工資卻比他割草幾個小時的收入還少。
長久以來,教育就被放在一個制高點上,認為是可以為美國糾正其歷史和文化上的體制性不平衡的方法。而本書有好幾篇文章,都在檢視這種公式當中的漏洞。克絲汀.佛達茲.郭德(Kirstin Valdez Quade)記得,他在一所菁英中學的暑期課程中擔任顧問時,一位西班牙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因為缺乏學校的支援而無法通過一項計畫,雖然那位女孩的多元背景極為適合。郭德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強烈的爭議︰為什麼參與這些計畫的學校,為了增加多元性,所以在學生一開始入學時,就訂作了許多要求。達格柏圖.基爾布(DagobertoGilb)在洛杉磯與德州長大時,這種計畫並不存在,學生必須為自己創造可能性,所以我們可在他的自傳中看到他為了達成目標的苦惱和必要的缺課。在文娜美(NamiMun)的短篇故事中,兩位家長為他們的子女犧牲了一切,以便讓孩子擁有自己不曾有過的機會,但當債務壓垮他們時,只好付出最終的代價。
喚回對不同族群的關懷與寬容大度
來自這些文章的一個最強大的覺知,是有關我們這個時代的倫理。知道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可以過著怎樣的日子,而其他人並不能享有同樣的舒適?在海克特.圖巴(Hector Tobar)的自傳中,他回憶一則有關幫派槍擊的傷害報導,一位與他兒子年齡相仿的年輕男孩,就住在洛杉磯緊鄰他家的地區。同樣的,愛達荷州的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與孩子忙了一天之後,疲倦地回到家中,卻發現一個男人把車停在他的車道上,可能在車裡睡著了。他感到疑惑,這個人是誰?又是什麼原因把他帶到這條死巷?他是疲倦了,或只是恍神罷了?哪裡是他的壓力落點?哪裡又是沒有壓力的?在一種急著要剝離社會連結的文化中,幾乎隨處就可感受到無所不在的殘酷。喬伊.威廉斯(Joy Williams)的故事中,說了一個緬因州男人準備要拆除富有政客的房產,雖然這位已故政客不在場了,但他的房子跟藏酒,卻凸顯了有錢人為囤積而囤積的荒謬。
所以,有一種疏離不和的感覺正在美國潛伏。這種感覺存在於人們的生活中,存在於美國人彼此的互動中,存在於我們所有人搶著要改變的地方。在詩作《看得見的城市》(Visible City)中,瑞奇.羅倫提斯(Ricky Laurentiis)希望可以使所有城市能在他的紐奧良地區更具能見度。賴瑞.華特生(Larry Watson)則哀歎北達科達州俾斯麥市(Bismarck, North Dakota)的沒落,他曾一度認為那是家鄉;在那兒,有錢人與中產階級住在同一個街區當中;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環繞著城市堆疊的教堂,在當時殊難想像。克里斯.歐福特(Chris Offutt)也惋惜這種改變,但他並不想把他繼承的遺產當作「垃圾食物」那樣,賣回給有錢的買主,而讓自己成為有財力的工人階級發言人。
在美國,如想做成一件事,往往必須要離開家鄉,並與新環境搏鬥。松卓.西奈布羅絲(Sandra Cisneros)記得那個養大她的芝加哥是如何訓練她離開,以便她求生存並成就自己。但另一個對於人格特質的更大威脅,卻在等待著羅珊.蓋(Roxane Gay)短篇故事中的女性:由暴虐、無業的醉漢父親扶養長大,嫁給不會控制體重的丈夫,她們可以感受到必須逃脫的時機,並隨時準備跑開。克萊兒.費.華特金斯(Claire Vaye Watkins)記得她長大的地方有許多房子與拖車,在她們的母親團團轉著快要放棄之際,她與姐姐是如何互相觀望與扶持。
我希望在美國,大家仍然存有一種足夠寬廣的關心。人們會伸出援手,並不只因為那是適合他們去做的一種行為,而是因為正確該做的事——這也就是我們該怎樣過生活。安妮.迪拉(Annie Dillard)把這個想法推薦給作者們,在他們有點搞不清楚為何而寫的時候。輝特尼.泰瑞爾(Whitney Terrell)也對隔壁鄰居施以大度,然後卻了解到他正在進入一種如此複雜的期盼網絡之中。安.派卻特(Ann Patchett)記得在納許維爾的一位傳教士,靠著信仰以及他做過的所有好事來過日子。而在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凱倫.盧賽爾(Karen Russell)描述著一個無居所遊民的問題是如此巨大,以致於蔓延在所有公民間的一種流行性慷慨行為,也許正好就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這樣的說法聽起來或許陳腐,但在美國,我們的問題解決之道,是存在於我們之間,不是在我們之上,當然也不是讓我們失望的政府。也許就像某一晚茱莉亞.阿佛爾瑞茲(Julia Alvarez)在回佛蒙特的家的路上,碰到所有人該做的一切事情,就是擠在同一個機場過夜,她了解到人與人之間的薄薄界線,可以很容易被一個分享的經驗就打破。阿佛爾瑞茲觀察到所有膚色與不同背景的人們,彼此相互幫助,找睡覺的地方,分享包裹身體的毛毯和食物。在美國,如果我們只檢討有需要的人會感覺苦惱的種種不公平問題,那將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因為,唯有分享,我們才能緩解這個讓大家都很痛苦的情況。
在我離開那位找流動餐車的人之後不久,有一個過去在沙加緬度的經驗浮現心頭。記得是1986年的耶誕節。在那些年當中,我父親在一個以家庭為服務對象的非營利組織擔任主管,進行毒品與酗酒更生計畫,並為老年人流動送餐,也對無力負擔費用的家庭提供諮商。那一年,他認為把我們帶到沙加緬度的南邊,去送玩具與火雞給貧困家庭是個好主意。所以,我們就把休旅車的行李箱塞滿了食物與禮物。
那時候,我有一張紙本的地圖,每個月我必須在城裡的鄰近地區騎好幾英哩腳踏車,去收《沙加緬度蜜蜂報》(Sacramento Bee)的報費,送到家是八塊五毛錢。我通常是敲門,大部分的都人會付錢,但從來沒有人邀請我進入家中,不過有一小部分的人會躲著我。有誰會不願意付錢給一位十一歲的小孩?人家每天早上五點半就騎車來到你家門口送報?所以,躲著我的這一群人讓我很不解。他們那兒也有著各種不一樣的房子,就像耶誕節我們曾經拜訪過的地方。即使在冬天,紗門也是打開的,狗看起來不是特別友善,但人是友善的。那個假日,我們開車挨家挨戶拜訪,被邀請入內,受到歡迎,即使感覺有點不自在,也互相擁抱,不過有位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少年卻跑開了,因為他哭了出來。我記得父親站在別人家的起居室,問他們是從哪裡來。
我的父母從不曾告訴我這些拜訪應有的意義,因為那很清楚,無須解釋。回到自己的家以後,我的感覺很不真實。為什麼我與我的兄弟可以在這裡成長,而不是我們剛剛拜訪過的家庭,雖然其中不見得有什麼偉大深奧的理由,也許就是宇宙主宰的神祕手指碰觸到一個不同的按鈕,我們在美國的每一個人,就長成了不同的個體。在之後的歲月中,我的兩個兄弟都曾在不同的時段短暫無家可歸;從這當中,我發現伴隨著舒適安逸而來的,是社會階梯就從你的腳下滑落了──這又是多麼的公平啊!只是在當時並沒有我所需要的故事來了解到這樣的可能性,我不過只經歷了一段旅程而已。感謝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