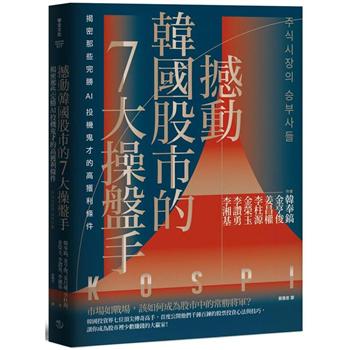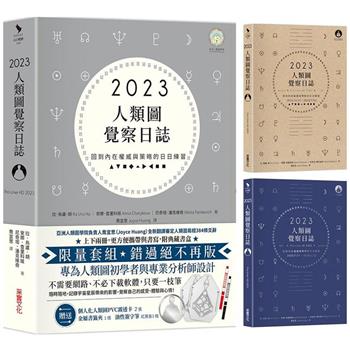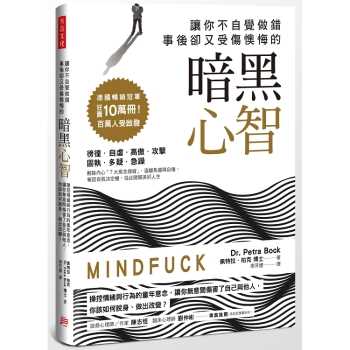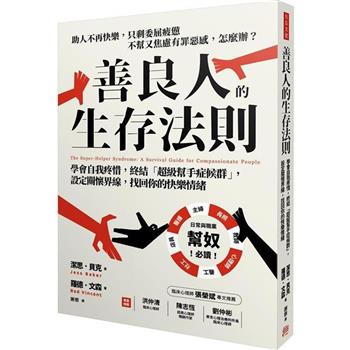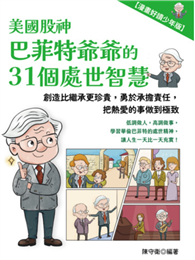【推薦序】
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一頁
◎陳志平(湖北省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院長)
周博士所撰寫的《康僧會大師》,是一部專以學術史的角度,將三國時期從交趾至東吳建業傳揚佛法的高僧康僧會,其一生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歷史定位,從歷史、地理、考古、康僧會所編譯的佛經,以及康僧會在儒、釋、道三教的貫通上,使「佛教中國化」得以被確立,以致形成唐代詩人杜牧所形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盛況的歷史原因及其脈絡,予以完整而系統的說明。
此外,藉由周博士以大量的歷史、地理及考古所進行的分析,使三國時期江南至交趾的水路交通狀況,可以得到更清晰的梳理。也正是因這項梳理,使我們認識到,秦始皇時期,江南的水陸交通儘管早已開鑿,但從交趾北上,不僅得翻越極險峻的鬼門關,還得走過一段又一段湍急而迂迴的水路;若不是有極大的願心和極大的勇氣,誰會甘冒如此險阻,願意從交趾一路走到建業傳法。學術史上對這項內容的梳理比較欠缺;但若少了這一段,對康僧會至江南傳法的堅決與毅力,便無法得著更全面的認識。
傳世文獻關於康僧會的記載,確實相當貧乏。目前學界對康僧會的研究,成果比較顯著的是越南僧侶;他們在康僧會的研究上,更看重的是康僧會所受佛教教育的傳承,以及康僧會所編譯的佛經,內容受到越南民間故事的影響程度。這些研究成果,固然可幫助我們對康僧會所編譯的佛經有更廣泛的解讀角度;但對康僧會何以能被梁代釋慧皎收入《高僧傳》中、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恐怕仍是無法得著全面而充分的認識。
藉由周博士《康僧會大師》一書的研究,使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佛教中國化」之所以能在江南紮根、使江南能為佛教而專門興建寺院,又令「寺」從官署轉變成為佛寺的專屬代稱,使原本對佛教還相當陌生的江南,終於成了佛教傳播的重要搖籃,這個根基的確立,竟是在一位出生、成長、受教及出家都在交趾的康居國人康僧會手中所成就的。
康僧會的祖上早從康居國移居天竺(今印度)經商,之後康僧會的父親康北沙,又從天竺轉移至東漢時期交州的交趾經商和定居。當時的神州大地,正經歷著戰火;所幸交州郡太守士燮,對北方南下避難的讀書人格外的照顧和禮遇,使得交州在當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被大力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據點。
正因如此,在交趾出生,又得士燮為康僧會挑選名師教導的優勢條件下,使得原本即相當聰穎又極好學的康僧會,四十歲時便已將儒、釋、道三教完全融會貫通。這個極重要的關鍵性條件,促使了康僧會既得以實現其北上傳法的具足條件,也讓於「佛教中國化」上推波助瀾。這個最關鍵的成果,就展現於康僧會所選定而加以編譯的《六度集經》。
《六度集經》雖都是佛陀前世的本生故事,但有些故事的內涵,是與儒家和道家思想特別相近。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旦讀到《六度集經》,便會自然而然地與所受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著思想性的連結。正因如此,周博士在本書第二部分之壹「展現救世精神的《六度集經》」裡,才會在某些與儒、道家思想最貼近的故事下,進行儒家及道家思想的說解;目的就是為凸顯出,康僧會在當時極迫切需要翻譯佛經的歷史條件下,何以會特別挑選《六度集經》進行編譯的極重要關鍵。康僧會想讓佛教的某些內容,能先與儒、道兩家思想進行相當的串聯和融合,甚至將佛教予一定程度的中國化,如此才能便於知識分子接受和學習。
透過周博士的研究,也使我們能認識到,令大、小乘佛法能在漢地得已逐漸完全融合,亦是康僧會在佛教思想上的一項重要工作。正當大、小乘佛法還在當時的佛教世界裡爭論不休時,康僧會卻能在譯經上為兩者進行融合。如此創舉,除了使大、小乘佛法的爭論可在尚非佛教世界的漢地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消,也能令大、小乘佛法得著開創性的調和,可說是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一頁。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對康僧會的研究,幾乎較少梳理到敦煌莫高窟三二三石窟《康僧會建業布教圖》。周博士在本書第二部分之貳中,卻能在史料的基礎上說解這幅圖,使我們對康僧會在佛教史上的地位能有更深刻的認識,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周博士的《康僧會大師》,將我們對康僧會從陌生一步步帶到了熟悉,瞭解康僧會何以能成為高僧的關鍵。康僧會這位在交趾出生、成長、受教和出家的康居國人,對中國文化與佛法所進行的融合與交流,實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歷史樞紐。
【編撰者序】
「佛教中國化」的大功臣!
《高僧傳》的出現,不僅將自古以來的佛教典範偉人一一記錄下來,同時也記下了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歷史進程。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後,便一直處於極尷尬的局面,不僅上層貴族弄不明白,飽受儒、道思想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會自然而然地抗拒,使得佛教思想的傳播一直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極大的障礙。正因如此,如何讓佛教能在中華大地上被認可、被傳播、被重視,並形成一普及的思想,便成了歷代高僧所要努力的極重要目標。
國籍康居、卻出生在中華大地上的康僧會,因父親曾在天竺經商,便使他自幼可耳濡目染地學習到從天竺所傳入的佛教思想;此外,康僧會也比任何人都更有機會學習和掌握到天竺等異域的語言、文字、經典及思想。當然,要孕育出一代高僧,絕對也得有著異於常人的特殊際遇。在康僧會所出生和成長的交趾郡,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諸子百家可再度齊放的重要搖籃;因為,儒家、道家及諸子百家的經典與思想,全都得著郡守士燮的大力支持與維護。
於交趾出生和成長的康僧會,雖是個外國人,卻也是個土生土長於中華大地、又可得著最全面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的幸運之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雖是到了晚清由洋務派的代表張之洞所提出;但遠在三國時期的康僧會,其實便已具備這項極超越的獨特條件。康僧會的異國底子,以及深厚的中華文化學養,都使他在當時的佛教傳播上,自然而然地接棒了另一異國高僧安世高所致力發展的佛教中國化工作。
佛教唯有中國化,才能在中華大地上被接納和廣傳。之前從西域前來的外國僧侶,之所以無法順利地傳揚佛法,最主要的關鍵就在他們少了安世高和康僧會所具有的中國文化學養;因此,佛教中國化的工作,便只有於安世高和康僧會才能展現成效。其中,康僧會又比安世高更見成效;因為,安世高所傳的是「小乘」佛法,康僧會則是將「大乘」與「小乘」相互融合。如此一來,與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和內涵才能更為相互融通,這才是令佛法足以跨出傳播困境的一重要步履。
正因如此,康僧會在譯經工作上,便特別選定了與儒、道思想更易融通的《六度集經》。為了將康僧會的譯經與中國文化相互融通之原因更為充分地展現,筆者在第二部分之壹「展現救世精神的《六度集經》」裡,即參酌了學界對《六度集經》所進行的修訂,使其故事內容得以和中國的儒、道兩家經典有更充分的連結。此外,筆者還在每則本生故事下,又特別徵引了與之相應的儒家及道家思想,目的也是為了要讓讀者能更清楚明白,康僧會在譯經工作上何以能形成「格義佛教」的效用。這是佛教得以在中華大地上最終能朝「佛教中國化」發展,還能讓佛法的傳播大大開展的極重要關鍵。
《高僧傳》對康僧會大師生平的記載雖是極其有限,但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石窟的《康僧會建業布教圖》,卻展現了康僧會大師一生的傳法歷程。筆者於第二部分之貳特闢一章節介紹《康僧會建業布教圖》,是想表達:康僧會之布教足以被畫入莫高窟,豈不說明了康僧會於東吳宣教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性!這也是世界佛教史上應當被頌揚的重要史實。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康僧會大師:誠感舍利顯佛力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康僧會大師:誠感舍利顯佛力
康僧會祖籍在中亞,成長、修學於漢化越南,博通儒道思想,並精研佛教典籍,為三國時代首位至東吳弘法之高僧。以至誠感應舍利降世,感化大帝孫權;融合傳統巧說佛法,令暴虐孫皓信服。融合佛道儒思想,實乃佛教漢化之大功臣!
康僧會大師精通梵文、大小乘佛法與儒、道思想,對越南佛教影響深遠;發願弘法東吳,揉合佛、道、儒家思想善巧說法,令佛法得以大盛於江南。康僧會之布教歷程被畫入莫高窟,說明了康僧會於東吳宣教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性,也是世界佛教史上應當被頌揚的重要史實。
【學界推薦】
周博士的《康僧會大師》,將我們對康僧會從陌生一步步帶到了熟悉,瞭解康僧會何以能成為高僧的關鍵。康僧會這位在交趾出生、成長、受教和出家的康居國人,對中國文化與佛法所進行的融合與交流,實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歷史樞紐。
──陳志平(湖北省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院長)
作者簡介:
周美華
國立中山大學(臺灣)中文系博士,湖北省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秦漢史、秦漢簡牘、秦漢考古,著有《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主要教授課程:中國原典導讀、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課程。
推薦序
【推薦序】
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一頁
◎陳志平(湖北省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院長)
周博士所撰寫的《康僧會大師》,是一部專以學術史的角度,將三國時期從交趾至東吳建業傳揚佛法的高僧康僧會,其一生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歷史定位,從歷史、地理、考古、康僧會所編譯的佛經,以及康僧會在儒、釋、道三教的貫通上,使「佛教中國化」得以被確立,以致形成唐代詩人杜牧所形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盛況的歷史原因及其脈絡,予以完整而系統的說明。
此外,藉由周博士以大量的歷史、地理及考古所進行的分析,使三國時期江南至交...
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一頁
◎陳志平(湖北省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院長)
周博士所撰寫的《康僧會大師》,是一部專以學術史的角度,將三國時期從交趾至東吳建業傳揚佛法的高僧康僧會,其一生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歷史定位,從歷史、地理、考古、康僧會所編譯的佛經,以及康僧會在儒、釋、道三教的貫通上,使「佛教中國化」得以被確立,以致形成唐代詩人杜牧所形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盛況的歷史原因及其脈絡,予以完整而系統的說明。
此外,藉由周博士以大量的歷史、地理及考古所進行的分析,使三國時期江南至交...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高僧傳」系列編輯序
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推薦序
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一頁 陳志平
編撰者序
「佛教中國化」的大功臣!
【示現】
第一章 出生與成長
皓(孫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
成長的故鄉--交州
家世背景
於交趾深植儒家文化的士燮
於交州積澱深厚國學素養
第二章 南越國的形成與發展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
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推薦序
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一頁 陳志平
編撰者序
「佛教中國化」的大功臣!
【示現】
第一章 出生與成長
皓(孫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
成長的故鄉--交州
家世背景
於交趾深植儒家文化的士燮
於交州積澱深厚國學素養
第二章 南越國的形成與發展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