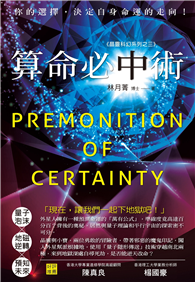人類的生命總感覺就是個完美的邊境國。一種永恆的跨越,朝著漫無目的的明日而去。
無名敘事者從曾在共產鐵幕籠罩下的東歐來到自由富裕的西歐,經歷種種衝擊與事變,陷入了回憶、想像與現實的模糊交界,開始寫信給一個不知是否存在的收信人,無休無止地傾訴、告解。敘事者告解說自己殺了戀人,一名享有高社經地位的法國教授,隨後揚長而去,逃脫法外,不知所終……至少留下的信中是這麼說的。
邊境國(border states)指的是位於西歐與俄羅斯之間,包含愛沙尼亞的一系列國家。這些國家曾是蘇維埃的一部分,也成為歐洲防堵蘇聯共產政權擴張、深入到他們內部,乃至跨越他們的「邊境」。而人所劃定的邊境是無形的,是故邊境國也似乎並不真的存在,為他人無視。蘇聯解體後,夾處在東西之間的邊境國,開始尋找自己的認同,面對自己在夢想的新世界中的不存在狀態。
托努‧歐內伯魯作為愛沙尼亞脫離鐵幕後第一代也是最受矚目的作家,本書是作者對愛沙尼亞獨立、開放邊境、加入歐盟後,愛沙尼亞人面對的身分認同與溝通問題的深刻反省。對照同樣夾處強權邊緣的台灣,本書具有特殊的──從他人眼光重審自身的意義。
而三十年過去,歷史輪迴重演,強權再次威逼,不管在歐洲或亞洲,邊境國依舊在存在與認同中掙扎。
我們相信過去徹底過去了,被我們拋在身後。但沒有,它回來了。
東歐,先前似乎已融入這個巨大的現代世界,再度成了地圖上的一道紅線。
再次,當下令人害怕,未來一片朦朧。我們又回到了邊境國裡。
商品特色
波羅的海議院(Baltic Assembly)年度文學首獎(1993年)
愛沙尼亞獨立以來外譯成最多國語言的文學代表作
問世三十週年經典紀念版,特別收錄作者專為中文新版撰寫之序言
作者簡介:
托努‧歐內伯魯 Tõnu Õnnepalu
1962年生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托努‧歐內伯魯在蘇聯體制下經歷過整個青少年乃至青年時期,1985年結束在塔圖大學(Tartu Ülikool)生物學方面的學習後,便投身寫作。除了創作與翻譯外,還當過自由記者、文學雜誌《Vikerkaar》的編輯、以及巴黎愛沙尼亞文化中心負責人。2006年,愛沙尼亞文學中心(Eesti Kirjanduse Teabekeskus)將歐內伯魯選為愛沙尼亞共和國獨立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他的作品圍繞著孤獨、性、社會生活、宗教自由、權力與背叛等人性主題,並在文字風格上展現出獨樹一格的國際性-──試圖讓自己的文字通過翻譯後仍易於理解,並且不執著於傳統所謂的「愛沙尼亞文學傳統」而自限於只有愛國人能瞭了解的主題;加上他週周遊列國的生活方式,讓他經常被稱為是「全歐作家」。
著有《邊境國》(Piiririik, 1993)、《價格》(Hind, 1995)、《公主》(Printsess, 1997)、《練習》(Harjutused, 2002)、《廣播》(Raadio, 2002)、《法蘭德斯日記》(Flandria päevik, 2008)、《樂園》(Paradiis, 2009)、《春天和夏天和》(Kevad ja suvi ja, 2009)。
譯者簡介:
梁家瑜,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英法文譯者,音樂依賴症患者。
章節試閱
與托努談文學、邊境︑國
首先,我想為您同意接受這次訪談向您致謝。
家瑜:
想問的問題很多。我想我們可以從台灣讀者或許會覺得最不能忽略的問題開始:書名。
我查了一下,「邊境國」(border states)這個字眼指的是一系列國家──包含愛沙尼亞──位於西歐與俄羅斯之間。這似乎是西歐國家的政策:讓「邊境國」成為防堵蘇聯共產政權擴張、深入到他們內部,乃至跨越他們的「邊境」。
我很好奇:如果我對這個字眼不是太誤解的話,那在蘇聯解體之前,這個字眼是否在愛沙尼亞社會為人所知?如果不的話,那我們的書名本身對第一批讀者──我是指愛沙尼亞讀者──而言,必然是一個新的概念,是不是?
另外,標題「邊境國」似乎意指「邊境國」並不真的存在,因為正如同書中的敘事者所說的,「邊境」是看不到的。然而,愛沙尼亞人民似乎有很堅定的國家認同,並期望他們的國家被看見。因此,藉由對愛沙尼亞讀者提出「邊境國」這個字眼,你是否有意喚起一些回憶,像是過去的處境、「胎死腹中的歷史」,亦或你想再現當前的處境(九零年代,因為你的小說是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意即儘管已經獲得獨立,但作為一個愛沙尼亞人,仍然不全然是可見的?
托努:
書名是一開始就選定的。我就是喜歡這個字眼。對我而言,它從過去到現在都至少有雙重涵義。沒錯,這是個地緣政治詞彙,但在愛沙尼亞當時的政治論述中卻不太常被使用。此外,比較「正確」的說法是強調「我們」(愛沙尼亞人)過去以來一直都在歐洲裡面,而非歐洲的邊緣、極端(或甚至是外頭)!我甚至可以宣稱,因為這本小說,我或多或少將這個字眼重新引入了愛沙尼亞的日常語彙。同時,如果現在有誰使用這個字眼,通常都可能隱含這本小說和其中的對偶(東/西;貧/富等等)的指涉。
但是對我而言,這個字眼向來都還有一個心理上的意涵:猶疑不決、不願讓自己認同於這樣或那樣東西,不願意選邊站。書中的敘事者甚至還做到了隱藏他或她的性別!但當然,這種居間狀態(In-Between)並不存在,至少對大部分人來說是如此。
另外在邊境國(Piiririik)這個字眼裡,還有一層歷史/時間(historico-temporal)的涵義:在九零年代初期,剛獲得自由的東歐國家正處於轉型期,處於邊境狀態,就歷史而言。事實上,當時整個歐洲都是如此,但在西歐卻不這麼明顯。在西歐有種(至少是無意識的)盼望:讓在東邊的「他們」改變就好,但讓在這兒的一切一如往常!這種不願意改變,或者不願意去正視對改變無法避免的需要,這幾乎是幼稚的。當然,你無法改變一邊(東邊),又讓另一邊(西邊)維持不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某種曾備受期待的全新穩定狀態,不過是進入某種未知狀態的過渡期。冷戰之後,我們進入的不是和平與穩定,而是一個全新而且甚至或許是更為劇烈的不穩定階段,進入(多重)危機的年代。
但是現在,在於巴黎寫完《邊境國》後十八年,像愛沙尼亞這樣的國家不再有太多的選擇。我們現在和法國、德國以及其他國家已經在同一邊了;我們家裡有一樣的冰箱、我們有一樣的超級市場、相同的無力感和相同的恐懼。現在,回過頭來看,九零年代的「轉型」時期(事實上,像我剛說的,整個世界現在看來不過是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轉型時期)現在看來是個單純而充滿希望的時期。那時候的希望,確實多少得到了滿足(對東歐而言):我們現在的確是富裕多了,在購買力方面(pouvoir d’achat,我不記得英語的詞是什麼了),但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富裕的另一面,即空虛,其虛幻的一面!我目前正在進行蕭沆(Cioran)的《誕生之不便》(De l'inconénient d'être né)的愛沙尼亞文翻譯。他說人們(人類)只知道一種讓事情變得更好的方法:就是讓事情變得更糟。回顧過去,再看看現在的世界,很不幸他似乎是對的……
但最終,邊境國這個字(piiririik)裡面,有件事令我著迷不已(儘管我以前未曾想過),亦即它的書寫形式:它是對稱的,PIIRIRIIK中間那個I就像一面鏡子,但卻似乎不太清楚:裡面反映的影像並不全然真切(一個字母看似另一個字母)。同時,大量的i就像地上風景中的一列邊境牌,或是柵欄……順帶一提,在蘇聯時期,愛沙尼亞是貨真價實的邊境地,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領地是禁區,所謂的「邊境區」(border zone)。大部分的海岸以及所有的離島都包含在內,所有人只要不是永久居住在其中,都得有警察給的特殊許可才行(而且你還得說明為什麼要進入該區:找親戚、工作等等)。因此,這個廣褒的國家邊境並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區域,寬達數十公里……我曾在西屋馬島(Hiiumaa)上住過一段時間(並且目前也住在這裡),就在邊境區裡面,並且是這個區域裡最森嚴的禁區……這也有好處: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的遊客,島上也沒有房地產開發。邊境區作為自然保育似乎是可行的……現在唯一真正的邊境是在愛沙尼亞與俄羅斯之間,即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的邊境。但這邊境大部分是在水裡(湖泊與河流),另一部分則大部分屬於森林,因此你可以在愛沙尼亞生活而從沒見過這個邊境。但邊境仍舊沒有太大的變動:從西邊海岸到愛沙尼亞的東邊,兩三百公里的距離……
家瑜:
很有趣的是,您談到了從上世紀九零年代到新世紀的轉型,特別是對東歐國家,這在某方面被您描述為富裕的虛幻面,即空虛,對此您似乎在小說中透過敘事者的話加以批判,在他談到(法國的)廚房、(法國的)櫥窗等等。而我猜想這是為什麼敘事者在小說中某處宣稱世界文學只存在於東歐某些意願良善而單純的教授腦袋裡。
您的小說中一直令我著迷的是認同的可能性。作為一個讀者,和所有讀者一樣,我們很容易將自己放到安傑洛的位置上。而許多人也說本書就某方面來看是您的半自傳小說。而我想,對許多西歐國家之外的讀者而言,也很容易能將自己置身於敘事者的位置。
同時,如您前面所說的,您正在翻譯蕭沆的作品。
因此,我的問題是:既然現在愛沙尼亞不像過去一樣有那麼多的選擇,已經與法國、德國在同一邊,你是否認為「世界文學」從任何角度而言比過去更為可能存在?因為在一個層面上,你的寫作似乎讓讀者很容易認同敘事者(儘管這是一個「不願認同」的人),而在另一個層面上,持續向西歐靠近,這或許讓愛沙尼亞的讀者處於新的位置,更能認同西歐國家至今持續面對的問題?
托努:
既然我們現在屬於西方,是西方的一部份,西方已失去了魔力般的吸引力。現在西方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通貨膨脹、經濟危機、失業率、過度消費、追逐錢潮,等等。當「自由世界」在邊境的另一邊時,對自由的夢想是強而有力的。但最後我們發現,自由是很微妙難搞的東西……你永遠無法擁有。當一個人以為他捕捉到自由時,他捕捉到的永遠是某種別的東西,某種比自由小得多的東西,而自由本身永遠在別處,像是天邊一朵美麗的雲,沒有形狀,無法觸及……就算你升到雲中,不管是坐飛機還是爬山,在一片水氣之外仍沒有任何東西,突然間你迷失了。越過它,什麼都沒有,除了我們稱為天空的一片空洞。
自由在歐洲是十九世紀強大理念中的一個,而在歐洲我們一直活在十九世紀,似乎無法從中逃脫。儘管那些大理念一個接著一個失去其真實的力量,但我們一籌莫展,我們仍然必須相信,因為我們沒有別的東西可相信。世界文學也是個十九世紀的理念(而那時候這指的當然是歐洲文學)。這確實表示有某種「優秀文學」的理念。而真的,在某些地方,現在似乎還存在著這種理念。就像十九世紀所有的大理念一樣,這個理念還是很大,但很詭異地,卻很無力,像是個鬼魂,像某種死後生存下來的東西(像是尼采之後的上帝理念,等等)。儘管我們無法辨認它的生死,而且如果我們(歐洲人)是在行將終結之邊境的這邊或那邊……我們活在一個終結的年代,某種無法避免的墮落,這也是個(終結中的)十九世紀的理念。但對我們而言它仍未真的終結。
認同的問題也與自由的問題、權力的問題緊密相連。如果我們內在認同自身,這就是種解放的行動,一種自由的行動,可是一旦認同變成一種外在的的標籤,它就變成一種綑綁,一座監獄。閱讀一本小說是一趟充滿魔力的自由之旅,我們全然自由地想像自己成為另一個人。可是一旦有人將我們認同為小說中的主角,這就變成了一種標籤的行動,權力的行動。只有對自己,我們可以自由地說我們是什麼。因為每次我們將它形諸言詞,它就會出現些許的差異。一旦我們將它說出口,我們就為自己畫出界線,將自己放進一個「身分認同」的牢籠。一個真實的人類身分認同永遠不能被文字所表達。它只能由生活,由整個生命來表達,而這在結束之前是不會完全清楚的……
與托努談文學、邊境︑國
首先,我想為您同意接受這次訪談向您致謝。
家瑜:
想問的問題很多。我想我們可以從台灣讀者或許會覺得最不能忽略的問題開始:書名。
我查了一下,「邊境國」(border states)這個字眼指的是一系列國家──包含愛沙尼亞──位於西歐與俄羅斯之間。這似乎是西歐國家的政策:讓「邊境國」成為防堵蘇聯共產政權擴張、深入到他們內部,乃至跨越他們的「邊境」。
我很好奇:如果我對這個字眼不是太誤解的話,那在蘇聯解體之前,這個字眼是否在愛沙尼亞社會為人所知?如果不的話,那我們的書名本身對第一批讀者...
推薦序
新版序
永恆的邊境(國)狀態
托努‧歐內伯魯
梁家瑜/譯
在一九八零年代早期,當我在愛沙尼亞小小的大學城塔圖(Tartu)唸生物學的時候,有個朋友問我為什麼只寫詩,不寫小說。是的,我當時已在某些地方發表了幾首詩,而且確實,我那時已經做了決定:我的未來在寫作,而不在科學研究。做個動植物學家一直是我兒時的夢想,但此時已然不同。我自己的天性似乎提出了比植物、動物和生態系統中的未解之謎更迫切的問題。此外,文字的世界向來吸引著我。單純的文字,以某種方式組合在一起,成為一首詩或是一篇散文,對我產生的影響無可比擬。但我對朋友的問題沒有答案。我知道他的意思。小說比一首簡單的詩更龐大,更像是真正的文學。我們全都、或者幾乎都會寫某種詩。詩沒那麼複雜。但我們當中沒有人寫過可稱作小說的作品。我自己也沒有。事實上,我甚至連寫小說是什麼意思都沒概念。我讀過很多小說,有幾本很欣賞,但閱讀並不會直接教你怎麼寫,怎麼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屬於你的世界。
我們坐在我的學生公寓裡──還是該怎麼稱呼它?那是間殘破的房間,位在一棟離河不遠的腐朽百歲老木屋裡。那時,冬天依舊嚴寒,壁爐中的柴火只能緩解片刻。但那些是充滿喜悅的片刻。當時我認為我的房間幾近完美:它是屬於我的。那裡我已經有自己的打字機,南斯拉夫製,很難得手(打字機,就算沒被禁止,在當時也還被視為有害公共秩序),我的錄放音機,我的書,還有一整盒黑膠唱片,大多是古典樂,但也有愛迪‧琵雅芙(Édith Piaf)。當我的朋友提出那個不知打哪來的問題時,正唱著歌的就是琵雅芙。我們喝著匈牙利產的葡萄酒,或許還點著一盞蠟燭,又或許當時寒冬已過,春天已到,而窗戶正開著。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或許在葡萄酒的幫助下,突然靈機一動,我說:「小說,我要在巴黎寫。」我的朋友笑了(我想),彷彿我說的是笑話,而不是認真的回答。沒有人從蘇維埃愛沙尼亞去巴黎的──我的意思是,沒有任何我們認識並認為是正常、體面的人這麼做過。身為作家,你得對黨和蘇維埃意識形態折腰,並做出過於沈重的讓步才有可能──當然,對我們而言,這不可接受。我們沒有人出過國。我的巴黎,是個近乎只存在於書本中的地方,而那些書多半是許久之前寫成的。然而,就算我的回答是以有點諷刺的方式迴避問題,但在內心深處,我卻是認真的。在心底,我確信(就算這個想法如此荒謬)我終將前往巴黎,置身其中,更自由,更自在,比在自己出生的國家更敢於做自己。嗯,我同意,那是個相當天真、相當浪漫,也相當老套的夢想。而我對朋友的承諾也不是認真的。我早忘了。
同時,一切都變了。突然間我們被允許去巴黎了,想去幾次就去──我們貧窮的東歐褲袋裡有或沒有錢都可以去。順帶一提,我們那時才剛得知一件事:我們是個特別的「種族」,不同於真正的歐洲人。
我自己也經歷了不少變化,發表了幾本輕薄的詩集,翻譯了幾本法文小說(我在學校從沒學過這個語言),同時生活在一個再次獨立(且極度貧窮)的國家,而且已經去過了巴黎,甚至還去了兩次。但我卻還沒寫出一本小說。確切地說:我寫過。我在當時生活的小島上寫過,但完成之時,我明白那部作品什麼都不是。我把它扔進壁爐裡燒了。在九零年代早期,在那座小島上,那部作品還只是草稿(儘管是打字機打的),只是一疊紙──一本小說。我不確定會不會再試一次。周遭充滿了太多新的機會。過去的夢想,在失能的社會中作的夢已然不再重要。有些人去搞錢了。有些人去搞政治。有些人出國之後再也沒回來。文學似乎不再是這一切的中心。但對我而言,文學依然是中心。而就算我現在已經知道真實的巴黎不是夢想中的那個地方,讀著舊的(甚或是新的)小說,它還是強烈地吸引著我。那裡一定有些什麼!然後,出乎意料地,我拿到一筆補助,來自法國政府(愛沙尼亞政府那時還太窮,沒法給作家任何補助),是一個翻譯計畫補助。
因此,在一九九三年早春,我又到了巴黎,口袋了有了點錢,還有屬於自己的房間!而腦袋裡卻沒有要寫本小說的想法。比起寫作,我更想體驗這種新的自由,這個新的生活,以及這個我渴望發掘、建構、創造的新自我。但我那時不知道,對我而言,生活與寫作如此緊密相連。
而在那兒,在巴黎,我遇見了某人,一個完美的陌生人,一個對我的出身、我的歷史、我的過去一無所知的人。我開始寫信給他,用法文(他不是法國人),但在幾封信之後,我明白到信開始變得冗長,開始變成某種不同的東西。我不再寫信給他。相反地,我找到了一個被創造出來的聲音(但依然是我的聲音),它開始訴說、告解、寫作──對著一個虛構的收件人。不知不覺我開始寫一個故事,一本小說。就這樣,這事依舊在巴黎發生了。有時候,透過愚蠢或是搞笑的話語,我們說出了真相。
如今,那些時光似乎如此遙遠,已然彷如「歷史」!在小說裡,敘事者有台電話,掛在他房間的牆上,只有他在家的時候才能夠聯繫到他。離開家在當時意味著離開一切連結。那是另一種自由,如今幾不可得:出門並消失在大城市的人類叢林裡,口袋裡沒有電話。沒有人知道你在哪。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在那些年,九零年代早期,那短短一段時期間,歷史似乎失去了其恐怖的力量,而自由似乎是場沒有邊境、永無止盡的冒險,可不是嗎?我們相信過去徹底過去了,被我們拋在身後。但沒有,它回來了。事實上,《邊境國》的敘事者並不確定他召喚的這個「不可想像」的過去真的離開了。他最深的恐懼是,這個過去就在某個路口轉角等著他,帶著它全部的殘忍與荒謬。不知為何,現在這發生了。東歐,先前似乎已融入這個巨大的現代世界,再度成了地圖上的一道紅線。紅意味著:血。紅意味著:可能的危險。紅(在此)意味著:我們不知道。再次,當下令人害怕,未來一片朦朧。我們又回到了邊境國裡。在某種意義上。當然,這並不是「回到」。當我在一九八三年承諾要在巴黎寫我的第一本小說時,我或許無意識嗅到了將來臨的巨大改變──那些巨大改變並不只是更自由的國度、更自由的人、與更快樂的世界。它們也帶領我們進入了更混亂的世界。在《邊境國》裡我親歷一個轉折點,既是個人也是歷史的轉折點:我身處其中。而我們是否正將來到另一個轉折點?或許比我更年輕得多的作家能嗅到,並表達出來。我只能說,我的感受出乎意料地沒有多少改變:人類的生命總感覺就是個完美的邊境國。一種永恆的跨越,朝著漫無目的的明日而去,口袋裡甚至沒有一台iPhone。
新版序
永恆的邊境(國)狀態
托努‧歐內伯魯
梁家瑜/譯
在一九八零年代早期,當我在愛沙尼亞小小的大學城塔圖(Tartu)唸生物學的時候,有個朋友問我為什麼只寫詩,不寫小說。是的,我當時已在某些地方發表了幾首詩,而且確實,我那時已經做了決定:我的未來在寫作,而不在科學研究。做個動植物學家一直是我兒時的夢想,但此時已然不同。我自己的天性似乎提出了比植物、動物和生態系統中的未解之謎更迫切的問題。此外,文字的世界向來吸引著我。單純的文字,以某種方式組合在一起,成為一首詩或是一篇散文,對我產生的影響無可比...
目錄
序──永恆的邊境(國)狀態
邊境國
與托努談文學、邊境︑國
譯後記
譯者新版後記──重返邊境/國
序──永恆的邊境(國)狀態
邊境國
與托努談文學、邊境︑國
譯後記
譯者新版後記──重返邊境/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