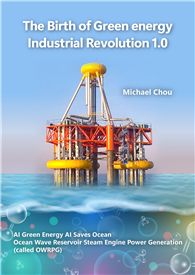我們如今所享受的大半的美好生活,都是英國和英國人所賜!感謝那些改變英國乃至人類歷史的英國人:約翰王、威廉‧華萊士、莎士比亞、牛頓、庫克船長、埃德蒙.伯克、瓦特、亞當.史密斯、納爾遜、南丁格爾、狄更斯、維多利亞女王、邱吉爾、歐威爾、西格蒙德‧沃伯格……
作者走訪不列顛群島,在不同的地點得到不同的啟發,並從歷史上的顯赫人物之生平獲得靈感,借古諷今。當中有國王及女王、有思想家伯克及政治家邱吉爾,有銀行家沃伯格,有大文豪莎士比亞及狄更斯,有科學家牛頓,有護理界先驅南丁格爾,每一位都是形塑不列顛文化的關鍵人物。讀者彷彿進入歷史長廊,感受群島上人民的艱辛及喜悅。—— 梁文韜(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
人口才我們三倍且長居全球軟實力排名第二的英國,以證據告訴我們一個島國能如何成就璀璨的人類文明。余杰這本書讓我們知道,如果夜晚的星空是現代世界的化身,而肉眼可見的星群是締造這世界的偉人,那英國大概就是不分南北半球都耀眼可見的獵戶座。——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
作者簡介:
余杰 Yu Jie
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世紀之交死水般寂靜的文壇掀起一陣旋風,短短數月間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此後十餘年間,與劉曉波一起推動中國的自由與人權,屢受中共當局之禁書、圍剿、軟禁、拘押乃至酷刑折磨。
2012年1月,攜妻兒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定居華盛頓郊區,主持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潛心讀書思考、著書立說。2018年12月,入籍美國,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拒絕鄉愁,享受孤獨。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只做這一件自己擅長做的事情。長期為北美和台灣多家華語媒體撰寫專欄文章,著作多達八十餘種,一千五百萬字,涵蓋當代中國政治、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等諸多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獎」、「廖述宗教授紀念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精神故鄉,心繫台灣的美食、風景、書店和朋友。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相信讀書這一古典的愛好能帶來生命中最大的快樂,願意以書為媒,結識更多自由而勇敢的心靈。
章節試閱
第十四章 喬治.歐威爾:你知道有一隻靴子踩在你的臉上嗎?
1949 年4 月22 日,《一九八四》的樣書郵寄到喬治.歐威爾養病的格羅斯特郡克蘭漢療養院。歐威爾告訴出版商沃伯格:「現在就能拿到樣書似乎非常早。」他很喜歡書衣,也喜歡整體的包裝,並列出六、七位名人的名單,包括T. S. 艾略特、亞瑟.庫斯勒、安德烈.馬爾羅等人,請出版社寄樣書給他們。
6 月8 日,《一九八四》正式上市,一石激起千層浪,將共產極權主義的真相曝光於天下。然而,此時的歐威爾已經「病入膏肓,完全無法工作」,只能臥病在床,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時間,下一部作品再也無法完稿。
他的墓碑上為什麼沒有他的筆名?
1950 年1 月21 日,歐威爾因肺結核不治,在格羅斯特郡一家設備簡陋的療養院去世。他的朋友們原本計畫將他送到瑞士阿爾卑斯山的一處療養院,那裡清新的空氣對他的肺病更有益,但他已衰弱得無法長途旅行。歐威爾的朋友、因揭露烏克蘭大饑荒而受到西方左派圍剿的記者蒙格瑞奇最後一次去探望他時,覺得歐威爾看起來就像曾看過的一張照片—哲學家尼采臨死前躺在床上的樣子。
在歐威爾去世那一晚,醫院房間裡一角還放著或許是跟他一起來的釣竿,主人卻再也無法拿起釣竿釣魚了。歐威爾說過,作為一名英國紳士,必須精通三項技能:釣魚、騎馬和園藝。或許,這就是英國紳士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儒家士大夫之間的重大差異。由於健康原因,歐威爾後來不能騎馬,卻將園藝和垂釣的愛好保持一生,他還熱衷於觀察鳥類,知道各種鳥的名稱。他是一個典型英國人,一個鄉下人。他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大城市,但只有到了鄉村,他才有如魚得水的舒適感覺,這是保守派的特徵。
歐威爾的個性非常英國化,不單單體現在日常生活方面,精神生活也是如此:他信奉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尊重傳統、質樸簡單。他的寫作風格平實,生活儉樸,跟他筆下的普通民眾渾然一體,更接近狄更斯和21 世紀的「後現實主義」。有研究者將歐威爾與清教徒作家約翰.班揚(John Bunyan)作比較,發現清教徒傳統、叛逆傳統能夠讓人更好地了解歐威爾,「清教徒試圖在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中,建構一套道德理想」,這似乎就是歐威爾的真實寫照。歐威爾與馬丁.路德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有一種覺得一定要反抗暴政和教會—尤其是羅馬教廷和莫斯科教廷—的迫切感。歐威爾本能地憎惡極權主義者,不是因為他和那些人有什麼不同,而是因為他暗暗害怕自己最終將變成那樣的人。這種反抗精神源自知識分子的正直,也是路德教派和個人良知綜合影響的結果。歐威爾在《文學的捍衛》一文中寫道:「在整個新教時期,反抗和知識分子的正直緊密相聯。」他特別引用一首新教的聖歌來彰顯此原則:「敢於做一個但以理(Daniel),敢於獨自抗爭,敢於堅定目標,敢於讓世人知曉。」
我在英國傳記作家泰勒的《歐威爾的一生》中查到歐威爾的墓地在牛津郡薩頓考特尼村(Sutton Courtenay)諸聖教堂公墓。歐威爾在遺囑中交代,他的葬禮儀式要遵從英格蘭教會(英國聖公會)的規定,並希望葬入教會墓園。然而,他生前並未公開宣布自己是信徒,也不是某個教區的居民和會友,這兩個普通的遺願似乎難以實現。他的妻子和朋友找來奧巴尼街基督教會的教區牧師來主持禮儀。那家教堂沒有暖氣,蒙格瑞奇描述那場喪禮「相當哀淒,且寒氣逼人」。歐
威爾的小說家朋友鮑威爾選擇以《傳道書》做為喪禮講章的文本—那一章很適合用來紀念一位作家的逝世,裡面有這麼一句經文:「著書多,沒有窮盡。」出版商戴維.阿斯特出面解決了第二個問題—他在薩頓村有一處住宅,他也在當地的教堂公墓中購買了兩塊墓地,並說服教堂的鄧斯坦牧師相信,若是作為「當代寒冬中的良心」的歐威爾埋葬於此,能為會眾增光。薩頓考特尼是一個寧靜的小村莊,歐威爾生前與這裡毫無關聯,它卻慷慨地為作家提供了一處小小的安眠之地。
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歐威爾的墓地,墓碑上鐫刻的是其真名阿瑟,沒有提及他那著名的筆名喬治.歐威爾。這當然不是他本人及他的親友的疏忽,而是有意的安排。或許,歐威爾生前對英國的共產化充滿疑懼,他像伯克一樣害怕被左派鞭屍,刻意讓其墓地隱藏在偏僻的鄉間,墓碑上使用鮮為人知的本名。
在歐威爾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察覺到英國左翼分子對蘇聯卑躬屈膝,這讓他他義憤填膺,他原本的反蘇態度變得更加強烈,同時他也更加親美,「我尤其討厭那種伎倆,一邊投靠左翼,一邊尋求美國的糧食和保護」。他當著國內反美派的面,公然選擇美國,排斥蘇聯。直到1970 年代,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在西方出版,西方左派才對蘇聯的殘暴本質恍然大悟,他們此前到蘇聯訪問看到的是當局精心安排的華而不實的「波坦金村莊」。
歐威爾是20 世紀最偉大的英國作家—這一事實幾乎要等到他去世半個世紀、冷戰落下帷幕才被世人認可。左派發現無法否定他的地位,乾脆將他拉入左派陣營—比如,在美國總統川普改變西方長久以來對中共政權的綏靖主義政策並譴責左派媒體炮製假新聞之際,西方左派卻將川普塑造成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還用圖書館中《一九八四》借閱量猛增來證明民眾對川普的厭惡。這是對歐威爾思想遺產的最大褻瀆—《一九八四》中陰鬱的場景,跟美國政制沒有半毛錢關係,倒是一面鏡子,照出今日中共政權無孔不入的數位極權主義的真相…… (未完)
第十四章 喬治.歐威爾:你知道有一隻靴子踩在你的臉上嗎?
1949 年4 月22 日,《一九八四》的樣書郵寄到喬治.歐威爾養病的格羅斯特郡克蘭漢療養院。歐威爾告訴出版商沃伯格:「現在就能拿到樣書似乎非常早。」他很喜歡書衣,也喜歡整體的包裝,並列出六、七位名人的名單,包括T. S. 艾略特、亞瑟.庫斯勒、安德烈.馬爾羅等人,請出版社寄樣書給他們。
6 月8 日,《一九八四》正式上市,一石激起千層浪,將共產極權主義的真相曝光於天下。然而,此時的歐威爾已經「病入膏肓,完全無法工作」,只能臥病在床,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
推薦序
英國人,「英國秩序」與「英國治世」:《不列顛群星閃耀時》自序
斯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的名著《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首次出版於1927 年,書中選取了歷史長河中14 個「星光時刻」,為平凡人的激情奉上讚歌,向偉大人物抗爭命運時的堅強信念致敬,並給黯然隕落的失敗者以應有的尊嚴,因為在人類歷史的夜幕上,他們才是恆久閃耀的群星,正如作者所說:「我想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這樣稱呼那些時刻,是因為它們宛若星辰一般永遠散射著光輝,普照著暫時的黑夜。」
這些「星光時刻」包括:西班牙的拔爾波亞(Vasco Nunez de Balboa,1475 年—1519 年)以逃犯之身發現太平洋,是大航海時代探險精神的代表;法國大革命時的一名軍官魯日.德.李爾(Rougetde Lisle)在激情的推動下,一夜之間寫出《馬賽曲》;紐約商人菲爾德(Cyrus West Field)屢敗屢戰,終於在1858 年實現了在大西洋海底鋪設電報電纜的偉大夢想;拿破崙因為手下將領格魯希(Emmanuel de Grouchy)猶豫一分鐘,兵敗滑鐵盧;英國探險家史考特(Robert Falcon Scott)率隊前往南極點,卻發現挪威探險家羅阿爾.阿蒙森(Roald Amundsen)已捷足先登;列寧抵達芬蘭車站,整個世界將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褚威格將這些歷史場景用生花妙筆娓娓道來,
倒是符合中國「文史一家」的傳統:司馬遷寫《史記》,「鴻門宴」上諸多人物的言行宛如電影畫面,明明生在異代的作者似乎身臨其境。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是我中學時代學習寫作的好範本。但我後來發現,這本書讓人津津有味、愛不釋手,但作者的歷史觀卻曖昧混亂甚至自相矛盾:褚威格對拿破崙的失敗頗為同情,對拿破崙的功業相當推崇,卻忽略了拿破崙對被侵略的國族之暴政與屠戮,在種族屠殺的意義上,拿破崙是希特勒的老師;褚威格也將被德國人當作禍水運回俄國的列寧予以正面描述和評價,隻字不提列寧共產革命所帶來的生靈塗炭,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在本質上一體兩面,只譴責法西斯而不譴責共產黨,在邏輯上無法自洽,在道德上是偽善和懦弱。
少年時代的我,喜歡浪漫的法國文學和沉重的俄國文學;中年時代,才發現寧靜內斂的英國文學以及背後的英國文明的偉大。在《大光》(八旗文化出版)三部曲中,我論述了清教秩序或英美文明的正途,可惜只能有一章的篇幅來寫英國。2022 年夏,我赴英國旅行和田野調查,突然發現可以寫一本升級版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不列顛群星閃耀時》,寫英國人的故事,不僅回答「誰是英國人」的追問(類似於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問題—《誰是美國人》),更是在人物的生命中探尋「英國秩序」和「英國治世」的奧祕。
我選擇了15 個人物及其創造的歷史性時刻,除了第一個人物「無地王」約翰,其他14 個都是「正面人物」(約翰王雖然是「反面人物」,卻做了一件對英國憲政進程影響深遠的好事—簽署了《大憲章》,儘管他不情不願且很快反悔。上帝如此幽默,祂有時會揀選壞人來完成美好的事情。)我的選擇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褒貶和臧否,任何一個作家在敘述歷史與現實時,都不可能實現所謂的「客觀中立」,反之,主觀性或個性越強的敘述才越有價值。
在我選擇的人物中,最能代表英國人的作家、學者和科學家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牛頓(Isaac Newton)、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瓦特(James Watt)、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等人。我走訪了他們的墓地、故居、紀念碑和紀念館,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文辭、思想與觀念已然融入世世代代英國人的血液與心靈之中,甚至成為英國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英國秩序」的內在邏輯:英國從來就不是歐洲國家
我寫這些人物,寫他們的悲歡離合,寫他們的榮辱興衰,寫他們的勇氣與智慧,寫他們的冒險與抗爭,寫他們「英國人之所以為英國人」的「英國性」:揭竿而起的蘇格蘭民族英雄威廉.華勒斯(William Wallace),生做自由人,死亦為自由魂;詹姆士.庫克(Captain James Cook)在大洋上乘風破浪,為大英帝國開疆闢土,為人類科學的版圖拼上未知的一大塊;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Nelson)在大海上向死而生,「為了英格蘭,每個人都恪盡職守」的旗語讓全體官兵熱血沸騰;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臨危受命,在至暗時刻力挽狂瀾,從未喪失信心和希望—「每個人都是昆蟲,但我確信,我是一隻螢火蟲。」他們用汗水、淚水和血水,完美地闡釋了何為英國人、何為英國。
《大憲章》一問世,英國與歐陸的歷史軌跡即南轅北轍,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說過:「在我一生,我們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歐洲大陸,而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來自說英語的國家。」(In my lifetime all our problems have come from mainland Europe and all the solutions have come from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across the world.)毫無疑問,「英國秩序」與「歐陸秩序」大相徑庭,更遑論西方之外的其他路徑和模式了。英國歷史學家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Peter Simms)在《千年英歐史》一書中指出,英國國力的巨大彈性可歸因於三個因素:首先,英國有其固有的內在力量。自中世紀以來,英格蘭王國一直是個大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自17世紀以來,英國從未經歷過內戰、外國佔領或革命。如今,英國人的國族認同感比歐洲所有國家都強,且反對歐盟合併主權的潮流。其次,英國盎格魯- 不列顛的「軟實力」(Anglo-British “soft power”)在於它有能力讓別國的追求與自己一致。長期以來,英國扮演歐
洲乃至世界的治安官的角色,提供某種重要的「公共財」(public goods)—維持均勢、開放經濟和自由的國際體系,大英帝國被譽為「被邀請的帝國」,它曾經的殖民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至今仍是其親密夥伴。第三,英國的憲政模式的彈性與恢復力強,多虧了國會(Parliament)和「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英國的總體戰略具有一個廣泛的政治基礎:它為這個政治民族(politicalnation)所擁有。
本書中每個人物的故事都驗證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英國從來就不是歐洲國家。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堅決反對,至今仍擲地有聲;亞當.史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架構,與歐陸的國家主義和重農主義經濟學分道揚鑣;當歐陸的女性被牢牢束縛在家庭中時,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已穿上護士服裝奔赴戰場。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指出,英國秩序的核心是絕對產權、言論自由、議會制政府、個人自治,而歐盟正在向「大明王朝- 蒙古- 奧斯曼帝國」的道路狂奔—大一統、中央集權、高稅率,以及國家控制。所以,西姆斯的結論是正確的:一個統一的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聯邦國家是與英國主權不相容的。相反,一個符合英美憲政體制的歐元區能和英國結成邦聯,並且通過北約與加拿大和美國形成安全夥伴關係,這既將保留英國主權,又能為英國帶來利益。歐洲大陸在1945 年之前就失敗了,即使是現在,歐盟已然是失敗的,只是程度稍好而已。因此,英吉利海峽兩岸需要的不是一個歐洲
化的英國,而是一個「英國化的歐洲」。歐洲只有與英國分開才能變得更加英國化。
從「英國治世」到「美國治世」
本書中的人物以及他們偉大的創造,都只能誕生於英國。我在寫這些人物時,每每將孕育其成功的時代和文化背景與東亞的儒家文化圈做對比:湯顯祖成不了莎士比亞;鄭和成不了庫克船長;大清王朝出不了牛頓;當亞當.史密斯在寫《國富論》時,乾隆皇帝在焚書和炮製文字獄;當南丁格爾成為「提燈天使」時,中國女子還在纏足。
「英國治世」的巔峰是維多利亞時代。儘管維多利亞女王在名義上統治著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廣袤的「日不落帝國」,但這個帝國卻不是她按照一個周密的計畫來打造的。她對英國本國和整個大英帝國的重大貢獻,不是像清帝國的康熙大帝或俄國的葉卡特琳娜大帝(凱薩琳大帝)那樣以絕對君主制完成野心勃勃的領土擴張,以及對天下事進行事無巨細的治理;反之,她的垂拱而治、無為而治,成就了她的卓越與尊貴,讓她與英國憲制融為一體。英國歷史學家拉姆齊.繆爾(Ramsay Muir)在《帝國之道》一書中指出,這也是英國秩序的本質:它在一知半解的狀態下為制度奠定了基礎,該制度力圖在嶄新而未開發的土地上,在其最古老的文明民族裡,即刻實現自由,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它探索著將迥異的自由國家以一種和平與相互尊重的手足之情聯繫在一起。這種壯大是相當偶然的,而且沒有成熟的理論或政策來指導。英國的政策從來不是由理論支配的,而是由一種有秩序的自由傳統來打造的。這一時期,英國沒有誕生一流的帝國主義政治家(維多利亞女王不是這樣的政治家,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也很難說是這樣的政治家),帝國問題也沒有在議會的審議中佔主要篇幅。事實上,大英帝國和其制度的成長是自發的、零散的;它們唯一的嚮導(事實恰恰證明這是一個好嚮導)是自治的精神,這種精神在民眾中廣泛傳播。
二戰之後,「英國治世」被「美國治世」所取代,這一過程從20 世紀初就緩慢開始了。就個人而言,邱吉爾遠比小羅斯福聰明睿智,但英國的國力已不足以支撐前者充當後者的政治導師。戰前從德國移居英國的猶太裔銀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Siegmund George Warburg),在戰後20 多年間堪稱英國的「編外財政部長」,他點石成金、合縱連橫,讓倫敦重新恢復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即便不能力壓紐約一頭,至少也與之並肩。正如宗教改革時代法國、西班牙迫害新教徒,信奉新教的人才逃避到英國,沃伯格若留在德國必然是死路一條,他在英國的成功表明英國是一個真正海納百川的國度。其實,早在此前數十年,猶太裔的迪斯雷利就已順利出任英國首相,這種種族寬容和種族平等,在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大國都是無法想像的。
美國是作為英國的改良版而誕生的。當年,北美殖民地居民奮起反抗英國,不是反對「英國秩序」,而是堅守「英國秩序」—他們的不滿,是因為沒有受到大英帝國子民應有的待遇,「無代表,不納稅」的觀念,就是典型的英國觀念。伯克為美洲人的解放運動鏗鏘有力的辯護,被美國的國父們寫入《獨立宣言》。歷史就是如此弔詭,也如此理所當然。那場戰爭的傷痕很快就癒合了,美國的崛起後來成了英國的福音。即便是英國激進派記者斯特德也承認:「在美國人以
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理由對美國人所發揮的作用感到憤怒,畢竟,這本質上也是我們自己的形象。」美國繼承而非取代了英國,即便如今盎格魯- 撒克遜人的後裔在美國逐漸成為人口中的少數(這是杭亭頓為之哀歎的事實),美國仍然是英國「政治計畫」的後裔。「英語文化圈」概念的延續時間已經超過20 世紀上半葉的「盎格魯- 撒克遜」世界團結的概念。
本書中15 個人物的故事,呈現了英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的15 個「星光時刻」,更闡釋了何為英國人、「英國秩序」和「英國治世」。今天的我們所熱愛的自由、獨立、憲政、共和這些偉大的觀念,在很大意義上都是英國式的。劉曉波曾經說過:「中國實現真正的歷史變革的條件是做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這句話傷害了許多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的玻璃心,但中國對香港的再殖民和劣質殖民很快毀掉了英國在香港留下的文明、法治和自由,卻證實了劉曉波說出的是刺耳的真理。
我們如今所享受的大半的美好生活,都是英國和英國人所賜。若追本溯源,不必遊歷長江長城、黃山黃河,不必查考四書五經、唐詩宋詞;更應當縱覽泰晤士河畔、牛津劍橋以及蘇格蘭高地,更應當吟誦莎翁、伯克、狄更斯、邱吉爾和歐威爾,而這本《不列顛群星閃耀時》正是一本關於英國文明的入門書。
英國人,「英國秩序」與「英國治世」:《不列顛群星閃耀時》自序
斯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的名著《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首次出版於1927 年,書中選取了歷史長河中14 個「星光時刻」,為平凡人的激情奉上讚歌,向偉大人物抗爭命運時的堅強信念致敬,並給黯然隕落的失敗者以應有的尊嚴,因為在人類歷史的夜幕上,他們才是恆久閃耀的群星,正如作者所說:「我想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這樣稱呼那些時刻,是因為它們宛若星辰一般永遠散射著光輝,普照著暫時的黑夜。」
這些「星光時刻」包括:...
目錄
自 序 英國人,英國秩序與英國治世 9
第 一 章 約翰王:暴君匍匐在《大憲章》之下 17
第 二 章 威廉.華萊士:誰願生做自由人,死做自由魂?
第 三 章 莎士比亞:即便我身處果殼之中,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
第 四 章 艾薩克.牛頓:我僅僅是一個在海邊嬉戲的頑童
第 五 章 詹姆士.庫克:每個英國人都把自己看成船長
第 六 章 埃德蒙.伯克:保守主義政治宏大且美
第 七 章 詹姆士.瓦特: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濺出無數的火花
第 八 章 亞當.史密斯:國家和個人的財富都來自於自由貿易
第 九 章 霍雷肖.納爾遜:為了英格蘭,每個人都要恪盡職守
第 十 章 佛羅倫斯.南丁格爾:女人的愛心比男人的野心,可以征服更多的地方
第十一章 狄更斯:那顆詩人的心,永遠與貧苦不幸的人在一起
第十二章 維多利亞女王:治理不列顛尼亞和日不落帝國的「母親」
第十三章 溫斯頓.邱吉爾:人最可貴的精神就是無畏
第十四章 喬治.歐威爾:你知道有一隻靴子踩在你的臉上嗎?
第十五章 西格蒙德.沃伯格:讓倫敦重新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附 錄 看哪,這個星球上最奇妙的島嶼—英國遊記
自 序 英國人,英國秩序與英國治世 9
第 一 章 約翰王:暴君匍匐在《大憲章》之下 17
第 二 章 威廉.華萊士:誰願生做自由人,死做自由魂?
第 三 章 莎士比亞:即便我身處果殼之中,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
第 四 章 艾薩克.牛頓:我僅僅是一個在海邊嬉戲的頑童
第 五 章 詹姆士.庫克:每個英國人都把自己看成船長
第 六 章 埃德蒙.伯克:保守主義政治宏大且美
第 七 章 詹姆士.瓦特: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濺出無數的火花
第 八 章 亞當.史密斯:國家和個人的財富都來自於自由貿易
第 九 章 霍雷肖.納爾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