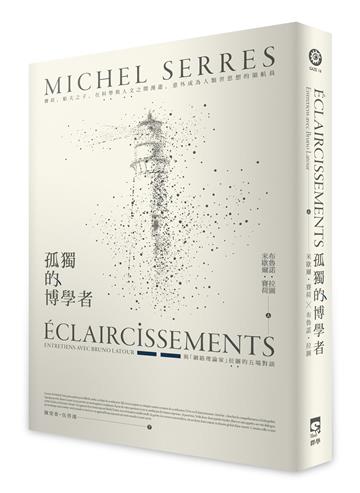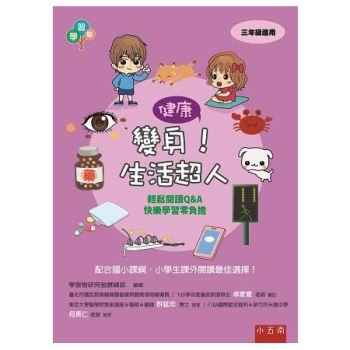預見人類世與手機世代
引進混沌理論、資訊理論與生態論述的跨領域先知賽荷
如何掀起人文思想界的革命?
最會「說故事」的法蘭西院士Michel Serres
與「科技與社會研究」宗師、台北雙年展策展人Bruno Latour
將以淺白的口吻,解析「物」與「人」的溝通網絡如何運作
並反思人類文明與科學的倫理困境
賽荷(Michel Serres),法國思想家。童年時期的二戰經驗,尤其是廣島、長崎的原爆事件,促使他反思科學的樂觀主義,並走向哲學。受過數學訓練的賽荷,是將資訊理論、混沌理論引進人文學科的先驅。不甘囿於專殊領域,尤其是人社/理工之間的僵固壁壘,賽荷的哲學遊走於學科之間,從流體力學、拓樸學、生命科學,談到倫理、宗教與政治。在寫作風格上,他則捨棄學究黑話,喜歡從故事的寓意中提煉出對於物-人關係的分析。
然而,跨領域的遊走與詩性的語言,在學科分工明確的戰後初期,並不為當時的同儕所接受,直到其前瞻性的思想,屢屢印證了近年的時代演變。
為此,知名學者拉圖(Bruno Latour)便展開五場訪談計畫,試圖以口語的形式,針對科學、文化、時間、關係網絡、暴力、美德、教育等大哉問,請賽荷一一釐清。
從希臘神話中掌管訊息的赫美使(Hermès)談起,賽荷對「人類關係」的討論,離不開通訊、噪音、寄生等看似屬於「自然科學」的概念。特別的是,他是從「物」(與人)的關係,界定人類性、社會關係與集體,因而不容於人文學科的主流意見,它們側重主體經驗,並強調自然與社會有著截然不同的邏輯。於是,賽荷就成了學院最後的博學者(savant),正如同他欣賞的柏格森、巴斯卡、萊布尼茲或希臘哲人,這些人在哲學之外,都還具有數學、理科或文學的涉獵。
而當今,有別於戰後,早已是個「斜槓」的時代,我們更需要「跨界」的思想家,以探索多變且複雜的現實難題。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它們往往超越狹隘的領域劃分,涉及了跨越多重學科的「整體性」問題。舉凡微生物、生態、數位資料權、人工智慧,都位於「人」與「科技」的介面,也必然觸及「科學-倫理」的關係。在媒介科技扭轉日常生活,氣候變遷亦反撲地球的當下,已經沒有科學可以宣稱自己免於社會的作用,也沒有任何人文議題,能夠無視技術的演進。
總算,這名孤獨許久的遨遊者,能成為我們「人類世」與「資訊世代」的知識嚮導。
本書特色
●兩位大師的多次對談集結成冊,在知識史上難能可見。書中,理論家拉圖以最犀利的角度,對賽荷刨根問底,並讓賽荷剖析他作為一名哲學家的治學之道;而對於引領人社思想潮流的法國學術界,賽荷亦揭露其親身體驗,令讀者窺見學術巨塔的真實面貌。
●在學科分工碎片化的戰後/現代,賽荷硬是反其道而行,遵循古希臘至文藝復興-近現代時期博學家,以跨學科的百科全書式知識,道出更有生產力、原創性與啟發性的洞見。同時,他不但預見了近20~30年國內外對於「科際整合」的呼籲,其跨領域的幅度更是巨大,不只是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還從非虛構的科學與哲學,跨進更洞悉人性的複雜面向之文學。
●本書的〈譯者導讀〉特別點出賽荷與拉圖在智識系譜上的傳承,而拉圖,作為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學門的奠基者,前期對於技術物、網絡、自然/文化、主體/客體的討論,有許多地方都能見到賽荷思想的蹤跡;到了學術生涯後期,拉圖更是呼應賽荷,將兩人對於昔日「社會學只關注人文現象」的反省,運用到生態人類學的研究,進而讓蓋婭理論(Gaia theory)發揚光大,遂引發歐美與台灣近十年來,人類世(anthropocene)論題的熱潮。
●兩人以關係論的角度,融合環境史與人類歷史的觀點,既描繪社會的運作,又刻劃出人與物質的交互作用。同時,點出「智慧」及「知識」原先就是人類面臨集體苦難時所發明的產物,因而讓「應然」與「實然」的討論,能夠搭起橋樑。在跨界與斜槓的當今時代,這尤其能讓人省思科技倫理的議題。
佳句摘錄
☆ 從科學走到哲學
▍我離開科學是為了研究哲學,因為嘛,數學直接通往哲學,真的;而我選擇哲學,是出自對戰爭與暴力的特殊感受,可以說是發自良心的抗議。
▍這就是我起意寫作的緣由,一方面站在科學家的對立面,替古典人文作辯護;另一方面,卻是為科學家展示、解說這些人文學科。我要告訴他們:「[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想得很深,甚至很理性,勝過今天大多數的科學家;而像左拉,一位小說家,早在熱力學出現以前,就發明了熱力學算子[opérateur]。
▍新觀念源於沙漠,出自隱修士、孤獨者,或那些搞避靜[retrait; retreat]的人,他們沒有陷於重複討論的喧囂與噪動。重複的討論往往製造過多噪音,讓人無法自在地思考。[…]科學也許需要不斷的公開討論,但哲學必將死於其中。
▍假如是要做科學研究,我們大概便得屬於一門學科,無論在內容、在制度上都有一定組織;於是才會有那麼多的教學啊、師生啊、實驗室老闆啊、期刊出版啊等等的組織遊戲。選擇哲學,就是假設要做完全不同的行為:獨立、思想自由、遠離壓力團體……所以,沒錯,就是孤獨。我再說一次,這不是為了與眾不同,而是獨立思考。組織嚴密的集體重視監督:在科學,這大概是件好事,它能造就嚴謹,當然還有順從;在哲學呢,這便算是警察查禁了。柏拉圖說得不對,我們給哲學家什麼都可,唯獨不能給他權力。
▍科學力量之攀升,必先招募大量兵馬,以至於它大權在握之時,周遭便形成真空。它周遭的人文、藝術、宗教、甚至法制等文化部門,自然首當其衝,瞬間沒落。
▍我希望做的是〔科學與哲學的〕兼容,而非模仿。
☆ 關於文學
▍我們有時發現,在文學作品裡已經出現了完美的直覺,預示了後來的科學論著。有時候,藝術家──包括音樂家、畫家、詩人──在科學真理誕生前便看見了它。
▍從某些方面來說,我覺得只要故事講得好,裡頭也能包含同樣多、甚至更多的哲學,不一定要用奢侈的技術性語言來表達。
▍做哲學的,多多少少要在乎「整體性」。哲學家啊,真的,應該要知道一切,理解過一切,體驗過一切,這包括:軟、硬科學,它們的科學史,還有非科學的那些東西;百科全書,包羅萬有。能撐起哲學的,並非科學裡頭的這個或那個部分;而是所有活躍的知識。[…]這包括體驗:他必須遊歷世界和社會,認識各地景色、各個社會階層,認識不同地區、文化。[…][…]所以,我為什麼要排除文學呢?
☆ 論哲學的任務
▍哲學專以創造為務,尤其是創造出讓人能夠創造的條件。
▍你不覺得哲學家在兩個極端之間拉扯?一邊在乎所有知識、經驗之最大量積累,而在另一邊,則想要絕學棄知,一切從零開始。[…]哲學不是一門知識,也不是在尋常科學裡的一門學科,正因它持續在全與無之間擺盪。哲學作品包含一切,這是它的必要條件;但接下來便跳到一旁去,以獲得嶄新,讓一切從頭開始。
☆ 科學的社會建構
▍科學裡有神話,神話裡亦有科學。
▍理性主義也應當適用於科學領域之外。[…]我們與前人想法不同,對我們來說,科學既非絕對善,也非絕對惡;既非全然理性,也非對存有的遺忘;既非魔鬼,也非上帝。科學終究是工具而已,不多也不少;但作為一整套工具,它卻具有如此高的重要性,在社會上如此有份量,以至於在目前,它成為西方世界唯一僅剩的歷史性任務。所以,沒錯,哲學問題開始浮現了。
▍科學的確是文化構成物,這跟其他東西沒兩樣。不用說你便很清楚,一般而言,工具(比如挑戰者號)同時是世界物(objet-monde),又是社會物(objet-société)。每一項技術都會轉變我們跟事物的關係(火箭往平流層飛去),同時也轉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火箭為發射它的國家做宣傳)。有些工具或理論傾向於某一方,有些則傾向另一方,但無論如何,所有工具都能一樣好地顯示出這兩個面向。
▍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在過世的前一天跟我說了一段話,我始終銘記於心。他說:「我向來取笑物理學家有良心問題,因為我是巴斯德研究院裡的生物學家;我創造、提出新療法,工作上總是心安理得,物理學家卻成功助長了軍火、暴力、戰爭;但現在,我終於明白,如果不是我們插手的話,第三世界便不會出現人口爆炸;我於是向自己提出很多問題,跟物理學家就原子彈問題的反省一樣地多;相較之下,人口炸彈可能還要更危險哩。」莫諾他本人認為知識構成了倫理的本質,並在離世之前,也針對科學責任的問題反躬自問。
☆ 跨領域的必要
▍我們至少要有兩個光源啊,不然就只能獲得單一的導標,那很快就會變成帝國主義的專制。[…][…]從語言學到宗教史,從人類學到地理學,我們感激這些重要資訊,沒了它,我們還不可能認識這世界的多元性。人文科學的訓練,讓我們能夠有一般、甚至是普遍的包容,讓我們如空氣般輕柔,至於父執輩所謂的嚴格,如今我們看來都是令人吃驚的武斷教條。假如沒有人文科學,我們這些研究硬科學[自然科學]的哲學也將不復存在。
話雖如此,每道光都伴隨著它的影。正如硬科學的明晰,最終竟投射入高效、卻盲目的「我們」,其慣性正隨質量與加速度繼續成長,也因此使我們亟需人文科學;但同理,若人文科學與事物疏遠,僅探討人際關係,而對世界萬物一無所知的話,那麼它也沒辦法教我們些什麼。
教育的目標在於教育結束;演練的目標在於從此解脫,複製的目的在於最終不再複製。
☆ 論書寫
▍學術論文著眼於可模仿的對象,真正的作品則尋求不可模仿。
▍在歷史上,一旦哲學進了學院、大學,就會沉醉在技術性[術語]裡頭,不能自拔;只要它一離開那裡,就能恢復它簡單的表達方式。因為這個緣故,如今我們更像在中世紀,而遠非啟蒙時代的沙龍。
▍教育的目標在於教育結束;演練的目標在於從此解脫;複製的目的在於最終不再複製。
作者簡介:
Michel Serres(1930~2019)
米歇爾.賽荷
哲學家、公共知識份子、暢銷作家。1990年榮獲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生平著述八十餘本,其橫跨自然與人文的前瞻性思想,在文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均產生重要影響,本書的另一名作者Latour即深受其啟發。
在台灣被翻譯出版的作品有:《失控的佔有慾》、《寄食者:人類關係、噪音、與秩序的起源》(群學);《拇指姑娘》、《劇變的新時代》、《自然契約》(無境);《米榭•塞荷的泛托邦》(麥田)。
Bruno Latour(1947~2022)
布魯諾.拉圖
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作為行動者網絡(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的奠基者,早期他以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作品聞名,中期試圖將ANT理論應用於法律、經濟、宗教等社會次領域,晚期則關注蓋婭理論與人類世等生態政治的命題。從1998年開始,亦密切與藝術家合作,透過影像、圖像、劇場、展覽等方式,呈現學術概念的公共面向。Latour也是2020年北美館雙年展的共同策展人,展題為「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與台灣淵源頗深,曾三度到訪台灣。在台灣被翻譯出版的作品有:〈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我們從未現代過》、《巴斯德的實驗室》、《激情的經濟學》、《面對蓋婭》、《著陸何處》(群學)。
譯者簡介:
陳榮泰
旅居法國,就讀於社會科學高等學院。
伍啟鴻 Kai
臺大物理系、清大哲學所畢業,巴黎高等翻譯學院碩士。
二人合譯有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米歇爾.賽荷著作數種。
章節試閱
◆ I-§0.~§2. 戰爭世代.繼續戰爭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這就是我想搞清楚的地方。你的書並不難懂,卻難找到閱讀之道。你開闢通道,尋遍各處,深入科學(les sciences)、神話、文學,但同時,你又常常抹掉通往成果的足跡。我今天不期待你告訴我們更多新成果,也不是要你評估你其他的著作,我無非希望你幫助我們閱讀你的作品。希望在接下來的對話裡,我們能重拾達到成果的線索,展示你是如何走到那兒的。我希望我們能走進魔術師的布幕背後,得悉誰是你的同行,探聽在你作品底下那些深藏不露的來龍去脈。
米歇爾.賽荷(Michel Serres):要是在十八個月前,我大概會拒絕做這樣的功課;現在的話,我同意大可一試。稍後我再告訴你為什麼。
BL:我的第一個困難是,你在作品中呼喚了赫美使(Hermès);可是,赫美使是中介(médiation)、翻譯(traduction)、繁多(multiplicité),而與此同時,特別在你最近的作品裡,又出現了另外一面,我稱之為「純潔派」(cathare)──這字眼也許不太恰當──它意在孤絕、隔離與無介(immédiateté)。那麼,我先來請教你的學思歷程吧。你不愛論辯;你雖然很有名,同行卻不怎麼瞭解你,而且不可否認,你談起他們,話也時常不太中聽。在你的成長過程裡,到底發生了什麼糟糕的事,讓你像被蛇咬了一樣,對論辯避之唯恐不及如此戒慎?是什麼事逼你跳進隱逸的哲學修行?
MS:我們那一輩聽見我即將要說的話,一定會感同身受。生於1930年左右的人,都像我一樣,身處在生死存亡的環境裡:1936年,我六歲時,西班牙爆發內戰;1939年,我九歲,德軍發動閃電戰,法軍敗北、潰散;十二歲,抵抗軍與合作派分裂,開始上演遣送集中營的悲劇;十四歲,巴黎解放,法國接著算舊帳;十五歲,廣島原子彈爆炸。簡言之,從九歲到十七歲,正值身體與感性成形之時,卻無止境來回於饑餓與配給,死亡與轟炸,在無數罪惡盛行底下偷生。接著,殖民地戰爭馬上登場,先是在印度支那,然後在阿爾及利亞……到了二十五歲,又再開始打仗,因為北非的關係,隨後又有蘇伊士遠征。從出生到服兵役的年紀,在我周遭,對我來說,對我們來說,在我們周遭,除了打仗,什麼都沒有。戰爭,沒完沒了的戰爭……就這樣,六歲時,我第一次看到屍體,最後一次則在二十六歲。我是否已經回答你,我們這一輩被什麼蛇咬了嗎?[…]
BL:但這個歷史時刻,屬於一整代的人。我們更特定談談你自己的教養過程吧。你的高等教育從1947年當「鼴鼠」(taupe)開始;1949年,你被海軍學院(l’École navale)錄取又自行退學,同年得到數學學士學位;你修習「坎涅」(khâgne),獲准進入高師(l’École normale,高等師範學院),並在1955年取得哲學教師資格(agrégation)。你在最優良的環境下受業,也將近十年了。
MS:是最優良,也是最糟糕的環境。戰後時期,從1947到1960年,當時的知識份子按自己的方式──現在我不知該如何描述它──回應那一連串的事件,為此,他們形成的社群,堪稱法國學術界曾經創造過、最具恐怖主義的一個。在裡頭,我從沒嚐到半點自由。在高等師範學院,恐怖統治了一切,跟別處沒兩樣;在那裡,掌權團體有時甚至會開庭審訊,傳喚某某人到評審面前,指控他這樣或那樣的立論非法,說他犯了思想罪。突擊隊會到寓所,把學生一個個搜出來,拉去審判。哲學教授通常也都是史達林主義的。就像1936年那場戰爭,西班牙難民都湧來法國西南部了;或像1939年時,那些集中營、解放時期、我們鄉間所發生的事,就我的記憶,高師幾乎和它們一樣可怕。
BL:我太年輕,沒有那樣的經驗。我屬於你之後的一代。但馬克思主義還不至於完全統治了巴黎吧?
MS:也差不多了。還是那句話,我寧願忘掉,也不想細述那時的氣氛。我還沒說到知識內容,而只是氣氛。恐怖主義大行其道:我甚至說得出來,那時候的私生活多卑鄙無恥。
可以說,早先已被戰事狂噬過,之後又給那學術氛圍咬了一口。
◆ I-§4. 三次科學革命
BL:你當時覺得真正關鍵的,是最前端的數學研究?
MS:我再說一次吧:我真正的成長,是目睹──或幾乎參與了──這門基礎科學所發生的鉅變。從此,我變得超級敏感,開始留意其他領域類似的轉變:我很快就注意到布里盧因(Brillouin),認為他的作品相當重要;還有資訊理論,在物理學裡的,以及很後來,那些觸碰到紊流(turbulence)、滲透(percolation)、無序(désordre)、混沌(chaos)等概念的問題。對我來說,這些轉變跟代數方法的革命一樣重要,都曾令我的精神狀態煥然一新。物理學變了,一個全新的外在世界嶄露頭角。碎形曲線(courbes fractales)、奇異吸子(attracteurs étranges)出現以後,你不會再感覺到像過去那樣的風,波浪、海濱都不再一樣。
而稍後,在生命科學那裡,也颳起了類似的風暴。有了資訊理論以後,即將成為生化學家的新秀很快就明白,革命快要輪到他們了。薛丁格(Schrödinger)在《何謂生命?》(What is Life?)提出的問題,或在法國,莫諾與賈柯(Jacob)的發現,都指出革命將至。然而,那些在談生物學的知識論,講的完全不是這些。
BL:這樣說來,你確實是無師自通,卻有一些人讓你成長了,像你的科學家同事們,他們投入革新,只是當時沒被哲學家所注意。
MS:對,回想起來,有三次革命形塑了我。第一次是數學的,從微積分、幾何學,轉到代數結構、拓樸結構。這是我第一所學校:我們處於兩個數學世界的交界,從這裡畢業的,都會頭腦一新;第二間是物理學的:我較早前學的是古典物理學,但突然間,量子力學跑了出來,尤其還有資訊理論,我們從這裡畢業,得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BL:這些都是在高師學的?邊做邊學?
MS:是在那裡,之後又在別的地方。1959年,同學借給我布里盧因那本新書《科學與資訊理論》(La Science et la Théorie de l’information);之後我便明白了,資訊理論才是真正的物理學哲學。既是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同時又是哲學;這有點像熱力學。事實上,資訊理論正衍生於熱力學。
後來的第三次革命,是因為我認識了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和他成為老朋友──一位很棒的朋友。他教我當代的生化學。他在出版《機遇與必然》(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Chance and Necessity〕)前,請我複閱他的手稿。我因此跟他變得很要好。這是我第三間學校;只要是從那裡畢業的,生命都發生了變化。但這是很後來的事了。給你一點概念有多晚:到了六〇年代末,我的那些哲學教授們還在攻擊莫諾,而且都用那些意識形態的爛理由。
BL:這些革命都沒被知識論記下來……
MS:據我所知,沒有。
BL:也沒記載你一開始提到的暴力年代嗎?
MS:沒有。因此,我的學術養成有別於一般學業體系,也不在那個報章上所謂「大思潮」的社會環境裡頭。唉,但這是好是壞,誰知道呢?大多數與我同時期的人都是那樣成長的;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卻都不在那裡。
於是,我培養了一種習慣,你大概會覺得很奇怪,也就是:我學哲學,偏偏不在一般人認為是教哲學的地方。在外頭,我幾乎學到了一切,在裡頭,卻幾乎什麼也沒學到。對,可以這樣說:一切都在外頭,裡頭幾乎什麼都沒有。
BL:所以,這是關於學術處境和科學危機的問題。這樣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你不怎麼相信科學的社會史研究。要是我們研究那時候的學術界,是不是就完全沒有辦法瞭解那些對你產生影響的事情?
MS:確實如此,幾乎完全沒辦法。除非你靠近一點看,到底發生了什麼──噢,我差點要說,「事實上」是什麼。我們剛叫它什麼來著,學術界?你說到「處境」:我跨步於人文與科學之間。在一邊,除了強加於人的高速公路和學究形式以外,什麼事也沒發生;在另一邊,則不停上演革命,每一次,我想可以這麼說,我都在場、見證,並且參與其中。
◆ II-§3, 7~8. 時間.風格.文學
BL:一直以來讓你感興趣的,是相反的動作:拎起盧克萊修,跳過那些忽略他、說他過時的哲學家們,把他帶到當今流行的物理學假說去。
MS:沒錯,就是這樣。而且,這些方法、策略、或計謀,是為了回答另一個關於「損失」的問題。凡事皆有代價。隨著科學進步,我們得到了好處,卻鮮少評估那些在文化上相對應的實際損失。[…]
BL:我懂,但這伴隨著雙重的困難:你所重新使用的作者、文本,都是知識論學者認為被罷黜、或過了氣的……
MS:舒曼曾笑說:「當你聽到某些人說貝多芬已經過氣,那就去聽聽他們自己的音樂吧!」通常這些人就只會寫些平庸的抒情歌。[…]
BL:你從來不說:「我們至少要尊重它們的不同、它們離奇古怪的地方,這是過往的有趣見證。」對你來說,這從來不是異國情調的問題……
MS:你說得對。
BL:……它們的過往、它們的不同,並不會抵消其真實性、或理性。你並不用歷史學家、或民族學家的方式,來尊重它們的不同。你把它們同最現代的論點並列在一起。
MS:是的。
BL:當然,這並不是沒有風險的……
MS:風險是,古羅馬拉丁學者固然對熱力學不屑一顧,科學家也嘲笑「微偏」。這便定義了何謂研究者的孤獨;當然,這沒那麼嚴重,重點還是要尋找公正。在尋找的時候,誰不是獨個兒的呢?
BL:這問題我們一定得談談。
MS:真的,專業的確有其風險,必須覺悟這是有代價的:一方面,古典人文學者再也認不出他們看習慣的盧克萊修;另一方面,科學家則對他的故事完全不感興趣。
但這開始在變了。談紊流理論的人開始說:「沒錯,事實上啊,盧克萊修那兒就已經有這些東西了。」每次重大發現,在闖過近人所設立的障礙之後,便會突然掀開一個充滿智慧的過去。每一次的進展,每一次的記憶還原!每項發明既揭示了真實,也展露了歷史。
BL:我們稍後再回來談這一點。總而言之,當下的時間,讓你得以抄小路,越過那些聲稱時間已過、實際上卻寸步不移的人;與此同時,你也不認為「尊敬時間性的唯一方式,就是照著歷史學家來做」。可以這樣來界定你的工作吧。
MS:可說是讓死者重生的文獻工作。但大學的分化極度嚴重,它一邊訓練科學家,一邊培養純文學學者,結果令雙方訊息交流困難重重。
BL:在進一步談這一點之前,我想確定我有真的搞懂你剛才說的事。你說,讓你感興趣的這種特殊的時間體制,不主張文理分離,是以跟當今流行的正解截然不同。文理分離,只會迫使古典人文投入歷史主義的懷抱,滿足於停留在過去的殘留,以發掘其獨特性為務;同時,在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觀點下,科學則做著一種「自發的哲學」(philosophie spontanée),逐年刪除歷史紀錄,也許是每小時就刪掉前一個小時的。
MS:沒錯。
BL:所以說了兩次都是這同一個問題;要對付的問題既是關於時間,也是關於科學。
MS:也關於跨學科。[…]
BL:你的方法裡的每個成分都被人誤解。我們以為:你是為了規避方法上的限制,才隨意地漫步;你盡可能地跟數學保持距離,達成了風格,這是出於文學上的選擇,跟技術上的理由完全無關。可是,假如我聽懂了你所說的,那事實上,在一個數學無法進入的領域中,採用一種盡可能準確模仿數學的風格,這樣的風格是最好的。
MS:至少要數學的嚴謹、精確。柏拉圖他不就是這樣做的嗎?每一次當他碰到什麼不好寫的東西,他便放棄技術用詞,前往神話,說個故事來涵括他的話。他總是從這裡「滑到」那裡,就像你之前說的。數學或邏輯到不了的話,就讓神話去唄!所以在柏拉圖那兒,或其他許多人那兒,才會出現偏離、跳躍、斷裂,從證明到敘述,從形上學到民間傳奇。萊布尼茲的《神正論》就是這麼搞,沒什麼好奇怪的。[…]
BL:同時,你的哲學工作並不在於用你本人的後設語言來覆蓋文本,反而是用了那些文學家的、或那些神話的後設語言,以便完成你的哲學或科學工作……你並沒有幫我們把事情弄得更簡單啊!
MS:事情本身是簡單的嗎?
說實在,當你沒有榜樣的指引,被迫在沙漠裡徘徊,你並不總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科學社群的持續存在、不斷辯論、同儕壓力等等,這些是你之前提過的,正好也是我相當欠缺的。這一切都能有助於澄清問題。孤獨常伴隨著困難,並能說明困難。當兩個人在一起,正如我們今天這樣辯論,就已經釐清了許多事情。所以你看,在關於討論的哲學問題上,我開始變了。
◆ III-§4, 6 說明.綜合
MS:我過去批評過的那些評論,或許可稱為帝國主義的一種吧──但其實,我現在已經志不在此,因為評論太寄生了,它本身只是發明的寄生蟲──說是帝國主義,是因為那些評論只用一把鑰匙去開所有門和窗:不論精神分析、或馬克思主義、或符號學等等,都是萬用鑰匙。帝國主義當然不只涉及內容和方法,還有機構:哪個系、哪間學校被哪個學派把持著,其他學派休想插手。思想自由之花,並沒有真的在大學綻放。
與此相反,我更在乎的是奇異性、或局部細節;在那裡,單一化的萬用鑰匙便不管用了;反之,只有精工細琢(ouvragé)的工具才是適用的。沒了它,就沒有作品(œuvre)。局部問題,必須新創局部方法加以應付。每次要打開一道不同的鎖,都得要打造一把特定的鑰匙;所以它必定是陌生、疏異的,在方法市場上找不著等同之物。那串鑰匙很快就變得相當重。可是,你所謂的後設語言卻好認得多:只是同一把鑰匙的不斷複製,在哪兒都買得到,像大賣場,還打著廣告叫賣著哩。
BL:這我懂,每一次面對新的研究對象,都需要重弄、重造分析工具。
MS:真的是每一次。所以才需要用局部的詞彙,以盡可能接近難纏的問題。假使不知道特定用詞,是要如何談樑架?如何談航海?如何談鍛造?正如不知鑽錐、皮革相關用字,便休想能談皮匠……這既是關於風格,也與方法或證明有關。[…]
BL:的確,這些例子全都很有說服力。這就是我剛剛提出的問題。我們必須做調和:一方面是有關綜合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必須一而再地鍛造適合局部的工具。你保留了證明所通常有的特徵,如獨特性、清晰性、節省性、封閉性、飽和性、綜合性等等。[…]
MS:你為何不問我另一些、或許我會更喜歡的問題?例如,一旦我決定擺脫掉寄食者後,到底是什麼使得哲學家同行決定不再視我為其中一份子?你為何不問問噪音、疏離(détachement)的問題?不問問身體、五官、塑像、死亡、花園、整體地球(la Terre globale)、自然契約之概念、教育學、哲學重組等等的事情?
BL:但第一個時期的賽荷並未比第二個時期更好懂。所以,我還是想繼續談談他,之後再來談你放棄評述的理由。
MS:好吧,那我就勉為其難,回頭來談證明了……我的證明嘛,總是依據相同的規則來進行,但我的確從來不用固定的術語。我的證明的開頭差不多是歸納的,而且,跟單一性的理論相反,我總是從眼前的作品或問題中,提取有差異的元素,並且兼採類比與差異之手法;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這是一種著重形式和關係的思考方式。是以,我的證明並未得到一個初始點、起源或者唯一的解說原理。即便這些一向被認為是系統、連貫性的關鍵,甚至是得出意義之所必須,但我所嚮往的卻是關係,它們雖各有差異,卻又有組織地被安排在一個集合裡。
BL:這的確是在做綜合,你確實有綜合的精神;但卻沒有系統,也沒有系統化的精神。
MS:沒錯。在這裡,綜合跟系統並不一樣,甚至跟單一方法也是有差別的。一組差異化的關係,才構成一體(corps)。
為了描述此差異化的關係集合,我正準備寫一本談介系詞的書。傳統哲學藉由名詞、或動詞來思考,而不用關係。因此,它總是發軔於某個照亮一切的神聖太陽,或始於某個讓歷史最終就範的開端,或某個以便進行邏輯演繹的原理,或某個賦予它意義的邏各斯(logos),或某套組織辯論的遊戲規則……如果少了這些,結果便是嚴重的毀壞、懷疑、四散,當今看到的一切潰敗。
直覺地想,這正是你在問我的,也是哲學家一直被要求回答的問題:你的基礎名詞是什麼?存在(existence)、存有(être)、語言、上帝、經濟、政治,如此等等,只要字典有的都可。所以你會被問:你從哪裡取得意義、嚴謹性?你的系統稱為什麼「主義」?或更糟的:你迷上了什麼?
我的回答是:我零零散散地從「關係」開始。我看個別的關係,它們各有差別,所以才顯得散漫,才有你向我提出的問題。但我也會盡量看到所有的關係,以求最終能把這些差別的關係包攬在一起。容我指出,我的每一本書都描述了一種關係,通常能以一個獨特的介系詞所表述。《干涉》,談的是處於「之間」(entre; between)的時空;《溝通》或《自然契約》,談的是「一起」(avec; with)的關係;《翻譯》,談的是「通過」(à travers; across);《寄食者》,談的是「在旁」(à côté de; beside)……等等,等等。《塑像》則從反面著手,問的是:在沒有關係時,會發生什麼?
◆ IV-§10 物.集體
BL:二十世紀的科學哲學,在美國有孔恩(Kuhn),在德國有哈伯瑪斯(Habermas),在法國有科學社會學,它們都花了不少時間,用認知集體替換認知主體。
MS:真可惜。人們曠日費時,就只是為了修改一些單純的人造物。但,另一方面,這又是多大的改變啊!「我們」的運作跟「我」完全不同,簡直天差地別。但無論如何,兩者都難以理解。
BL:我們把這位置稱為「主體/集體」吧。
MS:好。[…]
BL:現在,我試著把你定位在批判哲學的對立面。為此,我要把刻卜勒的橢圓一分為二。在最上面的,是一種愈來愈強大的努力,誓要把純神話和純科學區分開來。而現在,最好玩的,是把這些哲學家的努力,以及這世上發生的一切,兩者疊在一起。那麼,我們便有了準客體、雜種、怪物、巴力-挑戰者號、天-父,等等,由於第一、第二、第三次的工業革命,這類東西愈來愈多。每一次,當準客體增加,哲學家就複雜化……
MS:……那些我們眼前正發生的事。
BL:當人們一邊在做哲學〔純化〕工作,另一邊卻完全相反,準客體不停在增生。因此,我們清楚地看到你的書起了什麼作用。
MS:我曾經夢想著,這些書將能有助於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當然,我並沒有完全相信這一點。也許正因如此,我也無法說服我的同代人去相信它。你讓我如釋重負,我要謝謝你,讓我對辯論改觀。
BL:正是如此,我們始終有必要置身於中道(position intermédiaire)。
MS:這是三百年來,所有哲學的盲點。
BL:這是一個節骨眼,是兩個極端的接合點。然而,正是在這裡,你的混雜理論就很重要了,因為你從不把它想像成不同純粹形式的混合。可是,這卻是康德的見解,他要把兩端洗滌得乾乾淨淨,再讓它們重新結合為現象。於是,現象被設想為一種能被完全決定的混合,由純粹的客體形式,加上純粹的主體形式混合而成。但你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MS:基於同樣理由,《自然契約》才引起了反彈。既然自然只是物件或客體,它又怎能變成契約裡的合作伙伴呢?[…]
BL:正因如此,搞後現代主義的也讀不懂你的《自然契約》,一如你其他的書那樣。現在,自然變成需要被保護、而非被主宰的東西,那麼,對他們而言,便不知從何來思考它了。在我們眼前正在結束的現代思維裡,已經沒有任何地方能容納一個人為造就出的自然。這是不可思議的雜種。所以我們才得重頭來過,一切重新開始。
MS:所以我才提到「天」「父」(Ju-Piter)的譬喻(parabole)。
BL:的確,這譬喻非常有啟發性。
MS:我從未離開過它。
BL:對你來說,在中間處,那裡有著不少有趣的東西。
MS:那裡的一切都很有趣。
BL:而這便扭轉了我們對歷史的想法,因為你以不同的方式,重新運用過去。過去不再是過時,那只是激進革命所予它的特徵。而你卻置身於中道。萬物本身有其歷史,是以並非只在外在自然(Nature)的那一端。這是你的研究裡頭最有趣的一面。當你批評無宇宙主義(acosmisme)時,你並沒有回到客體……對你來說,事物總是生動的、社會化的,成千上萬出其不意的事都會發生在它們之上。而另一方面,「社會」(le social)也並非像社會科學所說的那樣。它又再一次地充滿著萬物。
MS:人性(humanité)始於物件(choses);動物並沒有物件(objets)。
BL:大家真的完全沒搞懂。
◆ V-§6, 8 惡.道德
BL:你重啟惡的問題,是否想要恢復過往哲學或神學所思考的、且為古典人文所載的大哉問?可是啊,批判哲學認為這問題已經被甩掉了,而且無論硬科學、抑或人文科學,都認為它已經過時啦。
MS:關於這一點,我們需要回顧歷史,看一下法律、科學、哲學三者之間的關係。
簡而言之,我們正經歷著某個循環的結束。據我所知,這循環從萊布尼茲的《神正論》開始,即便其根源恐怕可遠溯至歷史之初、世界之創立。我們來討論他的問題:痛苦、不公、疾病、饑荒、死亡,簡單講,就是我們一概視為「惡」的種種東西,到底要拿它們怎麼辦?或以更好的說法,這看起來更有效、更公道:我們能夠指出來,誰該為這一切負責嗎?
套用我們前面曾說過的:「所謂『一切操之於我們』者,它已非操之於我們」。我們能否指出某個單一的人,或集體中的某些人嗎?或者說,這個我們熟悉不過的「我們」,以及那個陌生的「它」指的是誰?[…]
你曾以「非批判」(a-critique)來稱呼我的天真,但如今在我看來,這批判傾向比我本身還要天真多了呢。因為它的出發點是:假定有一個或多個人必須負責,對於惡、苦難、不公正等問題,這主體或集體責無旁貸;然而,它卻沒有首先對被告所處的位置本身提出疑問。
BL:你的意思是,我們必須繼續思考惡的問題,但不再以批評的方式尋找可以指責的人或事。是這樣嗎?
MS:是的。追根究底,即便批判哲學不信上帝,它依然相信上帝的位置。批判不再相信存在有一位創世的上帝,但仍相信有一個或多個邪惡製造者,即撒旦、或一百隻惡魔,正在輪替、候補。於是,批判把所有通常的被告當事人,把我們所學習、傳遞的名字,一一放在這個位置上:男性、父親、剝削者、白人、西方人、邏輯中心主義、國家、教會、理性、科學……這些當中的每一個,毫無疑問,都曾犯下彌天大罪,深深捲入事件之中。[…]
不然我來提供兩個例子。
先從集體講起。即便我當然沒辦法證明,但我的直覺卻常告訴我:在社會或道德問題上,有某個無法估量的定值,就像是整套力學或熱力學的第一定律所指出的常數。暴虐的帝國酷刑固然有其不公,濫殺不少無辜;但當這帝國解體,亦會引發無數種族仇恨與戰爭,同樣屍骸遍野。數量相較起來不多也不少,兩者之間存在一個可怕而神秘的等號。如此一來,若把人類劃出一定區塊,裡頭所含的暴力量便似乎恆定不變。這經驗對我是那樣地尋常,以至於伴隨著我的一生,並啟發了我對歷史的認識。
要證明這一點,我們尚欠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才能把恰當的部分劃分出來。惡仍如其舊,無論它如何改頭換面,卻總是維持相同的力量,整體來說,仍產生同等份量的毀壞。
然而,我們知道,類似這一類的常數建立起與其對應的科學。因為,我們的思考或多或少都必須以「變而不變」(invariance par variations)為立足點。
BL:那麼,這會不會就是惡的「第一定律」?
MS:我相信是的。因此,整個道德,也許還有政治,都在於先行正面認清這定律,然後盡力發明方法來凍結某種潛在性:惡持續窺伺埋伏著,隨時準備用其可怕的效率,放出凶殘的獵犬。因此必須以智慧的目光,對這些凝結以及爆炸保持戒備。比如說,任何政治體系在本質或憲法上,皆不能豁免這樣的警戒。
BL:那麼,問題在於管理和調動惡的定量,而非糾正它?你的說法確實帶給我們一個光明的未來!
MS:延續《寄食者》的思路,我們必須不斷重新改述同一個問題:何謂敵人?對我們而言,他是誰?如何對付他?換言之,例如:何謂癌症?是惡性細胞群的異常增生,以致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將它驅逐、切除、丟棄嗎?或者像是寄生物一類的東西,能與之協議共生?我傾向第二種解法,生命本身就是如此;我甚至敢打賭,未來治療癌症最好的方法,不在於把它消除,而是利用它的活力。
為什麼呢?因為客觀來說,我們必須持續與癌症、微生物共存,甚至與惡、與暴力同住。與其一再啟動永無勝算的戰爭,不如尋求共生的平衡,即便這分配得不十分均勻。因為,我們和敵人都會在這關係中找到新的力量。如果我們學清教徒的做法,清除所有病菌,趕盡殺絕,那麼,微生物很快就產生抵抗力,本來的消滅技術無效,便需要更新軍備。但把它放在凝乳裡接種呢,有時候卻會產生美味的乳酪!
◆ I-§0.~§2. 戰爭世代.繼續戰爭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這就是我想搞清楚的地方。你的書並不難懂,卻難找到閱讀之道。你開闢通道,尋遍各處,深入科學(les sciences)、神話、文學,但同時,你又常常抹掉通往成果的足跡。我今天不期待你告訴我們更多新成果,也不是要你評估你其他的著作,我無非希望你幫助我們閱讀你的作品。希望在接下來的對話裡,我們能重拾達到成果的線索,展示你是如何走到那兒的。我希望我們能走進魔術師的布幕背後,得悉誰是你的同行,探聽在你作品底下那些深藏不露的來龍去脈。
米歇爾.賽荷(Mich...
推薦序
譯者導讀
賽荷與拉圖:科學人類學的交會
這一系列訪談是在一九九一年進行,最初由布魯諾.拉圖提議。前一年,賽荷剛獲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他和天文物理學家皮耶爾.雷納(Pierre Lena)合作的天文學紀錄片影集《環遊天際,環遊世界》(Tours du monde, tours du ciel),正在法國公共電視台上映,獲得了熱烈的迴響。此前,他接連出版的哲學隨論《自然契約》和《第三學子》兩書都登上了暢銷書之列,也受高收視率的讀書節目「猛浪譚」(Apostrophes)邀請談其新書。或許是賽荷說故事時的迷人魅力(尤其還帶了點法國南部的加斯貢腔),當時他已是法國媒體的寵兒,演講、談話邀約不斷──但奇怪的是,他寫的書卻被評為「非常難懂」。如同波布斯期待與普桑一起揭開遮住費朗霍費畫作的布幕,拉圖也希望透過問答,為讀者提點線索,諸如賽荷使用的證明方法,他在知識論或價值層面的判斷,甚至是他的形上學許諾,讓讀者不致迷失在賽荷著作的風格迷霧裡。本書裡拉圖與賽荷兩人間的對話甚或爭論,應能有助於對賽荷著作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的閱讀。
不過,如果從今天來看,本書在問世三十年後似乎還有另一種讀法。訪談進行的同一年,拉圖出版了《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在這本篇幅不大的論文裡,拉圖利用此前新興研究領域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技與社會研究)的集體成果──尤其是謝平與謝佛(Steven Shapin & Simon Schaffer)對波以耳與霍布斯關於真空是否存在的論爭所做的經典科學史研究──建立說明現代性困境的模型。在冷戰似乎結束而生態環境問題突然登上檯面的情境下,這本書很快引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廣泛關注。
拉圖的讀者應會注意到,除了STS的養分,賽荷的著作也是《我們從未現代過》的重要資源。拉圖似乎首度在該書完整表達其哲學關懷(儘管採用負面表述的方式),並將之延續到後來對生態政治、乃至存有模式的探問。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回頭重讀拉圖如何吸納賽荷成為其思考養分,對讀者應會有所幫助。[…]
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生態突變的議題又把兩人的工作拉近。比如,在拉圖和科學史者阿伊-杜亞蒂(Frédérique Aït-Touati)合作的劇場式講座《顛動地球》(Moving Earths)裡,拉圖把布萊希特的劇作《伽利略的一生》(Leben des Galilei)和賽荷的《自然契約》並列,指出兩者各自呈現了人們對地球之認知的兩次重大劇變:一次是發現地球是繞著太陽移動,另一次則是發現地表實是一個會翻騰、激動的複雜系統。賽荷從法律的角度探問在世存有(être au monde)所處的生態新變局,相較之下,拉圖對蓋婭的新解則常被視為把生態問題政治化的嘗試。但兩人對生態議題的關注,都源自於他們對科學與宗教的思考。
繞道
拉圖曾被形容為「賽荷星系」裡耀眼的一顆星。不過嚴格來說拉圖並不是賽荷的「弟子」,畢竟在認識賽荷之前,拉圖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也早為自己擬定了一個近乎終生的研究計畫。若要了解在上世紀八〇年代賽荷的哲學計畫如何接連到拉圖及其同事在巴黎開創的STS研究社群,也許必須要回到拉圖更早先的學術生涯。
拉圖生於勃根地博納(Beaune)的自由派布爾喬亞天主教家庭。他在高中最後一年的哲學課上讀到尼采,從此立志走哲學這一行。雖然曾打算進入師範學院,但在結識了宗教哲學家安德烈.馬勒(André Malet)後,拉圖後來決定到後者任教的第戎大學就讀,研究解經學(exégèse)。一九七二年,拉圖以第一名成績通過當年法國中學哲學教師會考。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間,他參與法國海外合作計畫(用以替代當時法國男子的義務兵役),與新婚妻子到象牙海岸的阿比尚,擔任當地技職中學的哲學教師。為了「保持智識活力」,他加入了海外合作計畫的社會科學團隊,參與發展社會學的研究。當時,法國社會科學家關心的問題是象牙海岸獨立後的發展「困境」(象牙海岸於一九六〇年脫離法國獨立),比如,反思法國企業外派主管常有的抱怨:他們認為即便獨立,當地人仍沒有足夠的能力接替前殖民者擔任幹部之職。拉圖自言此前對社會科學一無所知,但在前法屬殖民地的經驗給他很大的震撼,讓他「同時發現了最具略奪性的資本主義形式、民族誌的調查方法,以及人類學的謎題。」
為反思後(新)殖民情境下前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拉圖興起了調查「現代」社會的念頭:是什麼讓這些前殖民者相信自己比別人更為現代?自從社會學家莫杭(Edgar Morin)在一九七〇年出版了《加州日記》(Journal de Californie)以後,在法國年輕人眼中,美國西岸已成為現代性的先鋒。於是,一九七五年拉圖回到法國並完成他的哲學博士論文《解經學與存有學》(Exégèse et ontologie : une analyse des textes de résurrection)後,便在同鄉神經內分泌學家吉耶曼(Roger Guillemin)的鼓勵下,申請一項「對稱人類學」計畫,前往他在加州沙克研究所的實驗室——儘管吉耶曼原本以為拉圖是要去做「知識論」研究。
不過,拉圖對科學實驗室活動的興趣,也與他在博士論文期間發展的想法有關。在第戎大學(現為勃艮第大學〔Université de Bourgogne〕),拉圖接觸了德國學者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等新教神學家對聖經的脈絡化解讀。依據這種解讀,聖經文本不再是(至少很少是)關於宗教事實的陳述,反而是讀者對基督之言一再解讀、轉化與創造的結果。既是解讀,讀者便時時面臨著忠實與背叛的考驗。不過,對拉圖來說,解經學雖然把經文視為詮釋的過程,從而解構了教條的確切性,但這麼做並未貶低聖經等宗教文本的真理價值,反而讓人得以探問何謂真實的宗教話語:宗教話語可能為真,前提是以一種特屬於宗教的方式說出。但要知道宗教真理的特異性,他還必須和其他亦在生產真理的領域進行比較。在現代社會,科學便是不二之選,畢竟一談到真理,很多人便想到科學,甚至只想到科學。
在加州期間,拉圖為自己補了很多課。除了默頓(Robert Merton)的美國科學社會學以外,部分因為與社會學者伍爾加(Steve Woolgar)的認識,拉圖也接觸到英國於新興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拉圖自言,當時他對SSK的興趣要甚於默頓探討科學專業的社會學,畢竟SSK也試圖解釋科學真理的生產。為了研究有別於宗教文本的科學文本與實作,拉圖也自學了俗民方法論和符號學,這些研究工具雖來自很不同的脈絡,卻似乎能與解經學相容。
回到法國後,拉圖嘗試把英語世界的STS引介到法國,除了翻譯相關著作,他也在一九七八年和卡隆共同創立了《潘朵拉》(Pandore)通訊報,提供不同背景的人士討論科技與社會之相關議題。這個跨領域的通訊管道成為法國早期STS發展的重要平台。一九八二年,在卡隆的邀請下,拉圖加入了巴黎礦業學校的創新社會學中心,一個別具特色的STS社群便在巴黎逐漸成形。
日後,拉圖有時把他STS的研究描述為一場大繞道,儘管如此,對許多讀者而言,拉圖最具啟發性的想法也許正是來自一九八〇年代的研究工作。他對巴斯德工作的新解開啟了微生物人類學的豐富研究(《巴斯德的實驗室》),其教學著作(如Science in Action)也成為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的經典讀物,至於某個意義下綜合了此時期工作的《我們從未現代過》,則宣告了他的哲學人類學計畫:盤點現代世界的各種「真理體制」或「存在模式」。
科學的人類學
拉圖雖然任職於創新社會學中心,卻把自己的研究定位為「科學的人類學」。其實,這個歧義之詞恐怕是連結賽荷「西北航道」與拉圖「STS迂迴」的重要線索——在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兩人不約而同用了這詞描述自己正在著手的研究計畫。
拉圖在非洲有了人類學初體驗,又在美國加州的前沿科學室進行民族誌調查,完成人類學者的「通過儀禮」,並在一九七九年與伍爾加出版了他們的《實驗室生活》一書。在這本書,拉圖已把自己的工作定義為科學人類學。當時在美國,「人類學」(anthropology)和「民族誌」(ethnography)二詞時常交替使用;類似地,在《實驗室生活》裡,「科學人類學」也更常是在指一套民族誌方法,粗略而言,便是像民族學者那樣調查科學部落,反思他我之異同。拉圖用專業民族學者看來頗為天真的方式和調查對象(實驗室科學人員)保持距離。伍爾加便很驚訝於拉圖能夠泰然自若對實驗室維持一種「陌生」感。他回憶第一次參觀吉爾曼的實驗室時,拉圖很嚴肅地拿起桌上的一支移液滴管,對他說:「有了這個,他們〔科學家〕便想像能夠測定出液體的量。」說完,慎重地把移液管放回桌上。
以外來者之眼觀察構成自身所處世界(現代世界)的關鍵地點(實驗室),這並不是故作姿態,而是為了進行「對稱」人類學調查不得不然的策略。拉圖認為應當使用同樣方法研究科學社群與初民部落,而非事先預設(即便是出於恢復後者名譽的動機)兩者具有對立的區別,諸如科學/拼貼(Claude Lévi-Strauss)、日常推理/科學推理(Harold Garfinkel)、科學精神/前科學精神(Gaston Bachelard)、反對矛盾/接受矛盾(Robin Horton)等。為了解釋科學活動最關鍵的特徵(產生具一定普遍性的科學事實),拉圖為科學人類學提出一個相反的原則:拒絕任何事先的大區分。基於某種經濟原則,或者應當說,基於混沌理論帶來的視野變化(顯著的現象未必來自巨大的原因),拉圖提議用微小的原因(差異)去說明最大量的效果(鴻溝)。他從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古迪(Jack Goody)和法國哲學家達勾涅(François Dagognet)對書寫文化與銘記(inscription)技術的研究得到啟發,指出不同人類社會多少都有的一些普通實作,如記錄、圖像等視覺化技術,能夠在一些情況下調動個體的意見,協調其間的行動,進而產生某種集體性。由此看來,民族誌便是在描述這些集體性形成或消解。實驗室的民族誌不外如此。
拉圖的自學民族誌雖說帶了點土法煉鋼之感,但拿個榮譽人類學家的頭銜仍應當之無愧。相較之下,要說賽荷是人類學家就有點勉強了,畢竟他既不曾做過「田野」,和專業人類學者的交往也不算頻繁。一九八〇年代起,賽荷較常提及「人類學」,並在《塑像》這本拉圖口中賽荷最好的著作之一裡,開始使用「科學人類學」一詞。事實上,賽荷口中的科學人類學比較不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或研究方法,而是有別於法國知識論傳統的一項哲學方案,用於探索科學與世界的關係。杜梅齊勒(Georges Dumézil)與吉哈(René Girard)的宗教研究尤其啟發了他的人類學轉向。
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準備博士論文時,賽荷對法國的知識論(前後兩位領銜人物巴什拉和康紀言〔Georges Canguilhem〕都是賽荷的指導教授)已頗有保留。由於賽荷自己的科學訓練,加上與科學家交流的經驗(或許也要考慮當時模控理論帶來的新型思考),他很早便認為科學知識本身便會反身生產關乎自身的理論,因而不需要知識論之類的外部評論。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哲學的任務不再是提供科學理據或是描述評論科學的意涵,哲學與科學的關係恐怕變得更像啟蒙時期那樣:哲學透過盤點、收集、整理一切能及的局部、百科的知識,但還包括探索被排除在科學以外的其他理性形式,其任務在於催生將要浮現的整體知識圖像。儘管科學知識不斷分枝並且專門化,窮盡一切知識並不可能,但哲學能做的,是打造環遊知識世界並建立其間關聯的可用工具(賽荷最初找到的工具是結構分析)。
但對賽荷來說,環遊知識世界並非目的本身,哲學首要的關懷還是存在於世的問題,亦即人與世界的關係。這便涉及到賽荷對當時法國知識論最主要的不滿:對當代科學造成的暴力破壞置若罔聞——廣島原子彈爆炸是最悲劇的例子。換言之,這也是理性(秩序)與暴力(混沌)矛盾互生的問題。某程度來說,賽荷追蹤的當代科學(熱力學、資訊理論、分子生物學、甚至生態學等)已內含此後設問題(追問的比較不是知識的知識,而是知識的正義),但他在吉哈的慾望模仿、暴力與犧牲的討論找到了適合的表述方式。吉哈分析大量文本,為人類社會的犧牲作為提出理由:人類個體之間的慾望模仿造成敵對關係,為免全面敵對導致集體瓦解,人類社會隨機挑選個別受害者(替罪羊),壓抑著總是潛藏的暴力,並維持在人類社會中,永遠只是暫時穩定的集體秩序。
兩人於一九七〇年左右在美國水牛城相識,後來成為終生好友。事實上,企圖透過吉哈的理論,探問物理科學的混沌、自組織、複雜性等現象用於思考人類社會問題的潛力之學者,賽荷並非唯一一人。儘管如此,賽荷的獨到之處在於,他在吉哈的人類學理論和他更熟悉的自然科學之間看到一個重要的線索,可用於探索科學與暴力的關係:非人犧牲/牲祭(也就是華語「物」的原意)在維繫人類集體所扮演的角色。賽荷嘗試把吉哈提出的犧牲動態過程,結合到他此前已很重視的杜梅齊勒自印度-歐洲文化比較研究中發展的「三官理論」,隨即指出:要阻止集體的崩解,不一定只能靠隨機的犧牲或集體謀殺,還能透過物件之流通來維繫極易失序的人類集體,諸如讓人崇拜的物神(fétiche)、戰爭競逐的賭注(enjeu ; stake)與流通交易的商品。
賽荷把這些流通於集體之間、維繫集體穩定的「物」稱為「準客體」(quasi-objet),並用團體球賽的比喻描述準客體(球)維繫集體(團隊)秩序的過程。正如少了球,球賽便無法進行,缺少流動的準客體,集體秩序也將瓦解。在這樣的動態影像裡,主體與客體是停頓的片刻:就像持球瞬間的某人成為群起圍攻的對象,所謂主體不過是一時被挑選出來的「受害者」,而不再具聯繫作用的靜止客體(例如球賽後被擱在一旁的球),則沉默地見證曾存在過的集體。
準客體的模型,如何有助思考科學與暴力(集體性之崩解)的關係?賭注、物神、商品都是集體的發明,人們藉其流通,以對抗失序之威脅。然而,留存的塑像遺跡卻沉默地見證到,這些社會物(建立社會連結之物)只能推遲暴力,卻無法一勞永逸地消除暴力。事實上,對它們的濫用,往往引發更大的暴力。循此,賽荷對科學在人與世界之間的中介角色,提出了一個疑難:一方面,作為人類另一種極不可能(發生機率極低)的集體發明,科學似乎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非關「利害」的認識活動,有別於宗教、戰爭或經濟等更涉及社會秩序的人類活動;另一方面,科學物(科學探究的對象及產物)卻又是不折不扣的社會物,就像賭注、物神與商品,科學物也能帶來暫時的和平,但也像這些與宗教息息相關的物件,若不夠謹慎對待,很容易造成集體的崩解,以如今科學的規模而言,甚至是全球性的毀滅。
就像其他社會物的發明,每一次重要的科學物的出現,都伴隨著新的集體秩序。準客體理論只是幫助想像(科學)物與集體秩序之關係的一個模型或一種虛構(fiction)。事實上,賽荷不太相信可以依賴文獻考察,找到任何物件-集體形成的歷史事實,對於此科學和宗教相會的人類學問題,他更傾向求諸各地文化皆有所發展的文學(故事、神話、寓言、戲劇……)加以表達。哲學可以向傳統人文技巧借鏡,探問自身和科學的關係。
譯者導讀
賽荷與拉圖:科學人類學的交會
這一系列訪談是在一九九一年進行,最初由布魯諾.拉圖提議。前一年,賽荷剛獲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他和天文物理學家皮耶爾.雷納(Pierre Lena)合作的天文學紀錄片影集《環遊天際,環遊世界》(Tours du monde, tours du ciel),正在法國公共電視台上映,獲得了熱烈的迴響。此前,他接連出版的哲學隨論《自然契約》和《第三學子》兩書都登上了暢銷書之列,也受高收視率的讀書節目「猛浪譚」(Apostrophes)邀請談其新書。或許是賽荷說故事時的迷人魅力(尤其還帶了點法國南部的加斯貢腔),...
目錄
推薦序 賽荷的時間機器/張君玫
譯者導讀 賽荷與拉圖:科學人類學的交會/陳榮泰
第一次對談:成長
§1. 戰爭世代|§2. 在學院裡繼續戰爭|§3. 自學者?|§4. 三次科學革命|§5. 廣島:從科學到人文的通道|§6. 韋伊的非暴力哲學|§7. 從哲學到古典人文|§8. 巴什拉與孔德|§9. 徒勞的討論
第二次對談:方法
§1. 所有作家都是我們的同輩|§2. 過去,不再是過時|§3. 既非審判,亦非缺乏審判|§4. 另一種時間理論|§5. 赫美使:牽接的操作子|§6. 數學家的方法|§7. 風格:其他延續數學的方式|§8. 文學:在哲學的監督之下
第三次對談:證明
§1. 說明之來龍去脈|§2. 必要與非必要的困難|§3. 綜合終究是可能的|§4. 評論之善用|§5. 重複|§6. 局部的說明、整體的證明|§7. 第二種手法:是運動,不再是文本|§8. 抽象:始自陳述,不再始自命題|§9. 赫美使:零散與綜合|§10. 赫美使與天使的綜合|§11. 不要歌頌破碎,而是歌頌脆弱的綜合
第四次對談:批判之終結
§1. 遠離知識哲學|§2. 遠離哲學審判|§3. 遠離哥白尼式的革命|§4. 走向科學人類學|§5. 別再搞哥白尼革命|§6. 遠離揭露與告發|§7. 天-父:在雙重揭露之後,一切尚待完成|§8. 關上批判括弧|§9. 刻卜勒的橢圓與其雙焦點|§10. 在哲學的盲點上,一切從頭開始
第五次對談:智慧
§1. 智慧與哲學|§2. 客觀的道德|§3. 被遺忘的古典人文|§4. 除教育不成道德|§5. 脆弱作為歷史推動者|§6. 客觀的惡|§7. 不可能的質疑|§8. 美德的基礎|§9. 事物走進集體之入口|§10. 論道德律
拉圖著作列表
賽荷著作列表
推薦序 賽荷的時間機器/張君玫
譯者導讀 賽荷與拉圖:科學人類學的交會/陳榮泰
第一次對談:成長
§1. 戰爭世代|§2. 在學院裡繼續戰爭|§3. 自學者?|§4. 三次科學革命|§5. 廣島:從科學到人文的通道|§6. 韋伊的非暴力哲學|§7. 從哲學到古典人文|§8. 巴什拉與孔德|§9. 徒勞的討論
第二次對談:方法
§1. 所有作家都是我們的同輩|§2. 過去,不再是過時|§3. 既非審判,亦非缺乏審判|§4. 另一種時間理論|§5. 赫美使:牽接的操作子|§6. 數學家的方法|§7. 風格:其他延續數學的方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