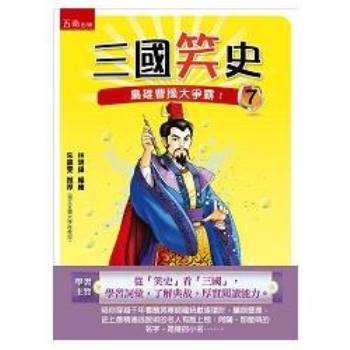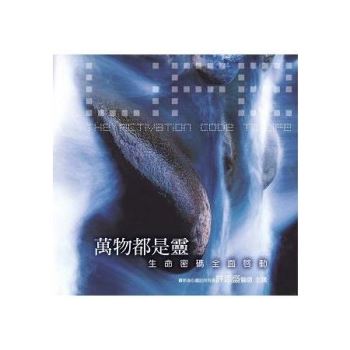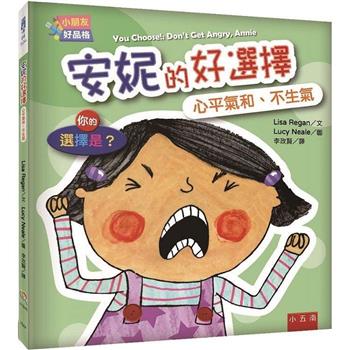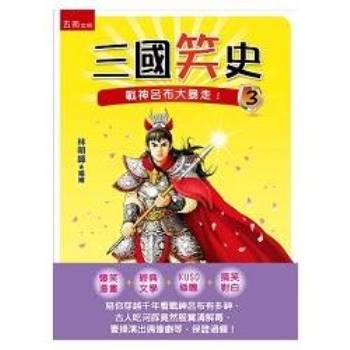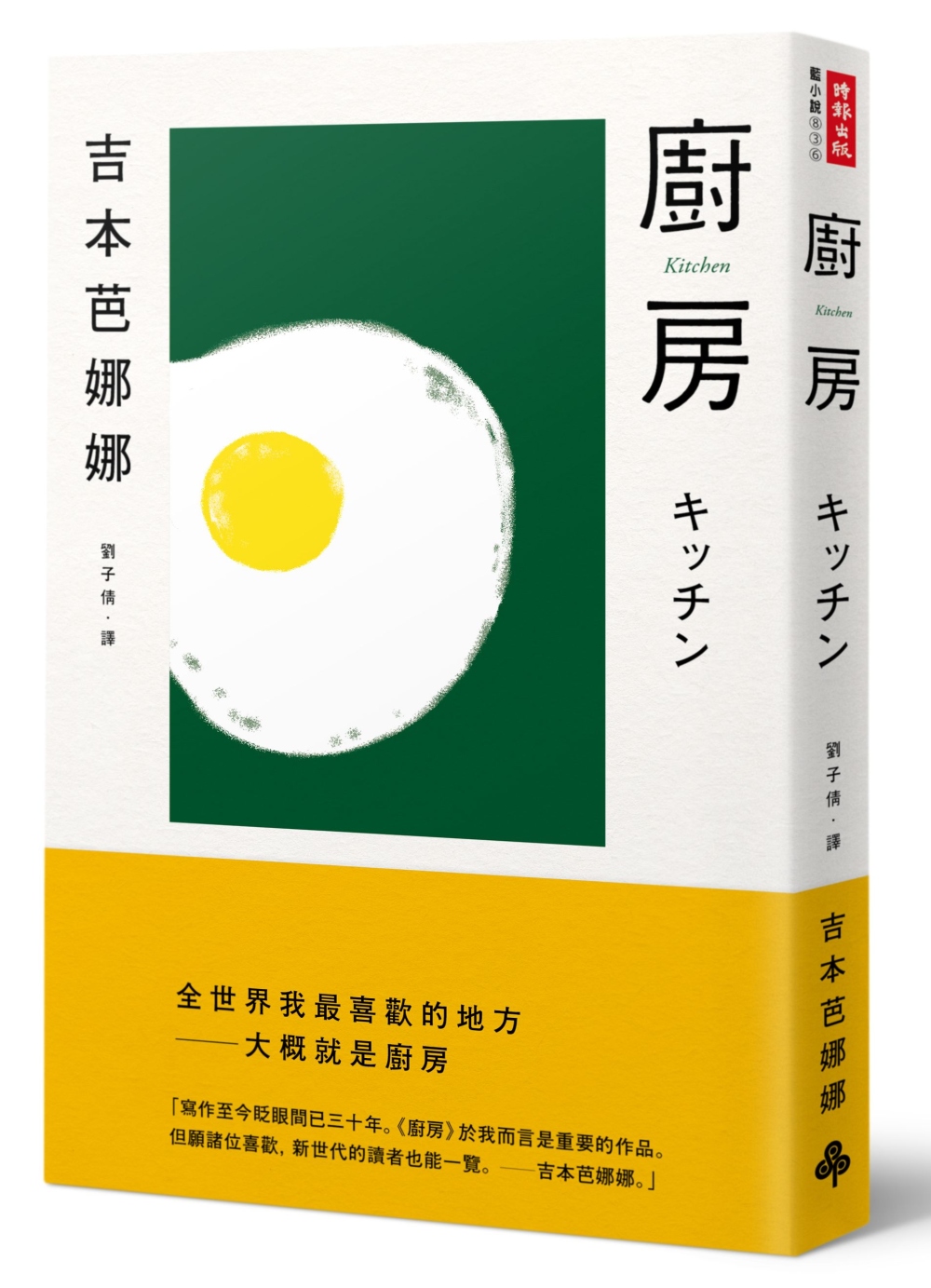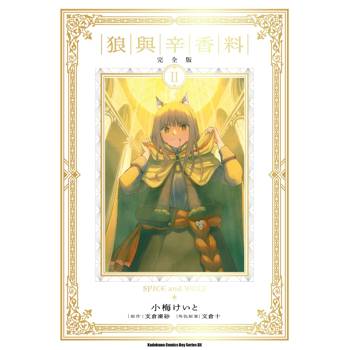為了回答中國當代期刊產業向何處去的問題,本書進行了綿密的縱向歷史線索梳理,及扎實的橫向價值鏈分析,且以文化技術的演進作為溝通相關梳理、分析的線索,在理論框架方面具有創新性。
本書作者號着實物經濟與信息經濟交匯的時代脈搏,以較寬的閱歷、沉穩的心態、良好的文筆,勾畫出了中國當代「期刊人」的理論和實踐探索軌跡,並在概念譜系的厘清、討論的引入、邏輯的貫通等方面,留下了有待開拓的誘人學術空間。
宋革新,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產業(學術專長為期刊產業研究)。曾任《消費指南》雜志副主編、《LADY都市主婦》雜志副主編等職。曾獲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屆「優秀皮書獎•報告獎」二等獎,第二屆、第三屆中國博士后文化發展論壇優秀論文三等獎、二等獎等科研獎項。已出版學術專着2部,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新聞及文藝作品百余篇。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紙刊至電刊的中國探求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紙刊至電刊的中國探求
內容簡介
目錄
第一章問題背景、縱向分析切口/1
一紙刊與電刊之間,事關生死的努力亟待梳理/1
二縱向分析切口:人類呈現可視世界的兩格式三階段/5
三紙刊處近代「相片」階段,電刊屬現代「屏幕」階段/10
第二章電刊屏幕生存史/11
一電視屏幕上的電刊主要屬E—only消費類/11
二電腦屏幕上的電刊主要是專業類紙刊「翻版」/15
三互聯網屏幕上的電刊消費、專業類兼具/17
四移動互聯網屏的電刊重新以消費類為主/22
五成功電刊實踐使期刊獲新定義
——具固定名稱、深度內容、技術比較優勢的定期傳播物/30
第三章三個「頂層」問題及橫向分析框架說明/32
一現代文化市場是如何形成的?/32
二產業變遷:文化產業傳統、新興業態有不同趨向/45
三本書橫向分析框架說明/50
第四章設計:差異化,追尋過渡時期的生存空間/56
一傳媒定位設計歷程:依次為決策者、受眾、廣告主、信息受眾量本位/56
二紙刊的規避替代策略:做內容整體化的專業「領先者」/60
三電刊從內容上成功定位:做信息受眾量占優的搜索「領航者」/65
四從技術演化理解期刊形式:紙刊作為「藝術」,電刊作為「玩具」/80
第五章制作:從大規模生產,到個性化定制/88
一期刊及其制作作為「文化技術」的哲學歷程/89
二紙刊形式的精致化——從鏡子到藝術的「補救」/101
三電刊的多向嘗試——從玩具到鏡子的「補救」/107
第六章行銷:從渠道為王,到中介趨逝/112
一如何在「數字復制」與全球文化產業階段,令我國文化產業「蛙跳」?/113
二紙刊的流程再造,及在產業結構中的負向變化/122
三占據與不占據搜索「領航者」位置的電刊/125
第七章消費:從突破時空限制,到融入創作生產/134
一受眾理論的一種輪廓:從客體,到主體,再到主體間性/135
二選擇:「一人受眾」時代,受眾不在乎什麼?關注什麼?/140
三接受:自由得失 由冷到溫 集於家庭 行為可溯/144
四認同:自我、社團身份強化,而族群、國家身份相對弱化/150
第八章管制:從主體、模式與原則變遷,到雙向權力轉型/154
一主體變遷:從利益集團,到民族國家政府、國際組織及大公司/155
二模式與原則:特許、預審、后懲、登記等制度及其背后原則/160
三我國現況:呈現一模式、多主體、多原則現象/162
四趨向:權力源由暴力至金錢、知識、共享的變遷/167
第九章案例:中外通用的4個「路標」指向前方/171
一延伸紙刊優勢品牌資源做電商,靠含品牌附加值的商品(第三次售賣)營利,如《YOHO!潮流志》等/171
二延伸紙刊內容核心特質至多媒體,靠贊助形態的廣告(第二次售賣)營利,如VICE等/174
三規模化匯聚紙刊內容成搜索「領航者」,靠出售下載文章或數據庫(第一次售賣)營利,如中國知網等/178
四調和「付費牆」與「點擊共產主義」,政府介入探索「開放獲取」有效路徑,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183
參考文獻/190
致謝/198
一紙刊與電刊之間,事關生死的努力亟待梳理/1
二縱向分析切口:人類呈現可視世界的兩格式三階段/5
三紙刊處近代「相片」階段,電刊屬現代「屏幕」階段/10
第二章電刊屏幕生存史/11
一電視屏幕上的電刊主要屬E—only消費類/11
二電腦屏幕上的電刊主要是專業類紙刊「翻版」/15
三互聯網屏幕上的電刊消費、專業類兼具/17
四移動互聯網屏的電刊重新以消費類為主/22
五成功電刊實踐使期刊獲新定義
——具固定名稱、深度內容、技術比較優勢的定期傳播物/30
第三章三個「頂層」問題及橫向分析框架說明/32
一現代文化市場是如何形成的?/32
二產業變遷:文化產業傳統、新興業態有不同趨向/45
三本書橫向分析框架說明/50
第四章設計:差異化,追尋過渡時期的生存空間/56
一傳媒定位設計歷程:依次為決策者、受眾、廣告主、信息受眾量本位/56
二紙刊的規避替代策略:做內容整體化的專業「領先者」/60
三電刊從內容上成功定位:做信息受眾量占優的搜索「領航者」/65
四從技術演化理解期刊形式:紙刊作為「藝術」,電刊作為「玩具」/80
第五章制作:從大規模生產,到個性化定制/88
一期刊及其制作作為「文化技術」的哲學歷程/89
二紙刊形式的精致化——從鏡子到藝術的「補救」/101
三電刊的多向嘗試——從玩具到鏡子的「補救」/107
第六章行銷:從渠道為王,到中介趨逝/112
一如何在「數字復制」與全球文化產業階段,令我國文化產業「蛙跳」?/113
二紙刊的流程再造,及在產業結構中的負向變化/122
三占據與不占據搜索「領航者」位置的電刊/125
第七章消費:從突破時空限制,到融入創作生產/134
一受眾理論的一種輪廓:從客體,到主體,再到主體間性/135
二選擇:「一人受眾」時代,受眾不在乎什麼?關注什麼?/140
三接受:自由得失 由冷到溫 集於家庭 行為可溯/144
四認同:自我、社團身份強化,而族群、國家身份相對弱化/150
第八章管制:從主體、模式與原則變遷,到雙向權力轉型/154
一主體變遷:從利益集團,到民族國家政府、國際組織及大公司/155
二模式與原則:特許、預審、后懲、登記等制度及其背后原則/160
三我國現況:呈現一模式、多主體、多原則現象/162
四趨向:權力源由暴力至金錢、知識、共享的變遷/167
第九章案例:中外通用的4個「路標」指向前方/171
一延伸紙刊優勢品牌資源做電商,靠含品牌附加值的商品(第三次售賣)營利,如《YOHO!潮流志》等/171
二延伸紙刊內容核心特質至多媒體,靠贊助形態的廣告(第二次售賣)營利,如VICE等/174
三規模化匯聚紙刊內容成搜索「領航者」,靠出售下載文章或數據庫(第一次售賣)營利,如中國知網等/178
四調和「付費牆」與「點擊共產主義」,政府介入探索「開放獲取」有效路徑,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183
參考文獻/190
致謝/198
序
本書為了回答中國當代期刊產業向何處去的問題,采用了歷時、共時兩個分析框架,並把文化技術的演進作為貫穿線索,在問題選取、視野開拓、研究旨趣等方面有諸多令人欣喜之處。借着給本書作序的機會,我圍繞相關問題談三點看法。
一以中國問題為立腳點
好的作品都是從問題出發,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問題意識要落實到問題設定上。提出問題是一種理論設計,問題是作者自覺設置的懸念、讀者開悟的鑰匙。因此,對如何提出問題、提出何種問題應有一些評價標准。問題有深有淺,有的人是從別人的問題出發,其實是從別人的理論假設出發、從條條框框出發。當前很多研究就不是以中國問題為出發點,而是從西方觀點、西方的條條框框出發來展開的。這是無根的。例如,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真正好的體制是利伯維爾場體制,最糟糕的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雙軌制;而事實證明,正是漸進式的雙軌制改革成就了中國。
要建立文化發展的中國學派,要從中國問題出發,建立我們自己的理論,完全跟在別人后面不行。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年寫了一本書《中國奇跡》,預測了中國20年的騰飛,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他們是傑出的經濟學學者,這是我們中國自己的理論。
我們提倡做文化使者,因為我們有使命。在研究文化的時候,要以問題為立腳點。那麼,什麼問題是真問題呢?
以你心中的困惑為立足點,你心中的困惑就是所有人的困惑。真正傑出的研究者首先解決自己心中的困惑,只有是自己心中的困惑,你才有興趣;只有存在困惑,你才有動力。當你把問題解決時,你就為社會做出了貢獻。你心中的困惑越深,寫出來,它的震撼力越大、傳播力越強。
二世界視野與「走出去」
說到話語權和話語體系的建設,關鍵是把自己心中的問題研究透,把一個有價值的問題搞明白,占領思想制高點,就有了話語權,才能為真正的「走出去」奠定基礎。
在這方面學術視野的拓展無疑是非常重要的。1919年底,馮友蘭先生要去美國留學之前找到胡適,請教如何選擇留學學校,胡適回答他如果圖名就去哈佛大學,如果真想研究哲學就去哥倫比亞大學。馮先生到哥倫比亞大學之后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說從1915年之后,他才知道在八股之外才有真學問。原來他認為所有的學問都在八股中,后來新文化運動使他明白學問不在八股里,由此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天地。到美國之后,他發現在這個天地之外,有一個更大的天地。這兩個天地是有差別的,這是兩種文化。
這兩種文化能否相處?如何相處?未來的中國文化向何處去?他是帶着這些問題去美國的,而赴美留學帶來的學術視野的拓展,無疑為他從哲學史角度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馮先生1982年去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校方授予他的榮譽博士學位時,在相關講話中再次談到,如何認識和理解中美文化關系是他一生的事業。在這兩種文化中,中國怎麼走,個人如何自處,這兩個問題決定了他從西方哲學回到中國哲學。馮先生學的是西方哲學,后來他轉向中國哲學研究。他的墓碑上寫的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他說,我的著作是我一生的足跡,你想了解我必須知道我為什麼這麼走。他就是要為中華民族找到從舊的傳統走向現代與未來的道路,他通過哲學方式,從文化上思考中華崛起的問題。文化的問題是價值體系的問題,價值體系的問題就是歷史發展道路的問題,作為文人,他只能從哲學角度思考。表面上看,馮先生大的成就是境界說,其實他真正的貢獻是「別共殊」,講文化的共相和殊相,這表達了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理念,而沒有世界性的寬廣學術視野,相關理念是難以建構起來的。
「走出去」現在是一個熱門話題。我認為,現在的學者應向馮先生學習,像他那樣找准並抓住文化領域的某個問題,把這個問題作為自己的領域不懈地研究下去;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有資格和機會代表民族發言,真正「走出去」,為人類文化進步做出貢獻。馮先生有多部中國哲學史著作,由美國人翻譯成英文,這才是真正代表中國發言,真正的「走出去」。
真正的「走出去」是人家邀請你去,是你有成就,不是空投過去,所以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我們的學術成果、學術優勢以及學術獨立性。陳寅恪什麼學位都沒要,他認為佛教對中國產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想要研究佛教就必須掌握它的語言,所以他學了方方面面的語言,他寫出的隋唐政治制度史,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他被國外稱為偉大的史學家,這才是真正的「走出去」。費孝通,國外稱他為中國的最后一位紳士。他的《鄉土中國》是關於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的著作。他搞了一輩子社會學,到晚年回歸到文化問題,思考中國問題。他說要真正強盛起來必須自己走出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別人是指引不了的,需要我們自己找出來。他思考的結果是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既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是世界所有民族文化發展的必經之路。我認為這種思想就是真正「走出去」了。
三把文化研究作為志業
過去人們談「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認為立言是真正的不朽。毛主席帶領人民打天下創立了新中國,他去世后不能再立功,但是他的「雄文四卷」留了下來,像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傳之百代而不衰,這才是不朽的事業。
立德很重要,因為它是立功、立言的前提和基礎。曹禺臨終時給女兒萬方留下三句話:要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卑鄙的靈魂寫不出偉大的作品;要有一顆童心,童心是學術研究和文化創作不竭的動力;要有一種超然獨醒的人生態度。這就是講,要看破紅塵,文化領域不是發財的行業。為了說明超然獨醒的人生態度,曹禺專門把李叔同的詩抄給女兒:「水月不真,惟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為之驅驅,背此真凈,若能悟之,超然獨醒。」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必須有這種胸懷。
每一種工作,都有它的形上層面,有超越世俗的宗教意義;任何學科都是具體的,為之奮斗是因為它有形上層面。所以任何工作,任何事做到極致都可以成佛,成為人們的楷模。從事文化研究沒有使命感和有使命感有天壤之別,從事其他工作也許可以沒有使命感,但是文化行業不行。文化的根本使命是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文化學者的使命,這是文化使者的理想。對於這種理想,要秉承「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信念和意志。
李景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一以中國問題為立腳點
好的作品都是從問題出發,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問題意識要落實到問題設定上。提出問題是一種理論設計,問題是作者自覺設置的懸念、讀者開悟的鑰匙。因此,對如何提出問題、提出何種問題應有一些評價標准。問題有深有淺,有的人是從別人的問題出發,其實是從別人的理論假設出發、從條條框框出發。當前很多研究就不是以中國問題為出發點,而是從西方觀點、西方的條條框框出發來展開的。這是無根的。例如,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真正好的體制是利伯維爾場體制,最糟糕的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雙軌制;而事實證明,正是漸進式的雙軌制改革成就了中國。
要建立文化發展的中國學派,要從中國問題出發,建立我們自己的理論,完全跟在別人后面不行。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年寫了一本書《中國奇跡》,預測了中國20年的騰飛,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他們是傑出的經濟學學者,這是我們中國自己的理論。
我們提倡做文化使者,因為我們有使命。在研究文化的時候,要以問題為立腳點。那麼,什麼問題是真問題呢?
以你心中的困惑為立足點,你心中的困惑就是所有人的困惑。真正傑出的研究者首先解決自己心中的困惑,只有是自己心中的困惑,你才有興趣;只有存在困惑,你才有動力。當你把問題解決時,你就為社會做出了貢獻。你心中的困惑越深,寫出來,它的震撼力越大、傳播力越強。
二世界視野與「走出去」
說到話語權和話語體系的建設,關鍵是把自己心中的問題研究透,把一個有價值的問題搞明白,占領思想制高點,就有了話語權,才能為真正的「走出去」奠定基礎。
在這方面學術視野的拓展無疑是非常重要的。1919年底,馮友蘭先生要去美國留學之前找到胡適,請教如何選擇留學學校,胡適回答他如果圖名就去哈佛大學,如果真想研究哲學就去哥倫比亞大學。馮先生到哥倫比亞大學之后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說從1915年之后,他才知道在八股之外才有真學問。原來他認為所有的學問都在八股中,后來新文化運動使他明白學問不在八股里,由此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天地。到美國之后,他發現在這個天地之外,有一個更大的天地。這兩個天地是有差別的,這是兩種文化。
這兩種文化能否相處?如何相處?未來的中國文化向何處去?他是帶着這些問題去美國的,而赴美留學帶來的學術視野的拓展,無疑為他從哲學史角度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馮先生1982年去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校方授予他的榮譽博士學位時,在相關講話中再次談到,如何認識和理解中美文化關系是他一生的事業。在這兩種文化中,中國怎麼走,個人如何自處,這兩個問題決定了他從西方哲學回到中國哲學。馮先生學的是西方哲學,后來他轉向中國哲學研究。他的墓碑上寫的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他說,我的著作是我一生的足跡,你想了解我必須知道我為什麼這麼走。他就是要為中華民族找到從舊的傳統走向現代與未來的道路,他通過哲學方式,從文化上思考中華崛起的問題。文化的問題是價值體系的問題,價值體系的問題就是歷史發展道路的問題,作為文人,他只能從哲學角度思考。表面上看,馮先生大的成就是境界說,其實他真正的貢獻是「別共殊」,講文化的共相和殊相,這表達了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理念,而沒有世界性的寬廣學術視野,相關理念是難以建構起來的。
「走出去」現在是一個熱門話題。我認為,現在的學者應向馮先生學習,像他那樣找准並抓住文化領域的某個問題,把這個問題作為自己的領域不懈地研究下去;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有資格和機會代表民族發言,真正「走出去」,為人類文化進步做出貢獻。馮先生有多部中國哲學史著作,由美國人翻譯成英文,這才是真正代表中國發言,真正的「走出去」。
真正的「走出去」是人家邀請你去,是你有成就,不是空投過去,所以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我們的學術成果、學術優勢以及學術獨立性。陳寅恪什麼學位都沒要,他認為佛教對中國產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想要研究佛教就必須掌握它的語言,所以他學了方方面面的語言,他寫出的隋唐政治制度史,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他被國外稱為偉大的史學家,這才是真正的「走出去」。費孝通,國外稱他為中國的最后一位紳士。他的《鄉土中國》是關於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的著作。他搞了一輩子社會學,到晚年回歸到文化問題,思考中國問題。他說要真正強盛起來必須自己走出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別人是指引不了的,需要我們自己找出來。他思考的結果是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既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是世界所有民族文化發展的必經之路。我認為這種思想就是真正「走出去」了。
三把文化研究作為志業
過去人們談「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認為立言是真正的不朽。毛主席帶領人民打天下創立了新中國,他去世后不能再立功,但是他的「雄文四卷」留了下來,像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傳之百代而不衰,這才是不朽的事業。
立德很重要,因為它是立功、立言的前提和基礎。曹禺臨終時給女兒萬方留下三句話:要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卑鄙的靈魂寫不出偉大的作品;要有一顆童心,童心是學術研究和文化創作不竭的動力;要有一種超然獨醒的人生態度。這就是講,要看破紅塵,文化領域不是發財的行業。為了說明超然獨醒的人生態度,曹禺專門把李叔同的詩抄給女兒:「水月不真,惟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為之驅驅,背此真凈,若能悟之,超然獨醒。」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必須有這種胸懷。
每一種工作,都有它的形上層面,有超越世俗的宗教意義;任何學科都是具體的,為之奮斗是因為它有形上層面。所以任何工作,任何事做到極致都可以成佛,成為人們的楷模。從事文化研究沒有使命感和有使命感有天壤之別,從事其他工作也許可以沒有使命感,但是文化行業不行。文化的根本使命是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文化學者的使命,這是文化使者的理想。對於這種理想,要秉承「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信念和意志。
李景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