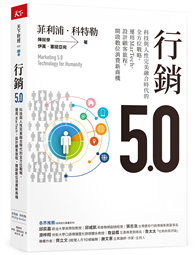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威瑪文化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威瑪文化 作者:彼得‧蓋伊 / 譯者:劉森堯 出版社: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06-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2 |
二手中文書 |
$ 135 |
旅遊 |
$ 299 |
中文書 |
$ 299 |
世界國別史 |
$ 30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真不愧為名家手筆,作者以其簡潔生動文筆,把一個偉大文化的起源和精髓和其政治背景巧妙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有條不紊娓娓道來……對材料的掌握駕輕就熟,而且表達方式精確婉約,展現一種高超的寫作風格。」──《新共和》雜誌,彼得‧傑柯布遜(Peter Jacobson)
「引人入勝……作者真正捕捉到這個時期的精神本質,他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精確可靠的導引。」──《紐約時報》書評,瓦特‧拉克爾(Walter Lagueur)
一個短暫而燦爛的「 黃金20年代」
威瑪共和誕生於1918年,于1933年壽終正寢,時間雖然短暫,卻已經成為一則傳奇。它那痛苦而短暫的生命,令人難忘的藝術成就及其悲劇性的死亡,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相當燦爛奪目。
威瑪讓人聯想到藝術、文學以及思想上的現代化,同時也會聯想到兒子對父親的反叛,達達主義者對藝術的反動,柏林人對粗俗文化的唾棄,自由思想者對保守道德家的鄙夷。
威瑪讓人想到「三便士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卡利加里醫生的小房間」(The Cabsnet of Dr. Caligari)、「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農家」(The Baurhaus)、以及電影女明星瑪琳‧黛德麗。特別是那些被放逐的人,他們把威瑪文化輸出到全世界各地。
在西方文明史上,放逐這類事情向來總是佔有一個相當榮耀的地位,但丁‧格老秀斯(Grotius)、貝爾勒(Bayle)、盧梭、海涅以及馬克思等這些人,他們都是放逐之後在異邦完成他們最偉大的作品,他們用既是憎恨同時又是渴望的眼光回望那曾經拒絕他們的祖國,然後默默寫出曠世傑作。
一九三三年的年初,納粹政權掌控德國之時,希特勒所驅趕出來的這批放逐者可說是世界上極少見的一批具有智識、才華和學問的精英分子。
這批令人目眩的放逐者當中的佼佼者──愛因斯坦、湯瑪斯‧曼(Thomas Mann)、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萊希特、格羅皮奧斯(Walter Gropius)、格羅斯(George Grosz)、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林哈特(Max Reinhardt)、瓦特(Bruno Walter)、貝克曼(Max Beckmann)、傑格(Werner Jaeger)、柯勒(Wolfgang Ko+..gker)、田立克(Paul Tillich)、卡西勒(Ernst Kassirer)這些人逼得我們不得不把威瑪看成是獨一無二的現象,所展現的文化是那麼不受拘束,那麼充滿創意,真真正正的一個黃金時代。的確,威瑪的傳奇正是從「黃金的二十年代」傳奇開始 。
威瑪文化所展現的令人興奮之處在於一部分來自它豐富的創造力和實驗,但絕大部分主要還是來自它的焦慮和恐懼,以及一種命定覆滅的危機感。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這位來自威瑪文化的倖存者,在威瑪共和結束不久前曾公正地指出,未來的人將會把威瑪看成是另一個古希臘的佩利克力斯黃金時代 (Periclean Age)。威瑪文化是由一群局外人所創造,然後由歷史加以推入局內,就像曇花一現那樣,令人目眩,可惜卻那麼脆弱而短暫。
- 作者: 彼得‧蓋伊 譯者: 劉森堯
- 出版社: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3-06-01 ISBN/ISSN:9570411740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西方國別史
|
|